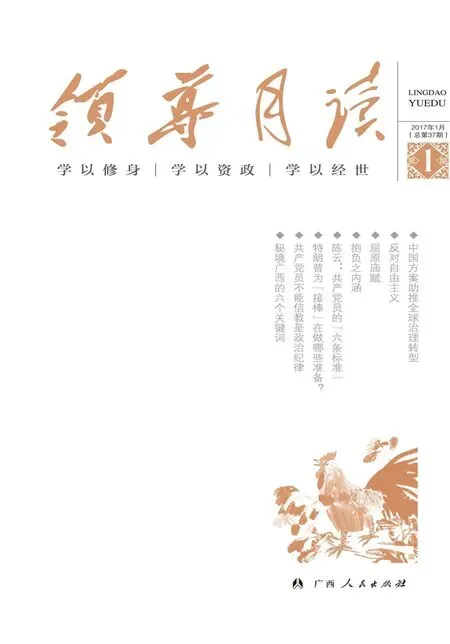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①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后圣,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
(原文據中華書局2010年版《春秋公羊傳譯注》)
【注釋】
①麕(jūn):獐鹿。
【譯文】
“魯哀公十四年的春天,在魯國都城的西邊捕獲了一只麒麟。”為什么要記錄?因為這件事不同尋常。為什么不同尋常?因為麒麟不是地上的物種。那么是誰捕獲了麒麟?一個砍柴的人。砍柴的人地位卑微,為什么要用“狩”這個字?這是為了表示重視。為什么要重視?因為獲麟是很重大的事情。為什么說獲麟是大事?麒麟是一種仁獸,有圣王就會出現,沒有圣王就不會出現。有人告訴孔子說:“有人捉到了一只有角的獐鹿。”孔子就說:“為什么要現身?為什么要現身?”用衣角擦拭眼淚,眼淚把衣服打濕了一大片。顏淵死的時候,孔子說:“唉!老天要我的命啊!”子路死的時候,孔子說:“唉!老天要絕我的路啊!”麒麟被捕獲之后,孔子說:“我的道無法實現了!”《春秋》為什么要從隱公元年開始?因為孔子的祖父輩只能夠聽到那個時候的事情。在表述親眼看見的、親耳聽說的以及傳聞的事情的時候,孔子采取的是不同的方式。《春秋》為什么要以哀公十四年作為結束?原因是這樣就很完備了。孔子為什么要寫《春秋》?遮撥亂世,返歸于正,沒有比《春秋》更能體現這個道理的了。《春秋》只是為了撥亂反正,還是孔子樂于稱頌堯舜之道?還是說堯舜樂于知道孔子會出現?創制《春秋》大義,以待后圣出現,從孔子的作為來看,他也是以此為樂的。
【簡析】
《春秋》本是春秋時期魯國的編年史,經過孔子的修訂和刪削,便以儒家經典的形象流傳于世。孔子之后,先后出現了三種對于《春秋》的傳注,也就是被稱為“《春秋》三傳”的《公羊傳》《穀梁傳》《左傳》。在“三傳”之中,《左傳》偏重于在史實的層面解讀《春秋》,《公羊傳》與《穀梁傳》則試圖闡發孔子的微言大義。在漢代,經由董仲舒的推揚,《公羊傳》最先被立為官學,對漢代的思想與政治影響甚大,堪稱漢代經學與儒學的主干。
本文大意是,麒麟是仁獸,只會在圣王出世的時候現身;春秋時代現身的麒麟,象征著孔子是能改變舊制、創造新制的圣王;可惜的是,麒麟被捕獲并被殺死了,孔子也便注定“有德無位”“吾道窮矣”;因此,孔子只能將自己的圣王制度寄托在《春秋》之中,以供后人效法。可以看出,《公羊傳》試圖借助《春秋》記載的“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這一簡單的史料,引申出一整套“撥亂反正”“為后世制法”的春秋大義,從而開啟了將孔子視為“素王”的說法。
現在來看,盡管《公羊傳》的思維模式具有濃厚的“牽強附會”的性質,但正是在這樣的態度之下,公羊學家才能突破習見與習俗的束縛與限制,而發揮儒學經世致用的效用;在晚清時期,康有為正是借助對《公羊傳》的全新闡發而展開其維新改良運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