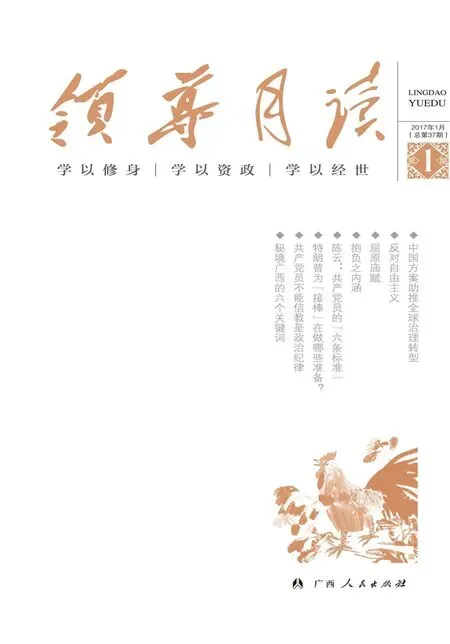“歐洲中心”格局的興起與衰落
張一飛
國際視野
“歐洲中心”格局的興起與衰落
張一飛
國際格局主要指涉國際范圍內主權國家之間根據權力分配形成的結構體系,它是主權國家體系形成后,全球化進程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只有交互聯系而無主權意識,則無法產生權力關系,而會走向融合;只有主權國家存在而無深刻聯系,則無法產生結構體系,而會走向離散。因此,在國際格局形成之初,誰主導了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與主權意識的形成,誰就會在國際格局中居于權力結構的中心地位。從人類歷史上看,自15世紀起,是歐洲國家掌握了國際格局形成階段的“天時”。
“歐洲中心”格局的興起
全球化進程由歐洲國家開啟。作為“海洋—商業—軍事”文明的載體(區別于“大陸—農業—文化”文明載體),歐洲各國對于海外世界的探索極為熱衷。“海洋文明”屬性使歐洲國家對外部充滿好奇,對家園沒有情感羈絆,原因在于:支離破碎的地理環境和政治環境沒有產生內部向心力;“商業文明”屬性使歐洲國家對貿易持久狂熱,對耕作沒有耐心,自古希臘時期起,歐洲人便“寧為海盜,不為耕夫”;“軍事文明”屬性使歐洲國家對于征服習以為常,對搶掠沒有道德負擔,自古希臘時期起,幾乎各城邦國家都鼓勵外出劫掠。因此,有了成熟的技術,加上早期殖民國家支持,歐洲航海家從15世紀開啟了大航海時代,他們對于建立全世界的聯系與溝通功不可沒。
從1488年迪亞士抵達好望角到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從達伽馬抵達印度到麥哲倫環球航行,一大批歐洲的優秀航海家勾勒出了全世界的海洋航路。掌握航路不僅意味著巨額的經濟利益,也意味著價值觀念和政治理念的傳播。掌握經濟利益,意味著硬實力的增強;傳播價值理念,意味著軟實力的擴散。從根本上加速了全球化進程的歐洲,在軟硬實力上都逐漸凌駕于各其他文明國家之上。
主權概念在歐洲形成。與新航路帶來的現實變化相輔相成的是歐洲精神世界的變化。一方面,新航路開辟帶來的巨大貿易利益使歐洲資本主義力量空前發展,原來“神權—君權”的權力結構對個人自由和世俗社會的限制,日益成為資產階級利益最大化的障礙;另一方面,提倡簡化宗教的宗教改革和以人為本的文藝復興,為更多歐洲國家指出了新方向,即宗教世俗化,政治自由化。在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都經歷了巨大變革后,讓·博丹、格勞修斯等一批思想家就君主國家興起提出了“主權”概念,即“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絕對的,永恒的,最高的權力”。主權概念從根本上終結了神權的權威,確立了世俗民族國家的永恒存在和權力界限,并且在三十年戰爭(天主教國家和新教國家的戰爭,1618—1648)后得到歐洲各國的普遍承認。隨著歐洲后來的殖民擴張,主權概念為各個文明國家所接受,直到今天仍然作為國際關系的核心概念存在,其發源地在國際格局形成之初,自然而然掌握了巨大的組織能力和話語權威。可以說,主權概念是歐洲塑造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基礎和開始。
“歐洲中心”格局的崩潰
主權概念的確立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國家存在的問題,但并沒有解決國家安全的問題,存在只是活著,但活著不一定安全,更不一定幸福。從17世紀后半葉起,歐洲的內部圍繞國家安全持續戰爭;尤其是自19世紀后半葉起,歐洲在國際格局中的權力中心地位經由歐洲內部的權力斗爭逐漸喪失。
權力均衡難實現。三十年戰爭后,尤其到了工業革命之后,歐洲的世界中心地位得以確立,但是歐洲內部始終面臨權力均衡難題,以至于戰爭不斷。所謂權力均衡難題,是指歐洲各國在從神權中解放出來之后,多個世俗權力中心并立,以致無法真正實現相互制衡與大局穩定。以三十年戰爭后至一戰前歐洲經典“五強格局”為例:英國始終扮演離岸平衡手的角色,加入弱小同盟制衡歐洲大陸的最強者;法國與德國(1871年之前為普魯士)不斷爭奪歐洲大陸霸主地位;奧地利主導中歐(1867年至1918年為奧匈帝國);俄國隨時準備西擴。這些國家各具優勢:英國的海軍強大,法國、德國的陸軍強大,奧地利占據中心位置,俄國具有遼闊內陸,并且他們都希望利用自身優勢獲得歐洲內部的權力中心地位,尤其是法蘭西帝國和德意志帝國分別受到來自周邊國家的圍攻,權力均衡只能通過一次次戰爭得到短暫的調整與維護,很難長期實現。
安全困境難解決。權力均衡無法實現的根本原因,是三十年戰爭后到二戰前,處于無政府且無核威懾下的多極歐洲,始終處在安全困境之中。由于諸國都具有進攻能力,且強國之間難以獲得彼此的真實意圖,各強國為維護國家安全只能依賴自身實力的增強,而任何國家實力的增強都會引起其他國家的猜忌和進一步自強,這一惡性循環最終往往以戰爭收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英國和德國對彼此的海洋力量都有所顧忌,但并不能真正判斷對方的真實意圖,于是陷入防御性軍備競賽,在薩拉熱窩事件后,通過戰爭釋放了各自積累的怨氣和能量。由于國家安全是國家關心的第一要務,各國不得不在涉及安全的事務上采取“底線思維”,將最壞情況視作常態,最后往往導致“自我實現的預言”,這正是歐洲歷史上“大國政治的悲劇”。
內耗過大難挽回。在經歷了遺產繼承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英荷戰爭、北方戰爭、拿破侖戰爭、德國統一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在物質和精神上確立的絕對優勢消耗殆盡。尤其是19世紀中葉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之后,世界其他地區與歐洲的相對差距逐漸縮小,盡管其精神遺產仍然影響著人類歷史的進程,但是在國際格局中的權力中心地位逐漸喪失,尤其是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殖民體系的崩潰以及美國和蘇聯的崛起對“歐洲中心”格局形成了根本性挑戰,歐洲在傷及元氣的內耗中喪失了對外部世界的干預和控制,逐漸由中心權力淪為一般權力。
“歐洲中心”格局的興起是歐洲連接世界、塑造世界的過程,其衰落是歐洲內部消耗和外部崛起的產物。把歐洲近代歷史與古希臘城邦歷史、中國春秋戰國歷史、日本戰國歷史等時期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它們的時間長度、戰爭進程、興衰原因都十分相似。在比較中可以發現:從權力關系來看,多極體系中國家對外政策靈活性極強,“朝秦暮楚”即為常態,極不穩定,至少不如兩極格局穩定;從國家戰略來看,國家之間彼此不能判斷真實意圖是主權國家的根本性“詛咒”,只要這一點仍然是現實,國家在思維的內核中便不會放棄“底線”思考和最壞打算;從國家崛起來看,新興國家在崛起過程中必須能夠為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和社會提供新質,如技術革命、思想更新、制度設計等,才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崛起,而不是單純物質權力層面的挑戰。
(摘自2016年10月17日《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