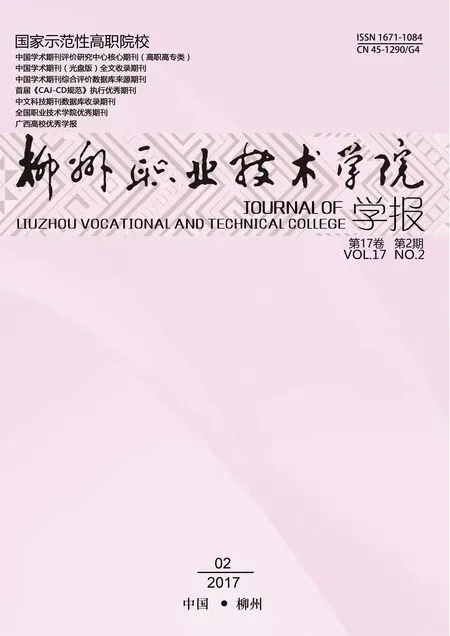探析西方公共行政理論價值變遷中的鐘擺現象
何琦潤
(廣西師范大學,廣西 桂林 541006)
[政治與社會經濟研究]
探析西方公共行政理論價值變遷中的鐘擺現象
何琦潤
(廣西師范大學,廣西 桂林 541006)
公共行政過程被視為對多元價值目標的平衡與追求的過程,公共行政的理論發展可以分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兩大流派,在其理論發展過程中,公共行政學的核心價值也隨著這兩大流派的交替出現而不斷發展演進,具體表現為對行政效率、行政過程蘊含的公共性和公平公正以及對公民和社會的回應性等觀念的追求。
公共行政;鐘擺現象;工具理性;價值理性
引言
從西方公共行政學發展歷程中,人們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即每一個階段的主導理論所包含的價值觀念是有明顯區別的,從一個主導價值觀念到與之對立的價值觀念,采取的工具、手段和目標也從一邊向與之對立的另一邊發展,公共行政學理論就是這樣不斷地更替演進,這樣的現象可以稱之為“鐘擺現象”,其類似于鐘擺的運行規律。主導價值觀念作為公共行政的靈魂,貫穿于公共行政活動過程的始終,是公共行政的終極目標和行動理念,對處在公共行政活動中的人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對研究公共行政的學者來說,主導價值觀念即核心價值代表他們不同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以及產生的研究結果。對公共行政活動的決策和執行者來說,核心價值直接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式,以及政府目標的確定。不同的學者所處的時代不同,導致其面對不同的社會問題和行政問題,他們在當前時代環境的影響下對政府實踐活動采取不同的態度和觀察角度,由此對于什么是政府應當承擔的主要責任和政府應當采取的行政實踐存在不同的看法,因此不同的學者追求的價值不同,從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公共行政理論。例如,威爾遜認為政治過多干預了行政,導致政府運作的效率較低,因此主張將政治與行政分隔開,為公共行政走向企業化行政道路埋下伏筆。而后來的學者則發現由于政府過多模仿企業的管理方式方法,導致政府行政過程中對效率、效能和經濟的極大關注,而缺乏對社會公平正義、政府對公民和社會的回應、公民參與的關注,因此主張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從而形成了所謂的“新公共行政”運動。
一、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
在西方公共行政學發展演進中,每一個階段的主導理論存在和以往有明顯區別的核心價值觀念,主要表現為工具理性或價值理性,這兩種價值觀念總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交替出現。
“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是由德國社會學家韋伯在研究社會行動時提出并加以詳細論述的。他認為,工具理性的社會行動取決于“對客體在環境中的表現和他人的表現的預期,將這些預期轉化為實現目標和追求的工具。而價值理性的社會行動取決于“內化為行動中的價值理念和信仰,這種不論是哪方面的價值和理念的體現伴隨著行動過程的始終,因此它側重于這個過程而不是結果”[1]。這段表述可以被理解為,工具理性強調手段——目的的合理性,主張通過精確的科學計算和縝密的邏輯推理來實現所預設的目標,而不關心行為本身的意義和價值;價值理性關注行為本身的合目的性,追求行為本身所具有的意義,要求人的行為必須指向美好的價值,而不管它的結果成功與否。簡而言之,前者關注“是什么”“如何做”的問題,通常與方法、技術、手段等工具相聯系,所追求的是科學性、有效性;后者關心“應是什么”的問題,往往與人性、信仰、信念、關懷、德行等目的性的價值相關聯,所追求的是正當性與公正性。工具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學強調效率優先,堅持理性——自利人的假設,傾向實證的研究方法,主張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積極構建行政科學。而價值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學注重公共精神的培養,堅持反思——利他人的假設,喜好規范的研究方法,主張政治家的角色定位,努力追求行政哲學。
對于西方公共行政學理論發展史,不同的學者從不同的角度來研究,其中一個主要的劃分方法就是“范式論”。“范式”一詞由美國學者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2]提出。他認為,“范式是經過大部分人肯定并且成為通用的模型或模式”。我國學者陳振明[3]提出了傳統公共行政學、新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學三范式;美國學者登哈特夫婦[4]也提出三范式論,即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毛壽龍和李文釗[5]提出四范式論,即官僚制行政理論、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民主制行政理論。
二、傳統公共行政學(工具理性)
行政學產生于政治學,但是經過發展從政治學中脫離出來。政治學被認為是行政學的理論基礎,將二者的關系比喻成花與樹,根與果的關系。伍德羅·威爾遜于1887年發表的《行政學研究》這篇文章開了美國行政學研究的先河,在此文中他將行政學從政治學中提煉出來研究。威爾遜在該文中提出行政和政治應當分屬于兩個不同的領域,所要研究的內容和問題也不盡相同。雖然政治規定了行政研究和實踐的目標,但是政治不能控制行政實踐過程。隨后,古德諾對威爾遜提出上述觀念做了進一步的研究和探討,他將政府功能劃分為兩類,一是“政治”即表達國家意志,二是“行政”即“執行國家意志”。[6]
威爾遜認為,行政是一門純粹技術性和應用性的學科,效率被視為行政學的目標也是行政學的核心價值。因此,為了獲得高效率的行政實踐,韋伯的官僚制層級組織產生了,“官僚組織的盛行和大范圍采用,離不開它對效率的追求,并且在此過程中影響組織成員為共同的目標一起努力。”[7]此外,泰勒提出的科學管理思想和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再一次豐富了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發展。威爾遜認為,行政作為工具,它是中立的,不需要包含價值因素,只有實現了它對高效行政實踐的追求,才實現了它對價值的追求。
三、新公共行政理論(價值理性)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出現了一系列危機,人們開始呼吁政府改革,以改變現有困境。因此,一些學者開始回顧和反思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缺陷,新公共行政學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了。1968年,包括弗雷德里克森在內的一批學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召開了有關公共行政學發展趨勢的會議。
新公共行政理論將“公共”作為研究的中心,它不僅追求傳統公共行政學所強調的經濟、高效和協調的價值理念,還追求社會的公平公正,強調在為社會高效經濟地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同時注重社會公平的實現。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和傳統公共行政學相比,新公共行政學不僅關注如何高效率的利用資源來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服務和如何在控制財政支出的情況下保持公共品與公共服務的供給,而且關注這種服務是否增進了社會公平?”即傳統公共行政學更多的是對經濟和效率的追求,而新公共行政學賦予了這一追求行為價值理念。新公共行政學主張公共行政不僅僅是有效的執行政策,而且由于它的“公共性”,它還擔負著廣泛的社會責任,需要了解廣大人民群眾的真實需求,并對此做出積極的反應,以此更進一步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標,承擔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新公共行政理論對“效率”所代表的含義有不同的認識。通常所說的效率,是少投入和大產出之間的比,也即傳統公共行政理論的理解。而新公共行政理論給“效率”賦予的含義則豐富的多,將價值觀念灌輸其中,即在追求效率的過程中必須時刻拷問是否促進了社會公平和人民利益的表達和滿足,考慮到社會性的公平分配,以有效改善公民的生活水平為目標。新公共行政理論認為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在于社會公平,即盡可能公平地分配公共利益,照顧到處于弱勢的群體。弗雷德里克森有一句話所表達的含義是:“新公共行政追求的社會公平意味著將部分公共權力和社會資源與福利的天平倒向社會中明顯缺乏這些的弱勢群體,”。即盡可能地對這些在社會分配過程中得到最少的群體給予應有的彌補,努力增加社會中的公平。新公共行政反對傳統公共行政所堅持的價值中立,他們認為,制定和執行政策的政府官員與研究公共行政學的學者們不可避免地會將自己的價值觀念和經驗加到決策和學術思想中,價值中立在學術研究和行政實踐活動中都不存在。
四、新公共管理理論(工具理性)
新公共管理最典型的表現形式便是奧斯本等人提出的企業家政府理論。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西方經濟危機擴大的背景下,需要政府做出有效應對,因此不可避免地要求政府的行政改革。企業家政府理論是對西方傳統官僚制政府組織的反思,在官僚制產生和盛行的時代,它代表著理想高效的組織形式,它的層級組織形式和專業化管理使高效地完成大規模的復雜任務成為可能,而現在的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較大的改變,經濟全球化使得原來的經濟模式不再適應新的時代要求,大數據和云計算的產生使得信息的傳播與獲取變得容易,并且公眾也能獲得相較以往更多的知識和信息,這使得在信息領域官僚和公眾的地位變得平等,由此看來行動遲緩、效率低下的政府已經不再適應當今社會的需求。“企業家”一詞是由法國經濟學家J.B.薩伊創造的,他認為企業家有敏銳的洞察力可以將資源轉向效率高的領域和地方,以達到高效利用。在奧斯本看來,薩伊對“企業家”一詞的解釋不僅適用于私人部門,也適用于公共部門和第三部門,它們都是合理的利用資源,注重投入和產出,提高行政效率。但是,奧斯本同時指出政府組織和企業組織存在明顯的差異,它們是兩個不同類型的組織。他指出“人們不能將他所要表達的意思誤解為政府行動過程和企業行動過程一樣。那就弄錯了。”[8]他認為,企業與政府有以下幾方面的不同:首先,企業領導者是為了獲取利潤而政府領導者是為了連任;其次,企業收入來自顧客,政府收入來自納稅者;再次,政府動力源于壟斷,企業動力源于競爭;最后,企業是對有支付能力并且支付了的顧客提供服務,政府必須對每個人提供平等的服務,不論他的支付能力如何,因此企業的行動要比政府快。奧斯本同時強調:“雖然政府行動過程和企業行動過程不一樣,但政府依然有企業家精神,且不見得比企業所擁有的少。”政府應當像企業家那樣“掌舵”而不是“劃槳”,具備分權意識將權力合理地下放,并不需要親身參與到每件具體事務的處理中,可以適當的引入競爭,注重目標的實現,具備顧客意識,將等級制的組織適當扁平化,相比行政指令而言傾向于市場作用的發揮。
新公共管理理論對管理理念的追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以管理學為出發點,對前人的看法提出了批判,尤其是韋伯提出的官僚組織,它認為官僚組織存在過度集權和管制、效率低下、組織僵化等問題,只有引入私人部門的管理技術,改變官僚組織,才能為其注入新的活力,改變其痼疾。[9]其核心價值在于“3E”即經濟、效率與效能,注重高效高質的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務,注重提高公民滿意度。
五、新公共服務理論(價值理性)
新公共服務理論認為,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非“掌舵”。新公共服務理論對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超越體現在對公平、公正、民主的價值理念的關注。新公共管理理論過多地注重效率和經濟管理層面的價值,主張政府向企業學習,主張政府“掌舵人”的角色定位,忽視了公共行政價值規范和倫理準則的建設。因此,新公共服務理論倡導公民權,強調公共行政的“公共性”、社會的公平公正、政府官員的回應性、公民的參與,堅持民主精神是公共行政的基本價值觀念。正是基于以上價值理念新公共服務理論提出了一種新的行政模式,該模式將政府定位于服務者的角色,賦予行政過程新的價值理念。[10]
新公共服務理論追求的公共利益,不是個體自我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建立在公民對話協商基礎上對共同價值觀念追求基礎上形成的利益。公民不是顧客政府也不是企業,只有公民成為公民時,才能追求公共利益而不是滿足個人需求。政府的責任在于服務社會和公眾,政府官員和行政人員要明確地意識到公共資源不屬于政府或者行政人員私有,而是公共的,他們在實踐過程中應該考慮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如果這筆錢是我的,我應該怎么花”這種問題。在政府的行政實踐過程中,效率是重要的,但它應該是在公共利益和公民權利的框架內思考。
六、后新公共管理理論叢林
(一)整體政府理論與網絡化治理理論 (工具理性)
整體性政府理論的出現是針對新公共管理理論提出而導致的政府部門過度專業化和分權化的問題,這種碎片化不僅沒能有效提高政府效率,反而加深了政府低效,各部門之間不能有效協調,注重的都是各部門的利益,忽視了對整體利益的追求,無人對整體負責。整體政府理論強調政府之間、政府各部門之間和政府各層級之間的合作聯動,強調協調整合,注重在技術層面改進政府治理模式。湯姆·林在對西方政府改革實踐和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最佳實踐的整體政府概念,由以下四個部分構成:“內”指組織內部的合作,“外”指組織之間的合作,“上”指組織目標的設計與貫徹是自上而下以及對上的責任承擔,“下”,指以顧客需要為服務宗旨的公共服務供給過程。[11]整體政府理論追求的核心價值是整合,既包括政府部門之間基于工作辦事流程的整合,也包括政府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以及私人企業基于共同的合作愿景的整合,打破部門之間的壁壘,促使資源和信息在其中的順暢流通。
基于西方學者認為市場和科層制的官僚組織都不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治理方式,有必要催生一種新的治理形式,于是網絡治理理論興起。在網絡治理模式中政府只是其中一個行動者,還包括第三部門和參與到社會治理中的私人部門。各行動者之間基于信任和依賴而進行資源共享。網絡治理模式的構建,要求網絡中的行動者要有共同的目標,能夠在實現共同目標的過程中互惠互利,各行動者之間無障礙地分享和運用各種信息和資源,在此情況下減少交易成本和溝通成本。與傳統科層制相比,網絡治理結構體現了一種水平協調的模式,決策是由各行動者共同參與和協商形成,各行動者之間是一種多點對多點的關系。網絡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各行動者之間的共同價值,他們是基于協商一致的、相互認可的共同準則連接在一起,而不是基于權威。各行動者之間是靈活、松散地聯系在一起,不是按照規則治理,由具有權威的政府主導在權力的控制下活動。從以上概述可以看出,網絡治理理論著重的不是給公共行政注入新的價值觀念,而是提出一種新的社會治理模式。
(二)公共價值理論(價值理性)
新公共管理理論的弊端使得政府部門不再單純注視工具層面管理技能的提高,而開始反思被忽略的公共行政價值。公共價值理論不是針對某一價值的追求,而是對不同價值加以整合,體現對價值的包容性。這一包容性的展開建立在“公民”定位的基礎之上。[12]對公共價值的追求在于將“基于政府判斷然后決定供給的公共品和服務”與“公眾認為重要的需求”聯接起來。[13]如何確定公共價值,即在公共行政實踐活動中確定主導價值,需要考慮公民意愿,是經過溝通、協商、互動達成的整體利益訴求。政府要承擔起公平、平等的責任;不僅把公民視為公共服務的對象和評價者,促進公民參與行政過程,使公民權得到全面的發揮而不是口頭上的宣揚。公共價值理論重新喚起人們對于公共價值的追求,它試圖將民主和效率兩大目標融合,充分發揮公民在行政實踐活動中的積極作用,強調公民和政府官員以及政治精英共同治理社會,維持社會平穩發展。
七、公共行政理論的發展方向
從西方公共行政理論演變過程中可以發現,其發展伴隨著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交替出現。在一個時間段特別突出工具、技術、手段和方法,在下一個時間段就會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著重提出行政過程中的公平公正、民主等公共性主張。這樣的發展是伴隨著公共行政環境的變化,在最初其所處的環境是單一的,所需處理的公共事務較少,到后來公共行政的環境趨向多元化,面對的挑戰和所需處理的事務呈指數遞增,這就要求公共行政理論與時俱進。
事物的發展總是遵循著這樣的規律,發展到一個極端后就會偏向另一個極端,被忽略的事物會被重新拿起,公共行政對管理效率和管理價值的追求,但這一變遷過程不僅僅是簡單地拿起過去的成果,而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吸取精華留下糟粕。現在興起了這樣一個趨勢,即試圖將公共行政中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融合,這個融合不是指二者處于平等的地位,而是在以一方為主的情況下,兼顧另一方。隨著公共行政客觀環境的變化,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技術的興起,公民參與熱情的升溫,筆者有理由相信在未來,公共行政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這二者是可以進一步融合的。
[1]馬克思·韋伯.經濟與社會(第一卷)[M].閻克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348.
[2]托馬斯·庫恩金吾倫.科學革命的結構[M].胡新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21.
[3]陳振明.從公共行政學、新公共行政學到公共管理學——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領域的“范式”變化[J].政治學研究,1999,(1):79.
[4]珍妮特·V·登哈特,羅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務:服務,而不是掌舵[M].丁煌,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25.
[5]毛壽龍.西方公共行政學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13.
[6]古德諾.政治與行政(中譯本)[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12-13.
[7]羅伯特·B·登哈特.公共組織理論[M].扶松茂,丁力,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36.
[8]戴維·奧斯本.改革政府——企業精神如何改革著公共部門(中譯本)[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6:25.
[9]國家行政學院編譯.西方國家行政改革評述[M].北京: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1998:57.
[10]丁煌.西方行政學說史(第二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4:414.
[11]蔡立輝,龔鳴.整體政府:分割模式的一場管理革命[J].學術研究,2010,(5):36.
[12]楊博,謝光遠.論“公共價值管理”一種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超越與限度[J].政治學研究,2014,(6):118.
[13]王學軍,張弘.公共價值的研究路徑與前沿問題[J].公共管理學報,2013,(2):127.
On the Pendulum Phenomenon in the Value ChangeofW estern Public Adm inistration Theory
HEQi-run
(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ilin Guangxi541006,China)
The processofpublic adm inistration isregarded asthe processofbalance and pursuitofpluralistic value.The theoreticaldevelopmentofpublic adm inistr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twomajor schools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In the course of its theoreticaldevelopment,the core value ofpublic adm inistrationw ith theemergence of these two schoolsof the emergence of the continuousevolu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adm inistrative efficiency,adm inistrative process contains the public and fairand impartialand the response to the conceptof the pursuitofcitizensand society.
public adm inistration;pendulum phenomenon;instrumental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
D 035-0
A
1671-1084(2017)02-0019-05
DOI 10.16221/j.cnki.issn1671-1084.2017.02.005
2016-11-05
廣西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云治理——大數據時代社會治理的新模式研究”
何琦潤,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2015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族地區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