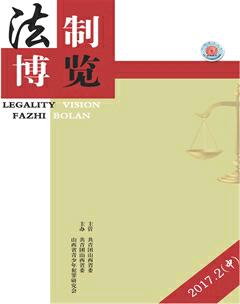淺析東西家長權
劉歡++于思染
摘要:由于地理、歷史等因素的影響,古代東西方分別發展出了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截然不同的兩種文明。但雙方的法律制度都不約而同地將一種名為“家長權”或者“父權”的權力規定于各自的法典之中,將其作為各自法律的核心與基礎。雙方的家長權在內容上雖然有諸多不同,但也有很多的共通之處。本文通過對古代中國家長權與羅馬家長權的對比,來探索家長權的概念、內容、歷史變遷與性質,以求對古代的“家長權”有一個較為全面的了解。
關鍵詞:家長權;父;權力
中圖分類號:D9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5-0071-03
作者簡介:劉歡(1996-),男,漢族,山東濱州人,青島大學法學院,法律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法理學;于思染(1996-),女,漢族,山東淄博人,青島大學法學院,法律專業本科生,研究方向:法制史。
一、家長權的概念
家長權,在羅馬和古代中國有不同的名稱,其概念內涵也不盡相同。在羅馬,它被稱為“家長權”或者“家父權”,概念則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家長權是指家長對家屬、奴隸、牲畜和其它財產的支配。狹義的僅以家屬為對象,也就是男性市民中的自權人對其家屬享有的支配權。”[1]在古代中國,家長權則被稱為“父權”“戶主權”,概念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中國家長權指家長對于家族和家庭的經濟權、法律權、宗教權,狹義的中國家長權僅指是家長對家庭的經濟權、法律權、宗教權。雖然兩國家長權在名稱、概念表述上有差異,但在構成兩國“家長權”的基本要素方面卻是相同的:(一)在行為主體方面,兩國家長權的行為主體是相同的。無論是羅馬的“家父權”還是中國的“父權”,其主體都為成年男性,女性被排除在家長權的行使主體范圍外。同時,成年男性還要滿足“上無父系直系尊親屬”的條件,若有父系直系尊親屬,則該父系直系尊親屬為家長。(二)行為客體方面,羅馬家長權的客體包括“家屬、奴隸、牲畜和其它財產”。中國家長權的客體則包括家屬,家庭財產和家庭宗教活動。由于中國的“家”包含“家庭”和“家族”兩種概念,因此中國的家長權的客體有時還包括家族成員,家族財產和家族宗教祭祀活動。排除由于中西文化不同造成的細微差異,家長權的行為客體主要是家庭中的家屬人身和家庭財產。(三)內容方面,家長權的內容是家長權主體對于家長權客體的支配與處分,即家長對于家屬人身和家庭財產的控制。(四)性質方面,“(羅馬)家長權的依據是權力關系,而不是權利義務關系,所以它原來不受法律的限制,不負任何責任。”[2]“中國的家族是父權家長制的,父祖是統治的首腦,一切權力都集中在他手中。”[3]因此,家長權中的“權”是一種權力(power),而不是一種權利(right)。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家長權,是家庭中上無父系直系尊親屬的成年男性,對于其下家屬的人身和家庭財產進行控制支配的一種權力。
二、家長權的內容
家長對家屬人身的控制有三方面的含義,分別是家長對子女的生殺權、家長對子女人身和思想自由的控制權以及丈夫對妻子的夫權。
首先,在古代社會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背景下,古代人的普遍觀念是,子女實際上是家長的財產。同時他們也認為,財產所有權人可以自由地處分自己的財產。因此,我們得出結論:家長權,其實就是家長對子女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家長決定是否“占有”子女,即家長對子女生殺權,則是家長權的首要內容。羅馬《十二表法》第四表規定“對奇形怪狀的嬰兒,也即殺之”,此權利不但可以在子女處于嬰孩時期行使,也可以延續到子女成年時期,“家長(對于子女)得監禁之、毆打之、使做苦役、甚至出賣之或殺死之”[4]古代中國則“父而是賜子死,尚安敢復請。”[5]在公元2世紀,羅馬便廢除了家長的生殺權,僅保留家長對子女的一般懲戒權。相比之下,古代中國雖然在法律上禁止家長濫殺子女,但在現實生活中,若是家長殺死子女,是不會被懲罰或者懲罰極輕。家長可以聲稱“違反教令”或“不孝”向官方要求免責或者減責。而且,雖然法律否認了家長的生殺權,但又補充性的授予家長“送懲權”,家長可以以“違反教令”或者“不孝”的名義將子女送官懲治,這實際上是給予家長變相的生殺權,可以被認為是家長的“間接生殺權”。對此,瞿同祖也認為“國家所收回的只是生殺的權力,但堅持的也只是一點,對于父母生殺的意志一直卻并未否認,只是要求代為執行。”[6]
其次,子女要終身處于家長的控制之下,除非由于婚姻(女)或家長(子)的死亡而處于新的家長控制之下或者自己成為家長。在此期間,“家長得監禁之、毆打之、使做苦役,甚至出賣之或者殺死之。”家長可以將子女賣給他人為奴。子女沒有思想的權利,也沒有選擇自己婚姻的權利,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實際是家長對子女的使用、收益和處分,其目的是為了家長的利益最大化。
最后,家長對自己的配偶享有夫權。夫權,意為丈夫對妻子享有的權力。古代東西方文明的共同點之一是,妻子與丈夫相互之間并不是平等的主體,而是依附與被依附的關系。古羅馬的俗語“妻子其實是其丈夫的女兒”清晰地表明了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在古代中國,雖然沒有這樣的說法,但在中國古代法中,妻子侵犯丈夫,比照“下犯上”,卑幼侵犯尊長的規定處罰。那么根據筆者前面提出的邏輯,妻子其實也是家長,即她的丈夫的財產,夫權內容比照家長對于子女的權力的內容。但在現實生活中,妻子或者母親似乎享有比子女更多的權利或者更高的地位,似乎家長的配偶與家長的地位相同。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家長的配偶與家長的關系依然是我們前面所描述的關系。妻子或母親作為家長的配偶,對于家長確實有不同于其他家屬的意義,因此夫權的內容相對于家長權較為緩和,如丈夫不可以隨意殺死自己的妻子,妻子也有一定的思想表達自由等。但這只是普遍中的例外,在大方面,妻子是絕對受命于丈夫的。至于母親也可以對子女進行“處分”,則是歸功于家長權的“輻射效應”。家長的配偶,相較于家中的其他成員更接近于家長,因而受到了家長權力的“輻射”。基于這種“輻射”,她的言行對家中的其他成員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這種影響力是基于倫理基礎而不是物質與法律基礎。
家長對家庭財產的控制是家長權制度得以維持的物質基礎,是家長權的核心,家長排他性地獨占家庭財產,脫離家長的家屬喪失在社會上生存的物質條件。家長控制家庭財產有兩方面的內容:(一)家長享有家庭中所有財產的所有權,家屬沒有自己獨立的財產。《坊記》云:“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二)家屬對家庭財產的處分行為的,法律認定為無效。在古代中國,要求“物即還主,財沒不追。”除此之外,這種擅自處分行為還要受到刑罰處罰。“唐、宋律私輒用財者十匹笞十,十匹加一等,罪止杖一百。”[7]當然,家屬也可以在滿足條件下處分家庭財產:(一)家長在化外以及阻隔兵戈可以不請示家長;(二)在滿足前一條件下請求州縣給予文牒以憑交易。在羅馬,則“父有權取得其子的全部取得物,并享有契約的利益而不牽扯到任何賠償責任”。家屬的財產行為無效,即使該行為對家長有利,或者甚至是在家長的授意下完成的。“家屬如果為法律行為,他們與奴隸一樣,只能使家長增加利益,而不能使家長負擔義務或者蒙受損失,不得以自己的名義做市民法上的債務人。如果家屬因訂立契約而負有債務,這種債務只能是自然債務,不受法律保護。”“家長對家屬和第三人所訂的契約,只享受利益而不須承擔義務,即便契約是經家長同意所訂,也是如此。”[8]
三、家長權的歷史沿革
家長權的產生原因,一方面是出于自然倫理。子女對于養育自己的家長是有一種自然的仰慕。在精神上,家長相比子女有著更豐富的社會經驗和知識;物質上,家長的身體和物質生產能力可以為子女的成長提供相關的物質保障。“當社會處在體力或者智力都有特殊價值的時候,就會產生一種影響,傾向于使家父權限于確實有才干水平的人。”[9]另一方面,是來源于人類群體生存的需要。人類只有結成群體才得以獲得生存,氏族、家族、家庭也就由此產生。由于生產生活圍繞群體進行,群體的活動也相應地要求生產的效率。如今被認可的對推動生產效率最有效的兩種方式——技術創新和制度改革——在古代社會被認為是不可能,則人類群體只能選擇第三種方式——集中的意志,即由單個個體指導群體活動。專制的個體選擇與前述的子女對家長(男性)的仰慕結合起來,家庭范圍內的家長權由此產生。至于上述原因導致的行為的具體產生時間,不可考證,可以得知的只有家長權被明文規定于法典之中的時間,羅馬是公元前五世紀中葉,中國是漢朝,大約在公元前兩世紀。
家長權的消亡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但羅馬家長權的消亡是由于社會內力的“消化”,而中國則歸之于外力的“沖擊”。羅馬建國以來,經濟上一直是奴隸主商品經濟占據主導。而商品經濟追求的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其核心理念是契約精神,指導原則是誠實信用,基本要求是效率。建立共和國后的羅馬經過多年對外戰爭,國家疆域不斷擴張,戰爭掠奪的大批戰俘與戰利品使羅馬社會占有了大量廉價勞動力及原材料。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的條件已然具備。而羅馬家長權中的家長與家屬地位的不平等、家屬處分家庭財產的無效力等內容,無不與這個社會的基礎經濟制度產生矛盾。再加上希臘斯多葛派哲學的廣泛傳播,人文主義思想深入人心,以及國家機制的完善,國家對社會生活的干預能力增強。為了解決這種矛盾,羅馬頒布多項法律削弱家長權。公元前89年,《龐泊亞法》取消祖父對孫子,丈夫對妻子,家長對兒媳的生殺權。特拉雅努斯帝在位時,禁止虐待子女,違者勒令家長將其解放,使之脫離家長權。公元二世紀,家長對家屬僅有一般懲戒權,重罪必須經過法院判決。家長同時開始承擔更多的法律義務,如“法律規定家長有義務為出嫁的女兒設定嫁資”,“家長在處分遺產時,要給家屬留有特留份”,“設定遺囑逆倫訴,對家長的遺囑自由予以限制。”家長對家庭財產的控制力度也逐漸放松,但相比于家長的懲戒權,速度緩慢且不徹底:家屬只可使家長獲得利益而不可使其承擔義務的原則被羅馬的法官修正,部分家屬與他人簽訂的財產性契約,家長也要受其拘束并承擔責任。家屬可以擁有自己的財產。四種家屬獨立財產被羅馬法律認可:家長授予的特有產,軍役特有產、準軍役特有產、外來特有產。但對上述財產,家屬并不享有完整的物權。第一種特有產,家屬只有使用收益權而沒有所有權。第二種和第三種特有產的所有主體特定,僅限于羅馬軍團的軍人、隨君士坦丁遷都的高級官吏、律師與教士。第四種財產所有權歸家屬而用益權歸家長,且家長的這種用益物權較一般用益物權為優。對于這種現象,英國法學家梅因評論道:“家父權的真正難理解之處實在不在這一方面(子只可以使父獲得利益),而是在父的這些財產特權被剝奪的如此之慢。”[10]
古代中國的家長權自設立后不但沒有削弱,反而一直增強。這種逆歷史潮流的趨勢的產生,源自于中國獨特的社會制度。(一)小農經濟模式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家長權治下的家庭能夠在最大限度上提高家庭的生產力,以維持小農經濟的穩定。而小農經濟的封閉性可以維持家長權在社會中的主要地位。(二)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的特征是“家國一體”。“(中國)國家的產生并未以氏族組織的瓦解為代價,而是相反,保留了原有的血緣關系,把氏族內部的親屬關系直接轉化為政治國家的組織方式。”[11]這樣,國家的政治制度是仿照家庭制度建立的,君權是仿照家長權設立的,君權理論來源于家長權理論。(三)儒家思想自漢代以來,一直是中國社會思想的主流,而儒家思想又歷來強是調家庭人倫的。它為家長權的存續正當性提供了最為完整的理論和法律支持。先秦時《論語》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也。”漢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成為不可質疑的“王者之綱”。唐朝《唐律疏義》則將“不孝”列入“十惡”重罪。宋代理學,家長權提升被到哲學思辨的高度,“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成為天地之本——天理。元代,出現了故事集《二十四孝》,其包括“臥冰求鯉”“郭巨埋兒”“嘗糞憂心”等二十四個宣揚家屬服從家長到極致的故事。得到了這三方面的支持,家長權根植于中國傳統社會內部,除非變更社會性質,其穩定性幾乎不可被撼動。但古代中國封建體制已經成熟到喪失了任何創新的活力,變更社會性質只能期待于外力沖擊。因此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西方工業文明被強行輸入中國,中國的家長權才開始逐步瓦解。
四、家長權的性質
在第一部分的家長權的定義中,筆者認為家長權的性質是一種權力(power),而非一種權利(right)。本部分的討論重點是為何認定家長權為一種權力。
筆者認為:權力,是特定個體基于特殊地位對不特定個體產生的影響力。權利,則是不特定個體基于法律授權或合同約定所享有的,在特定領域內的對特定或不特定個體的行為自由。其具體的差異主要有:(一)權力僅為少數人基所擁有,如君權僅為一國國君所擁有;權利為社會全部成員普遍享有或者可得到,如每個公民都享有生命權、健康權、選舉權,可以因侵權而獲得損害賠償請求權。(二)權力來源于特定的地位或者身份,由某種強力作為支持;權利只可以來自于法律的授權或合同的約定,且均由法律得以保障。(三)權力內容寬泛而模糊,沒有特定的行使范圍。擁有權力的個體似乎可以影響行為對象的全部行為,行為對象也甘于承認這種影響;權利的內容由相關的法律明文規定或合同基于合意的約定,行使范圍相對特定明確,超越這個界限權利不再發生效力。(四)權力與權利最顯著的區別,是權力不具有對等性而權利卻具有對等性。權力行使人僅享有權力而不承擔對等義務,權利行使人行使權利的同時還要承擔相應義務。這是劃分權力和權利的關鍵。
通過以上權利與權力的辨析,結合前面第一、第二部分對家長權內容的研究,可以得出“家長權是一種權力”的結論:(一)家長權只為“家庭中上無父系直系親屬的成年男性”所享有,主體為特定的少數人;(二)家長權基于家長地位獲得,法律只是對這種既存事實進行確認而不是授權;(三)家長權的內容寬泛,涉及家屬的人身行為、家庭的財產、家庭宗教祭祀活動;(四)家長權不具有對等性,家屬只可以使家長獲得利益而不可其承擔義務。
[參考文獻]
[1]周枏.羅馬法原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2]周枏.羅馬法原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3]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2.
[4]<十二表法>.
[5]<史記‐五七‐李斯列傳>.
[6]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2.
[7]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12.
[8]周枏.羅馬法原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9]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2(第一版).
[10]梅因.古代法[M].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2(第一版).
[11]江兆濤.中國古代法與羅馬法中家長權之比較研究[J].法治與社會,2008.1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