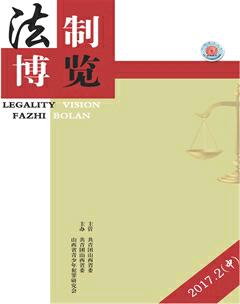監(jiān)獄法第47條是否違憲相關(guān)問題研究
摘要:針對相關(guān)學(xué)者對《監(jiān)獄法》第47條涉嫌違憲問題的研究,通過對監(jiān)獄工作的發(fā)展歷程、監(jiān)獄相關(guān)法律法規(guī)和憲法出臺的特定時間點的梳理,對監(jiān)獄工作性質(zhì)和對罪犯信件檢查的法理分析,得出了《監(jiān)獄法》并不當(dāng)然違憲的結(jié)論,并提出了進(jìn)一步完善釋法和立法工作的建議。
關(guān)鍵詞:監(jiān)獄法;通信;罪犯;違憲;規(guī)范評價
中圖分類號:D926.7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05-0077-03
作者簡介:姚學(xué)強,北京市柳林監(jiān)獄辦公室,主任科員,工程師,中國人民大學(xué)法學(xué)院,2015級法律碩士研究生。
《監(jiān)獄法》第47條規(guī)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yīng)當(dāng)經(jīng)過監(jiān)獄檢查。監(jiān)獄發(fā)現(xiàn)有礙罪犯改造內(nèi)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jiān)獄的上級機(jī)關(guān)和司法機(jī)關(guān)的信件,不受檢查。”作為一項限制或剝奪公民權(quán)利的公權(quán)力,其必須有相應(yīng)的憲法授權(quán),否則必然涉嫌違憲。《憲法》第40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hù)。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jī)關(guān)或者檢察機(jī)關(guān)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qū)νㄐ胚M(jìn)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憲法》第40條是《監(jiān)獄法》第47條的授權(quán)來源。有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監(jiān)獄法》第47條涉嫌違憲,問題在于主體不合憲——監(jiān)獄不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理由不合憲——監(jiān)獄理所當(dāng)然地檢查信件并不是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對象不合憲——不能不加區(qū)分的凡是罪犯的信件都進(jìn)行檢查。[1]筆者研究認(rèn)為:《監(jiān)獄法》第47條雖然從法條上看涉嫌違憲,但如果結(jié)合當(dāng)時的特定歷史和《憲法》、《監(jiān)獄法》的發(fā)展演化來看,《監(jiān)獄法》第47條并不當(dāng)然違憲。我們需要在尊重現(xiàn)行法律的前提下,針對實踐中出現(xiàn)的問題,有針對性地進(jìn)行立法解釋,或是進(jìn)一步進(jìn)行相應(yīng)的憲法修正或監(jiān)獄法修正,才能更好地推進(jìn)相關(guān)法律的實施和完善。
一、監(jiān)獄是否屬公安機(jī)關(guān)范疇的分析
(一)現(xiàn)行憲法實施時,監(jiān)獄恰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改造條例》(1954年8月26日政務(wù)院第222次政務(wù)會議通過,1954年9月7日政務(wù)院發(fā)布,下稱《勞改條例》)第2條、第3條明確了勞動改造機(jī)關(guān)包括關(guān)押已決犯的監(jiān)獄、勞動改造管教隊,關(guān)押未決犯的看守所和關(guān)押少年犯的少年犯管教所;第6條則明確了勞動改造機(jī)關(guān)受人民公安機(jī)關(guān)的領(lǐng)導(dǎo),受各級人民檢察署的監(jiān)督,在有關(guān)司法業(yè)務(wù)上受各級人民法院的指導(dǎo)。
1983年9月26日,根據(jù)“(83)國函字第204號”《國務(wù)院關(guān)于將公安部勞改局、勞教局及其編制劃歸司法部的通知》決定:“將公安部的勞改局、勞教局及其編制一百一十人劃歸司法部,全國勞改、勞教工作歸司法部領(lǐng)導(dǎo)。”由此,監(jiān)獄、勞動改造管教隊就不再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管轄而歸屬司法行政機(jī)關(guān)管轄,但其關(guān)押改造已決犯的職能未變。
現(xiàn)行《憲法》于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1982年12月4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公布施行。從時間節(jié)點上看,現(xiàn)行《憲法》通過并施行時及之前近三十年間,監(jiān)獄恰受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是公安機(jī)關(guān)內(nèi)部承擔(dān)已決犯關(guān)押改造的部門。從《憲法》特別授權(quán)的指向上看,其所指的檢查信件的主體當(dāng)然是包括監(jiān)獄、勞改管教隊、看守所等在內(nèi)的公安機(jī)關(guān)。
1983年監(jiān)獄由公安機(jī)關(guān)回歸司法行政機(jī)關(guān)后,一方面,監(jiān)獄執(zhí)行刑罰、關(guān)押改造罪犯的職能未變,職能需要職權(quán)的保障;另一方面,國務(wù)院(政務(wù)院)對內(nèi)部機(jī)構(gòu)的調(diào)整,不應(yīng)反過來要求相關(guān)法律尤其是憲法做出針對性調(diào)整。《憲法》特別授權(quán)中所指的公安機(jī)關(guān)既然在立法階段和法律生效時均未排除監(jiān)獄,那么監(jiān)獄延續(xù)既有的憲法授權(quán)就具有正當(dāng)性。
(二)國務(wù)院、公安機(jī)關(guān)都明確賦予了監(jiān)獄對罪犯信件的檢查權(quán)
國務(wù)院(政務(wù)院)通過的《勞改條例》第58條規(guī)定:“犯人發(fā)受書信,應(yīng)當(dāng)經(jīng)過勞動改造機(jī)關(guān)檢查。未決犯發(fā)受書信,由原送押機(jī)關(guān)或者審判機(jī)關(guān)檢查,或者委托勞動改造機(jī)關(guān)檢查。如果發(fā)現(xiàn)有串通案情或者妨礙對犯人教育改造的情形,應(yīng)當(dāng)扣留。”1982年2月1日公安部通過的《監(jiān)獄、勞改隊管教工作細(xì)則(試行)》第71條第1款規(guī)定:“犯人發(fā)受的一切信件,一律經(jīng)過干部檢查,如果發(fā)現(xiàn)有妨礙犯人改造和泄露勞改單位機(jī)密的信件,應(yīng)予扣留,并對犯人進(jìn)行教育。”
根據(jù)1954年《憲法》第90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hù)。”和1978年《憲法》第45條:“公民有言論、通信、出版、集會、結(jié)社、游行、示威、罷工的自由,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quán)利。”的規(guī)定,《勞改條例》和《監(jiān)獄、勞改隊管教工作細(xì)則(試行)》相關(guān)條款顯然是違憲的。但同時也突顯了1982年《憲法》第40條特別授權(quán)的指向性。在新中國法制相對不完善的初期,先有實務(wù)部門的實踐,再由國務(wù)院的行政法規(guī)上升為法律,甚至推動憲法的修正,是法制建設(shè)的必由之路。
由此,1994年12月29日通過的《監(jiān)獄法》,通過相關(guān)條文的明確,使之前的實踐和行政法規(guī)上升為法律,也是對監(jiān)獄擁有對罪犯信件檢查權(quán)的憲法特別授權(quán)的進(jìn)一步法律明確,同時也隱含著全國人大常委會的一個態(tài)度,即監(jiān)獄雖然不再由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但并不影響其歸屬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時所獲得的憲法授權(quán)的效力。
(三)監(jiān)獄不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的現(xiàn)實需要相關(guān)的立法解釋
在建國初期法制、司法體制、國務(wù)院組織機(jī)構(gòu)都不完善,需要不斷探索、調(diào)整的情況下,監(jiān)獄先是受司法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后改為公安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最后又改為司法機(jī)關(guān)領(lǐng)導(dǎo),這種反復(fù)性必將給司法實踐帶來諸多問題,也需要相關(guān)法律的修正來完善。比如,195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條例》第4條規(guī)定:“人民警察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和地方各級公安機(jī)關(guān)的領(lǐng)導(dǎo)。人民警察的編制和管理機(jī)構(gòu),由國務(wù)院另行規(guī)定。”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廢止了《警察條例》并在第2條第2款規(guī)定:“人民警察包括公安機(jī)關(guān)、國家安全機(jī)關(guān)、監(jiān)獄、勞動教養(yǎng)管理機(jī)關(guān)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的司法警察。”這是從人民警察的管理上,明確監(jiān)獄與公安機(jī)關(guān)的不同。
根據(jù)《監(jiān)獄法》第10條“國務(wù)院司法行政部門主管全國的監(jiān)獄工作”的規(guī)定,國務(wù)院如再對監(jiān)獄的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進(jìn)行調(diào)整,則不再是國務(wù)院可以決定的了,而是需要《監(jiān)獄法》的授權(quán)才行,但也因此法律上明確了監(jiān)獄不再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正如相關(guān)學(xué)者所研究的那樣,僅從條文上看,《監(jiān)獄法》第10條和《憲法》第40條構(gòu)成了《監(jiān)獄法》第47條主體不合憲的證據(jù)鏈。因此,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有必要進(jìn)行立法解釋、司法解釋或是修憲、修法。
二、監(jiān)獄檢查罪犯信件的正當(dāng)性分析
(一)監(jiān)獄安全穩(wěn)定是否屬于因國家安全的分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第二條規(guī)定:“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quán)、主權(quán)、統(tǒng)一和領(lǐng)土完整、人民福祉、經(jīng)濟(jì)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于沒有危險和不受內(nèi)外威脅的狀態(tài),以及保障持續(xù)安全狀態(tài)的能力。”不管是政治視角下監(jiān)獄是國家暴力機(jī)器的定位,還是法治視角下監(jiān)獄是國家的刑罰執(zhí)行機(jī)關(guān)的定位,監(jiān)獄都需要以法律賦予的國家強制力為后盾,通過對罪犯人身自由的限制甚至剝奪來執(zhí)行刑罰和對個體的懲罰,而這種刑罰執(zhí)行功能只能是嚴(yán)格限制的國家公權(quán)力行為,而不是監(jiān)獄作為一級司法行政組織的部門行為,更不是監(jiān)獄警察的個人行為。襲警、暴獄、越獄等威脅到監(jiān)獄警察個人人身安全、威脅到監(jiān)獄的安全以及威脅到社會的安全,其所侵犯的根本指向只能是監(jiān)獄和監(jiān)獄人民警察所代表的社會利益與國家安全。同樣,罪犯的自傷自殘自殺,侵犯他犯權(quán)益的獄內(nèi)再犯罪,以及與家屬及社會人員謀劃實施的其他違法犯罪行為,以及向外界傳遞的關(guān)于監(jiān)獄的各種不應(yīng)傳遞的信息等,都屬于威脅到人民福祉、監(jiān)獄安全等的國家安全范疇。而這種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普通公民需要被公安機(jī)關(guān)列為犯罪嫌疑人時才能受到通信的限制和檢查,而罪犯是已經(jīng)從犯罪嫌疑人轉(zhuǎn)為法院判定的罪犯,不管是基于對以前犯罪的懲罰還是基于對以后犯罪的預(yù)防,都需要伴隨刑罰執(zhí)行施以更嚴(yán)格的管控措施。尤其是從預(yù)防犯罪的監(jiān)獄職能角度看,通過信件的檢查來發(fā)現(xiàn)違法犯罪線索,預(yù)防犯罪,維護(hù)國家安全具有法律的當(dāng)然性。
(二)清查余罪漏罪是否屬于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的分析
1982年憲法之所以增加賦予公安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因特定需要和依法律規(guī)定檢查信件的權(quán)力,從而打開公權(quán)力合法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私權(quán)利的口子,反映出我國憲法一方面在不斷地推進(jìn)通過憲法明確保障人權(quán)的進(jìn)程,使人權(quán)的各種具體內(nèi)容在憲法中予以明確的確認(rèn);另一方面,也考慮到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依法治國初始階段打擊和預(yù)防犯罪的特殊需要,從而使保障人權(quán)不致成為掣肘相關(guān)部門打擊和預(yù)防違法犯罪的不可逾越的障礙,不致成為違法犯罪人員以個人權(quán)益為由逃避應(yīng)受懲罰的絕對保護(hù)傘。
《監(jiān)獄法》在明確監(jiān)獄是刑罰執(zhí)行機(jī)關(guān)的功能定位的同時,也賦予了監(jiān)獄懲罰和改造罪犯,預(yù)防和減少犯罪的職能。從懲罰罪犯的角度看,由監(jiān)獄對罪犯實施的刑罰是自由刑或監(jiān)禁刑,是將罪犯監(jiān)禁于特定場所,剝奪其人身自由的刑罰。有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狹義的自由刑是指國家為剝奪或限制犯罪人正常生活和交往的需要而設(shè)置的懲罰性障礙。[2]在監(jiān)禁的條件下,罪犯作為特殊公民,其一般公民所具有的正當(dāng)權(quán)利雖未被剝奪,卻必然受到較大的限制,即使實體權(quán)利不受限制,實現(xiàn)實體權(quán)利的過程也要受到限制,這種限制,這種身不由己,才是自由刑使罪犯感受到懲罰的所在。從改造罪犯、預(yù)防犯罪的角度看,監(jiān)獄警察需要對罪犯的主觀方面的了解,雖然不能把所有罪犯都看作有余罪漏罪或再犯罪的嫌疑人,但改造罪犯、預(yù)防犯罪的指向是每一名罪犯,這是罪犯不同于一般公民非因明確證據(jù)不能定為犯罪嫌疑人的區(qū)別所在,所以通過信件檢查清查所有罪犯身上的余罪漏罪,排查所有罪犯獄內(nèi)犯罪的思想苗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結(jié)為追查刑事犯罪的范疇。
(三)檢查和扣留信件對罪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侵犯需要正確認(rèn)識
檢查信件侵犯的主要是通信秘密,扣留信件侵犯的才是通信自由。1994年《監(jiān)獄法》第四十七條規(guī)定:“罪犯在服刑期間可以與他人通信,但是來往信件應(yīng)當(dāng)經(jīng)過監(jiān)獄檢查。監(jiān)獄發(fā)現(xiàn)有礙罪犯改造內(nèi)容的信件,可以扣留。罪犯寫給監(jiān)獄的上級機(jī)關(guān)和司法機(jī)關(guān)的信件,不受檢查。”相對于1954年《勞改條例》,《監(jiān)獄法》對罪犯的通信權(quán)予以明確,并對監(jiān)獄檢查罪犯信件進(jìn)行確權(quán),同時變更原應(yīng)當(dāng)扣留為現(xiàn)可以扣留,并對可以扣留的情形從“發(fā)現(xiàn)有串通案情或者妨礙對犯人教育改造”變更為“發(fā)現(xiàn)有礙罪犯改造內(nèi)容”,變更后的有礙罪犯改造不再局限于教育改造,而是擴(kuò)展至包括串通案情在內(nèi)的監(jiān)管改造、改造罪犯主要形式的勞動改造和更廣泛意義上的教育改造。
從相關(guān)條款上看,相對于通信秘密,通信自由受到更大的保護(hù),除非涉及到法條規(guī)定的情形,通信自由不受限制。而從通信秘密上看,一方面,監(jiān)獄在獲得罪犯信件檢查的權(quán)力同時,也負(fù)有不將通信內(nèi)容用于獄情分析和獄內(nèi)偵查以外工作環(huán)節(jié)的保密義務(wù);另一方面,在信件必然受到檢查的情況下,罪犯與親友通信的內(nèi)容,也必然經(jīng)過了寫信人的“涉密自審”,這是與通常意義上的侵犯公民通信秘密案件中被侵犯人不知信件將被查看、不知誰查看以及不知是否會更大范圍擴(kuò)散不同,這是相關(guān)人知情、可控的。因此,監(jiān)獄對罪犯信件的檢查跟一般的侵犯公民通信秘密有著實質(zhì)的區(qū)別。
三、對相關(guān)法條完善的建議暨結(jié)語
從前文分析可以看出,監(jiān)獄對罪犯信件的檢查,具有與憲法做出特別授權(quán)的意圖相一致的正當(dāng)性。正當(dāng)性才是憲法授權(quán)的關(guān)鍵,才是可以進(jìn)行釋法或修憲修法的關(guān)鍵。從英美等國外的監(jiān)獄實踐來看,對罪犯信件的檢查也屬于通行做法。[3]因此,我們不能從法條的字面意義上得出涉嫌違憲的結(jié)論,更不能動輒質(zhì)疑甚至否定經(jīng)過歷史檢驗的實踐做法,而應(yīng)運用規(guī)范評價論的原理找尋其合憲的論據(jù),并對因行政管理的變動、立法活動對相關(guān)問題的重視不夠,而導(dǎo)致法條的含義不夠清晰等,提出相應(yīng)的立法解釋或法律修正建議。
一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進(jìn)行立法解釋。按照《憲法》第67條第一款、第四款規(guī)定,對《憲法》第40條、《監(jiān)獄法》第47條開展解釋憲法、解釋法律工作。釋明因特殊歷史時期監(jiān)獄領(lǐng)導(dǎo)機(jī)關(guān)的變更,而導(dǎo)致監(jiān)獄行政管理上不再屬于公安機(jī)關(guān),但并不影響監(jiān)獄行使刑罰執(zhí)行等類似于公安機(jī)關(guān)的屬性和職能;同時,監(jiān)獄作為刑罰執(zhí)行機(jī)關(guān),其維護(hù)監(jiān)獄安全穩(wěn)定、防范和打擊獄內(nèi)犯罪和預(yù)防再犯罪的活動均屬于維護(hù)國家安全的范疇。
二是由全國人大進(jìn)行修憲并全國人大常委會進(jìn)行《監(jiān)獄法》修正。在《憲法》修正中,將《憲法》第40條修正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hù)。除因國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機(jī)關(guān)、國家安全機(jī)關(guān)、檢察機(jī)關(guān)、刑罰執(zhí)行機(jī)關(guān)各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qū)νㄐ胚M(jìn)行檢查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另外,由于“信件”的范疇比“通信”的范疇要小,而監(jiān)獄實踐中對出于安全的需要不僅要檢查罪犯的傳統(tǒng)信件、短信平臺收發(fā)的短信息,更多的是對親情電話、會見的監(jiān)聽,因此,《監(jiān)獄法》第47條應(yīng)采用《憲法》第40條“通信”一詞,以涵蓋傳統(tǒng)信件、較少用的手機(jī)短信息和電子郵件,以及電話、會見等所有通信方式。
三是加快推進(jìn)刑罰執(zhí)行體制改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執(zhí)行法》的出臺。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推進(jìn)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完善刑罰執(zhí)行制度,統(tǒng)一刑罰執(zhí)行體制。”對此,很多學(xué)者都進(jìn)行了專題研究。[4]筆者主張國家成立刑事執(zhí)行院,與法院、檢察院并列,并由全國人大出臺《刑事執(zhí)行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共同構(gòu)成完整的刑事法律體系,從而使監(jiān)獄等刑罰執(zhí)行部門在對相對執(zhí)行人權(quán)利的限制或剝奪上有更完備、嚴(yán)謹(jǐn)、明確的憲法授權(quán)和法律依據(jù)。
[參考文獻(xiàn)]
[1]張紅林.關(guān)于監(jiān)獄法第47條涉嫌違憲的探討[J].改革與開放,2011(22).
[2]賴早興,賈健.論自由刑中的“自由”及其演化[J].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8(4).
[3]吳宗憲著.西方監(jiān)獄學(xu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1).
[4]賈曉文,張婧.統(tǒng)一刑罰執(zhí)行體制研究觀點綜述[J].中國司法,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