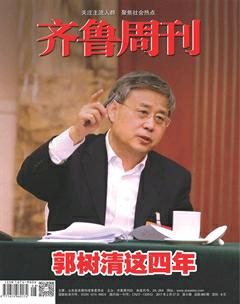“代孕”之殤
海欣
2017年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發題為《不孕不育成難題 代孕是否可放開》的文章引發熱議。
代孕爭議的本質不是醫療問題,也不是技術問題,是更深層次的法律、倫理和社會問題。只有當女性的身體不再被等同于工具,這項討論才有了最大程度的人性意義。 (本專題58-61頁)
誰在出租子宮?
凱特37歲,事業有成,卻依然單身。當有一天她發現會議室的所有同事都幻化成含著奶嘴撒嬌的寶寶時,她明白,自己想要一個孩子了。不幸的是,醫生告訴她:她受孕的幾率只有百萬分之一。按捺不住母性的凱特最終通過代孕中介找到了一位素不相識的女人替她懷孕,為此凱特向她支付了大量的美元。
這是好萊塢片子《代孕媽媽》里的情節,電影中戲劇化的一幕正在中國悄然上演。代孕,這個詞正從“嬰兒交易”“肉體買賣”等臭名昭著的名稱中解脫出來,出現在電視節目、報紙新聞中,呈現在公眾面前。
有人怒罵“代孕意味著道德的流產”,有人呼吁“倫理最終要從人類的幸福出發”。在商業、倫理和法律之間,代孕中介尚處于灰色地帶。
小孔今年32歲,離異,有一個四歲的兒子。為了賺錢她瞞著父母來到武漢,在經歷了體檢、移植、持續數月服用雌激素、注射孕激素后,進入孕后期的小孔獨自居住在武漢的一所高層公寓里,有專用保姆陪同并照顧生活起居,按照客戶的要求每天喝孕婦奶粉、聽胎教音樂、散步、午休。生產之后,她會帶著相當于她家庭年收入18倍的約15萬元人民幣“打工”所得回到家鄉,與父母一起照顧兒子成長,并計劃開一家家政公司。而一對來自河南的夫婦將迎來一個他們企盼十余年的孩子。小孔說:“他們好像是在銀行工作的,做了十年的試管嬰兒,還通過輸卵管,但一直沒成。”
有數據顯示,我國實際不孕不育發生率超過15%。其中部分夫妻因為身體原因,無法自己懷孕。隨著生殖輔助技術的發展,代孕成為解決問題的一條途徑。
但也有趨勢表明,新富的都市女性出于保護工作前景、害怕體形走樣等目的,而找人替生孩子。
寧麗(化名)的丈夫是私企老板,她成功找到了一名剛畢業的女大學生做代孕者,理由是怕疼,怕影響身材。她不愿意因為懷孕影響自己目前的工作,更何況她還有升遷的機會。
另外一種情況則出現在已經有一個孩子的新富階層家庭。據北京某代孕網站負責人高先生透露,很多新富階層的家庭由于還想要一個孩子,但又憚于國策,所以找人代孕,以掩人耳目。由于中國法律禁止代孕,這些有經濟實力的夫妻,會轉而尋求海外代孕。
從國際情況來看,不同國家、地區,文化價值觀不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關于代孕的政策也不盡相同。印度是世界第二人口大國,但允許代孕,而且是商業代孕,明碼標價。出生率偏低的俄羅斯也允許代孕。在歐洲,英國允許的是“親情代孕”,如姐姐替妹妹懷孕,母親替女兒懷孕等,這種“非營利性代孕”,機構和個人不能以此謀取利益,國家對代孕有價格指導。法國也有類似的代孕指導價。美國國內對代孕也有很大的爭議,目前有26個州允許代孕,但這26個州的代孕政策也各不相同。由于在美國捐精捐卵均被允許,還可以為嬰兒選擇性別,不少人尋求通過胚胎基因診斷技術“定制”一個金發碧眼的嬰兒。
代孕“紅與黑”
1988年3月10日,中國內地第一例試管嬰兒誕生于北醫三院。此后,試管嬰兒技術迅速普及應用。目前,全國每個省都有生殖中心,他們能夠制造的試管嬰兒總量相當可觀。
但是,2001年8月,衛生部出臺《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嚴格禁止代孕母親的試管生產,這項新業務胎死腹中。直到今日,它仍是醫學領域的禁區,只是逐漸轉向了“地下”交易。
近30年來,試管嬰兒、人工授精等輔助生育技術的發展,和高達15%至20%的不孕不育率,造就了一個“嬰兒市場”的發育。在中國,用互聯網搜索就可以找到上百家代孕中介網站。
對于“代孕”商業行為本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德博拉·斯帕爾(DeboraL.Spar)2006年出版了一本書《嬰兒生意》,專門探討了輔助生育市場的現狀。在接受采訪時,她表示,最讓她吃驚的是:在她所接觸過的眾多行業里,這是第一個很明顯存在買賣雙方,而且有金錢交易,但是卻沒有人承認他們正在從事商業交易的行業。
在AA69代孕網上,“代孕媽媽”的級別被分為A—H級:A級標準最低,初中學歷,容貌一般,待遇4萬,到了H級,要求有本科學歷,容貌較好,待遇可以提到10萬元以上。這讓很多人覺得和在超市里挑選商品并無二致。
“如果經濟上不困難,沒有誰愿意做這個。畢竟有10個月你不能見到家人。一位山東聊城的代孕媽媽表示,她認識的大部分代孕媽媽都出于經濟上的無奈。
這是一次拿身體換金錢的冒險。在這場復雜的博弈中,金錢、道德、倫理、法律、醫學等一系列問題的相互糾結,考驗著買賣雙方的情感與理智。
廣州醫科大學第三附屬醫院生殖醫學中心主任劉見橋表示,代孕行為屬于地下交易,其操作者的專業水平、從業經驗等根本無法保證,這就大大增加了手術的風險。
此外,因為代孕產生的法律糾紛和官司,也層出不窮。2015年10月,南方日報曾報道,有代孕媽媽生下雙胞胎,親子鑒定結果顯示,孩子與委托代孕的夫妻沒有任何血緣關系,矛頭指向混亂的代孕產業鏈,最終這對雙胞胎“砸”在中介手中,無人認領,命運堪憂。
在社會倫理層面,誰才是孩子的母親?這是代孕面臨的諸多質疑中的一個。
有的國家規定“分娩者即母親”,有的地方則承認遺傳學上的母親,而代孕嬰兒的母親的認定,既不同前者又不同后者,它更符合一個“契約上的母親”的定義。但在沒有法律規定的情況下,任何契約都有可能是一紙空文。倫理上的混亂帶來了無盡的爭議。
在《鳳凰衛視》的“一虎一席談”節目中,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新聞研究所研究員時統宇極力反對代孕,他認為這種明碼標價的商業,是女性子宮的工具化,代孕中介暴露了赤裸裸的商業和產業目的。
即使開放如好萊塢,電影《代孕媽媽》里最后也回避了“代孕”沉重的倫理爭論,編劇讓故事回到了常規:代孕媽媽懷的其實是她自己的孩子,而幾乎不可能懷孕的凱特也奇跡般地產下了小孩。“代孕”在這里只是喜劇元素和商業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