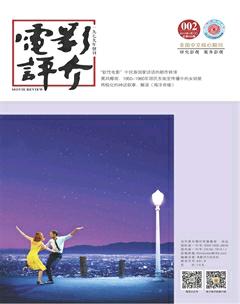當文學經典遇到電影
李楠 吳思萌
經典對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它給人以思想、給人以力量、給人精神上的指引,它穿越古今、超越時空,直至現在它所散發出的力量仍能在人們心中發芽。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電影傳入中國,無論是文學、歷史領域,還是哲學、政治領域,很多經典都被改編為電影呈現在觀眾面前,但在眾多經典作品中,文學經典與電影的關系最為密切,電影的情節設置、人物形象、審美特質等方面都受到文學經典的影響,電影改編也多以文學經典為主。同時,電影人也以其獨特的視角和拍攝方式詮釋經典。九十余年的電影發展歷程中,文學經典的電影改編版本在聲效、色彩圖像等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其改編方式也由忠實原著到戲仿、大話。文學經典在電影影響下廣為傳播的同時,其本身的主題和價值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構與顛覆,這樣的改編現狀不得不引起電影人和觀眾們的反思。
一、 電影版《西游記》的改編特征
伴隨著電影拍攝技術的不斷進步,文學經典的改編版本也由最初的無聲、黑白式的膠片版,逐步發展為融合特技效果、立體聲響、斑斕色彩的數碼版,以及更具體驗感的三維立體版。其改編數量更是不勝枚舉,單從“四大名著”的電影改編來看,20世紀以來其改編成果頗豐,其中,《西游記》更被稱為“史上最強IP(Intellectual Property,知識產權)”。據統計,1926年至2012年間,《西游記》的影視、動畫改編作品有80余部,2012年至今也在推出新的改編版本,包括《西游降魔篇》(2013年)、《西游記之大鬧天宮》(2014年)、《西游記之大圣歸來》(2015年)、《西游記之孫悟空三打白骨精》(2016年)等。
在眾多依據《西游記》改編而成的電影作品中,不僅可以看到電影技術的變革,還能看到電影改編對文學經典態度的變化。早期作品如1966至1975年間由香港邵氏公司改編的版本,《西游記》《鐵扇公主》《盤絲洞》《女兒國》《紅孩兒》,人物、情節、主旨等方面都是在原著的基礎上演繹而來,而從1994-1995年間拍攝的《大話西游之月光寶盒》《大話西游之仙履奇緣》到近年來的一系列版本都是以戲仿、“惡搞”的方式解構與消解經典。經典在電影中不再是典范的、權威的文本,改編也不是在經典文本基礎上的演繹,而是一個借經典外殼而做的新文章。
在大話、戲仿經典的電影中,《西游記》因其本身的娛樂性、通俗性和神魔性特質也最易被改編者接受,因此在眾多改編版本中《西游記》的改編最具代表性,這些惡搞、戲仿的改編版本至少具有以下三個特征:
(一)娛樂化。大眾文化時代下的改編不再將經典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典范,經典人物在鏡頭里走下了神壇,走向了“非經典”。文本也不再是“由一個高高在上的生產者——藝術家所創造的高高在上的東西(比如中產階級的文本),而是一種可以被偷襲或被盜取的文化資源。文本的價值在于它可以被使用,在于它可以提供的相關性,而非它的本質或美學價值”[1]的確,經典的價值在一些電影改編版中早已不再具有導向意義,更重要的作用是作為一個為電影提供資源和文本的客體,一個不需要去深入挖掘的客體。《大話西游》中,《西游記》只是起到一個線索的作用,一個只要聽到名字就能聯想到人物角色的作用,電影在情節和主旨上完全另起爐灶。在時空來回穿梭中蜘蛛精、白骨精、牛魔王齊上映,孫悟空轉世的至尊寶與白骨精轉世的紫霞仙子上演了一場前世今生的愛戀,唐僧也變為喋喋不休、絮絮叨叨的人物。這一類型的電影改編以篡改人物、拼接劇情的方式,在一派熱鬧中娛樂了經典,也在追求感官刺激的快感中顛覆和消解了經典建立的話語權。
(二)淺表化。經典是厚重的,是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經典中蘊涵了無盡的闡釋空間,其人物與情節都有豐富的內涵。經典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經歷了千百年來的考驗而來到我們身邊。當代的大話類的電影改編則不同,它們更關注當下的、直觀的內容,正如美國學者丹尼爾·貝爾所說:“當代文化現在正在變成一種視覺文化,而不是一種印刷文化”“目前居統治地位的是視覺觀念。聲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組織了美學,統帥了觀眾。在一個大眾社會里,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2]在前視覺時代,語言是文學作品得以建構的基礎,表達約定俗成的概念,也表達人類豐富的思想情感,當語言文化轉變為視覺文化,文學作品中的思想與意象都變為固定的、直觀的表意符號,在一定程度上使經典更簡單直接的表現在讀者面前,但隱含在經典深處的意蘊便難以被挖掘出來。《西游記》被稱為“明代四大奇書”,它也是一部較為特殊的著作,它以神魔為寓意,并在嬉笑怒罵中講述真理。一系列大話作品為迎合消費者心理,以一種簡單直白的處理方式去改編經典,這樣的方式也就難以傳遞出西游故事背后的真諦。
(三)速食化。文學作品或因情感宣泄而來,或因載道之用,它們無不是作者仔細推敲、字斟句酌的結晶,后又經歷代接受不斷傳播而來,每一部經典都是作者嘔心瀝血的成果,僅《紅樓夢》便經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才初步成稿。與前消費時代的慢產出、高質量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時期改編自經典的文學作品和影視作品的數目繁多,這與很多作者草率成書、借經典而宣揚自身的做法不無關系,它們以經典為依托,其目的是為了謀求商業利益,追求短線回報,這樣的作品即便當時能獲得追捧,也無法經受住時間的考驗成為經典電影。
二、 電影改編背后的后現代主義思潮
電影中經典被消費的現象,不只出現在中國,而是世界范圍的。美國導演庫布里克的《發條橘子》是對《雨中曲》的戲仿,它如《約會電影》《恐怖電影》等影片中也有很多經典片段雜燴在其中。經典文本的藝術魅力、深度意蘊就是在這種大話、戲仿的過程中被不斷解構的。
經典被消費,究其原因在于20世紀60年代西方后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影響。所謂后現代主義思潮,是針對現代主義而言的,其所有特征都以“反”傳統、“反”現實的方式出現,后現代主義強調反文化、反傳統、反權威,是對原來建立的話語權的一種顛覆與解構,進而以后現代的方式重構的一種新的話語方式。說其解構,是因為后現代主義以不確定性為核心,它堅持一切都是不確定的,認為創作本身應該是無主題、無形象、無情節的,既有的邏輯性、連貫性、完整性都可以被打破,傳統的權威、原則與深度都是值得懷疑的。在解構的同時,后現代主義也試圖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構一種話語權。后現代主義所建立的體系中,提倡拋卻制約,追求自由、無限制的創作,推崇多種方式混搭、拼接的創作手法,以反諷的方式嘲弄、戲仿經典。在重構的所有特質中,后現代主義的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強調內在性,它專注于自身的愉悅之中,在感官刺激中尋求快感,不再渴望對真善美的挖掘,也不再關注對終極價值的追尋。
這種后現代主義思潮從產生之日起在西方便產生強烈反響,伴隨著世界各國的廣泛交流,后現代主義思潮在很多國家傳播,從空間上看,可以說后現代主義思潮是世界性的。大話、戲仿的電影作品就是在這一時期廣泛流行的,這類電影作品所具有的娛樂性、淺表性及速食性特征無不與后現代主義思潮相關。這類影片在挑戰傳統之后構建的以無原則、無方向、無標準、無秩序為主話語方式,也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藝術應有的底線,使高雅與低俗混同,也使創作者和接受者在情感缺失中失去了信仰。
誠然,后現代主義思潮本身也有一定進步意義,正如美國后現代理論家伊哈布·哈桑所言:“后現代主義的學說錘煉了我們的感性,使之善于感受事物的差別,使我們更能包括諸多無常規、無標準的宇宙事物。”[3]它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迥異于傳統思維的模式,后現代視域下慣常思維被打破,人們可以從多角度、多空間去考察事物,從這一點來看,無論對創作者還是接受者來說,無疑都是一個進步。但若一味講求照搬照抄,也會在接受后現代主義精華的同時將其思想中的糟粕一同繼承過來,在娛樂經典的同時也迷失了自我。
三、 經典與電影改編的未來
面對后現代主義帶來的問題,伊哈布·哈桑也曾坦言:“我不知如何讓我們的精神沙漠,多增添一點生命的綠意”[4]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深遠的當下,在電影發展的歷程中,或許讓我們精神沙漠增添一點生命的綠意的方式,應當從電影人與觀眾的身上去追尋。
其一,作為電影人,應始終保持“二心”,即敬畏心與責任心。所謂敬畏心,是電影人面對經典時應有的態度。電影人對經典的敬畏心,還應該從電影改編如何對待傳統經典說起,這是一個老問題,但也是一個能夠解決后現代主義思潮帶來的困境的新方法。后現代主義影響下,經典在電影人心中是可以隨意惡搞、任意戲弄的文本,經典也早已成為被顛覆的靶子,在如此境遇下產生的改編作品,也難登經典電影的大雅之堂。以敬畏之心對待經典,并非指改編要完全忠實原著,依據原著亦步亦趨、小心翼翼的改編,同樣不會創作出優秀的電影作品。好的改編,應該是既忠實于原著而又不愚忠、既改編原著而又不亂改,這就需要電影人有一雙發現美的慧眼,將語言文字掰開揉碎成很多未加工的元素,用電影的技術,從視覺、聽覺等方面將這些元素融合成一部內涵豐富、極具藝術魅力的值得觀眾一看再看的影視作品。
所謂責任心,是指電影人應具有傳承經典的責任意識。電影的發展離不開經典的滋養,無論在體裁上、還是在敘事方式等方面,經典都為電影創作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方法。相應地,在視覺化時代中,經典的傳播也離不開電影,經典中蘊涵的人生哲理、生命體驗乃至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都需要電影人以更開闊的胸懷去感受經典,進而成為連接經典與現代讀者的橋梁,改編出符合當代社會價值理念、適合接受者心理的優質影片。優秀的電影人,所改編的作品一定是符合而非迎合接受者心理,因為電影的品質與品格絕不會在迎合中體現出來,不論影視拍攝技術如何更新,電影人心中對經典的責任應該是永恒的。
其二,作為觀眾,也應始終保持“二心”,即警惕心與好奇心。消費浪潮推動下出現的這些惡搞、大話類影片,其產生不僅有電影人的因素也有很多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對此,不能一味的苛責電影人。但作為觀眾,面對這一類型的影片,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吸收借鑒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產生優質影片的同時,對待那些娛樂性、淺表性、速食性強的影片應保持理性態度。經典是經歷千百年累積和考驗而來,雖暫時處于一種尷尬局面,但經典不會輕易被歷史所淘汰。因為“惡搞”版《西游記》“對原著的消解、顛覆作用只發生在大眾消費的娛樂層面上,對作品的哲理、宗教、社會文化等廣袤、深邃的思想蘊藉基本沒有涉及,也即沒有指向作品文化精神的硬核。”[5]但由于很多正處于成長期的青少年,缺乏辨別能力,影視傳媒影響下很容易迷失方向,對此我們應時刻保持警惕心理。
在對大話、戲仿類電影作品保持警惕心的同時,也應對經典保持好奇心。消費時代下,經典被解構、消解的浪潮,或許難以阻擋,但我們卻可乘勢而為,在冷靜對待影片的同時以一顆好奇心去看待被解構和嘲弄的經典,去探索影片到底解構了經典哪些成分,磨平了經典哪些內涵。
電影的發展需要經典的滋養,而經典在現代的傳播同樣需要電影的幫助,即便在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的當下,電影與經典的天然關聯也沒有消失,電影可以通過變革技術、傳遞思想來拯救處于尷尬地位的經典,經典也可以給電影的發展送去精神的養分,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電影與經典的良性互動。
參考文獻:
[1](美)約翰·費斯克.理解大眾文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171.
[2](美)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北京:三聯書店,1992:45.
[3](美)伊哈布·哈桑.革新/更新:人文科學研究的新視角[M].麥迪遜:威斯康星大學,1983:27.
[4](美)伊哈布·哈桑.后現代轉折[M].哥倫布:俄亥俄州立大學,1987:181-182.
[5]竺洪波.經典在大眾傳媒時代的命運——“惡搞”版《西游記》之我見[J].中文自學指導,2007(5):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