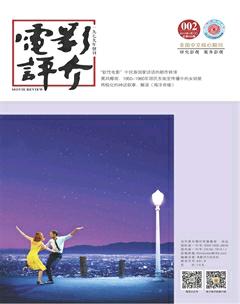結構主義視域下的《天那邊》
趙元
電影《天那邊》是一部關于大學生志愿到貧困山區支教的現實主義影片。該影片講述了大學生許曉萌和其男友江可可到邊遠山區水咕嚕小學支教的故事,其男友因為無法忍受鄉村生活條件的艱苦、落后而中途退出,許曉萌則克服了心理上與環境上的困難,實現了支教三個月的愿望;后來當她得知水咕嚕小學唯一的教師因修筑教室遭遇泥石流意外去世后,再次自愿回到鄉村小學繼續教書。通過對影片《天那邊》的結構主義分析,我們從物質層面分析出隱藏在表層的語言結構下的深層結構,即經濟的發展導致鄉村教育的落后。
一
20世紀20年代,在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的啟發下,結構主義應運而生。結構主義在50年代是人們普遍用來分析文化、語言和社會的研究方法之一,為人們認識事物、研究事物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結構主義認為,任何敘事作品都是一種話語系統,具有整體性,并且各個要素的性質都由這個系統的整體的性質所決定。其內部結構都可以從兩個維度進行分析:其一是表層結構,即根據敘述的前后順序研究句子與句子、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系;其二是深層結構,即潛藏在語言組織背后并且可以不斷生成意義的系統,以及由這一系統組成的隱藏在一系列作品中的那類影響和支配每個作品意義生成的結構模式。同類型的敘事性的作品,不論是從表層結構還是從深層結構來看,作品的內在結構是永恒不變的,變化的部分只涉及環境、人物和故事情節、時間等因素。同一類型的故事,雖然其中發生了很多細微的變化,但是它的基本框架始終都沒有發生變化。[1]
影片《天那邊》主要分為五部分進行:開始時的平衡狀態;出現失衡;努力恢復失衡;解決失衡;重新建立平衡。
“水咕嚕小學在羅老師的帶領下有序地進行著教學活動”,這是最初的平衡狀態。志愿者許曉萌和江可可來到水咕嚕小學,許曉萌主動要求給學生上課,這時,原來的平衡開始出現失衡。第三部分是努力恢復失衡。羅老師和村長聯合起來阻撓許曉萌給學生上課。隨著許曉萌的返城,事件似乎回到了最初的平衡。之后,羅老師為了修筑教室遇到泥石流不幸去世,許曉萌決定再一次回到那片天——水咕嚕小學任教,把自己的才華和青春奉獻給那里的孩子。這樣事件才獲得最終的新的平衡。
二
“二元對立”結構是結構主義理論的根基,當我們把研究對象分解為若干結構時,便可以從中找出一些相互聯系的、對立的矛盾、包涵、轉換等關系。通過對這些關系的研究,發現這些關系又表現為兩類事物處于相互對立的位置,產生明顯的對比和區別,進而產生各一層次的意義。這種二元對立形式表現在影片的各個方面,并且始終處于斗爭的狀態。“這是一種神秘的(也是戲劇的)黑暗與光明的偉大的斗爭:一方面是黑夜、陰影、悲哀、眼淚、昏睡、沉寂、怯生生的溫柔和延綿不斷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響當當的東西,武器、蒼鷹、棍棒、火炬、軍旗、吶喊、漂亮的外表、亞麻布、紫色和金子、鋼鐵、火刑柱、烈焰、鮮血。”[2]“二元對立”的碰撞和張力構成了整體結構的變化和運動,發揮整體結構的功能。批評者通過對對立的“二元”的分析深入到影片的深層結構,進而把握影片的整體內容和深層含義。
在每個電影的整體結構內部,都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元素。這種對立元素相互依存,二者之間有一種“交換紐帶”作為溝通傳達信息。
(一)理想與現實
許曉萌,一個品學兼優,有活力、有激情,對未來的人生有著無限美好憧憬的女孩子。在她即將畢業之際,為了響應國家號召自愿到偏遠山區實現自己理想。盡管她從小生活在城市,對農村生活不甚了解,但是她認為自己有責任為農村的教育事業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她還動員自己的戀人江可可一起去偏遠山區支教。在去支教的路上,許曉萌還為自己所做的選擇而驕傲,對她將要去的地方充滿憧憬,那里是與她所生活的城市不一樣的新奇的世界,是天那邊的世界。那里有高聳的青山,茂密的森林,連綿起伏的農田,新鮮的空氣,炊煙裊裊升起的農家小屋,還有一群瞪大銅鈴般的眼睛認真聽自己講課的農村孩子。她要把自己的所學、自己的教育理念在這里實現。這將是一次非常難得的體驗,這將成為自己人生道路上不可多得的一筆財富。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這些。泥濘的道路,簡陋的校舍建筑,水跡斑斑的教室墻壁,未見漆色的門窗桌登,雜草叢生的土地操場,低矮潮濕的住房,沒有室內廁所,購物的不便,沒有任何業余文化生活,電壓不穩、沒有信號,閉塞的交通等,這些都是呈現在她面前的真實的現實生活環境。這里的教學環境更是超乎她的想象:她所任教的小學竟只有一個老師,不同年級的孩子都由羅老師一個人來授課,教室是用農民居住的土屋,教學器材幾乎沒有,桌椅破舊不堪,操場上雜草叢生、雞牛相伴。
(二)愛情與現實
江可可,一個多年在國外求學的海歸,尚未完成大學學業的時尚都市男生。他到水咕嚕小學支教并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沒有許曉萌的雄心壯志,他是為愛情而來的。愛情的力量讓他不顧將要面對的所有困難,不顧朋友的再三勸阻,堅決追隨許曉萌去偏遠山區支教。然而,山區的生活條件與他的城市生活相差甚遠,山區信號差,打電話要爬梯子上房頂,還因此摔傷;帶去的電腦除了聽歌什么也做不成,還因電壓不穩而報廢;每天都是素菜,沒有肉,還因想吃肉掉到水里;到了晚上還要和羅老師擠在一張單人床上。另外,許曉萌每天忙自己代課的事情而冷落他。最終艱苦的現實生活環境擊敗了江可可“山無棱,天地合,我也不與她絕”愛情誓言,他選擇了放棄,離開了水咕嚕小學,離開了許曉萌。
(三)以許曉萌為代表的大學生志愿者和以羅老師為代表的鄉村教師
許曉萌代表著無數赴山區支教的大學生,他們學有所成,有熱情有夢想,敢想敢干,希望把自己的所學應用到實踐中,希望自己的教育理念能夠實施,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改變山區落后的教育事業。因此,當羅老師百般阻撓不讓她上課時,她認為自己的理想和熱情受到阻礙,因而態度堅決,想要掌握這三個月的教學主動權。
但羅老師認為這些志愿者不過是鄉村學校的匆匆過客,他們在短暫的支教期間,用時髦的教育方式來教導學生,雖然很受孩子們的喜歡,但是三個月過去之后,隨著志愿者的離開,這些先進的理念也隨之悄然結束,還是由自己來接手,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仍然要回到最初的教育模式。正如曾經的志愿者白老師,以各種教育方式來教導孩子們,可是在他離開之后,現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只不過讓充滿希望的孩子哭泣一場,徒增一次失望罷了。因此他對這些“三月的天使”持以懷疑和不配合的態度,遲遲不肯給他們安排教學任務。但是羅老師最終是迫于行政壓力,安排了教學任務,卻仍遭到許曉萌的反對,因為沒有給她安排語文、數學等主課,這與她改變鄉村教育落后的現狀,引進先進教育理念的理想出入很大。
(四)自我與他者
在影片中始終存在兩種身份的對立,即以當地鄉村教師為代表的自我,和以志愿者教師為代表的他者。這種對立是通過城鄉二元對立逐步表現出來的,并貫穿影片的始終。在影片的開始,列車上許曉萌和江可可的對話表現出他們對自己的定位“城里人”,對農村的定位則是“有牛、有羊、有豬”“多牲口,少點娛樂”。村長簡短而流暢的歡迎詞和江可可嘲弄搞怪的表情以及許曉萌的偷笑形成鮮明的身份對比,之后江可可要求村長講普通話則把兩者的身份沖突進一步揭露。在歡迎儀式上,不只有學生,還有牛、豬、雞,當許曉萌準備開始講話時被抓雞、抓豬、牽牛的鬧劇而打亂,而在這種鄉村生態中,許曉萌和江可可始終是充滿恐懼的局外人。戲劇性的歡迎儀式,將城鄉二元對立的身份差異徹底呈現,志愿者以一個他者甚至游客的身份進入農村,無法真正的深入了解農村,更做不到以農民自居。
(五)去與留
去與留是始終貫穿影片的一條線索,也是人物之間矛盾沖突形成的內在邏輯。曾經的志愿者白老師的匆匆來去;江可可為愛而留在水咕嚕小學,又因無法忍受鄉村落后的生活條件而離去;許曉萌為了完成自己的畢業論文,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留在水咕嚕小學,因三個月的支教生涯結束而離去。之后得知羅老師因為修繕教室遭遇泥石流去世,她放棄了在城市的穩定工作,再一次回到曾經教書的地方。她的留下對鄉村的孩子們來說是一種福音,但對她自己呢?是否還記得當江可可離去后,她在大雨中的呼喊:“那我們的愛情呢?”她是否也將面臨著羅老師同樣的問題,即個人情感將如何解決?許曉萌的留下,是出于道義還是心如止水呢?她是否也將離去?去與留不僅表現在志愿者身上,在當地村民身上也同樣。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大量農民進城務工,以羅老師妹妹為代表的一大批水咕嚕村的青壯年都離開鄉村到城市打工,留下來的只是老人和小孩。
由“80后”導演韓延導演的影片《天那邊》,是一部以“農村支教”為題材的電影。影片中存在的二元對立結構,不僅推動了故事的發展,更使得故事變得曲折而耐人尋味。通過對影片中二元對立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隱藏在影片語言話語系統背后的深層內涵,即市場經濟的發展,大量勞動力的需求使得越來越多的農民走出農村走向城市,而且更多走出的人們不愿再回去,這就造成了鄉村人才的斷層。
結構主義電影批評理論主要是到受列維-斯特勞斯的整體結構和二元對立的分析方法影響,從而對影片進行深入分析。“運用結構主義分析電影,主要是在一部影片、或某導演的全部影片、或某一樣式的影片中找其基本結構。這個結構一方面表現為表層和深層兩個層次,另一方面表現為雙元對立組,即在影片的內容和形式上找出一組對立特征,各對立組中的成分內容盡管不同,卻都具有對立性。這些對立特征組連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結構整體。”[3]“通過對影片的重復性主題,事件和視像風格表現,找出基本對立的結構,如由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個人與荒野、男人和女人、成功和挫折、內部與外部等主題組成的結構”[4],達到欣賞、理解、領悟一部影片的目的。
參考文獻:
[1]童慶炳.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48-249.
[2]巴爾特.論拉辛[M].紐約:希爾出版社,1964:36.
[3]李幼燕.當代電影美學思想[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105-106.
[4]李維品,鄒定武.電影藝術導論[M].重慶:西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