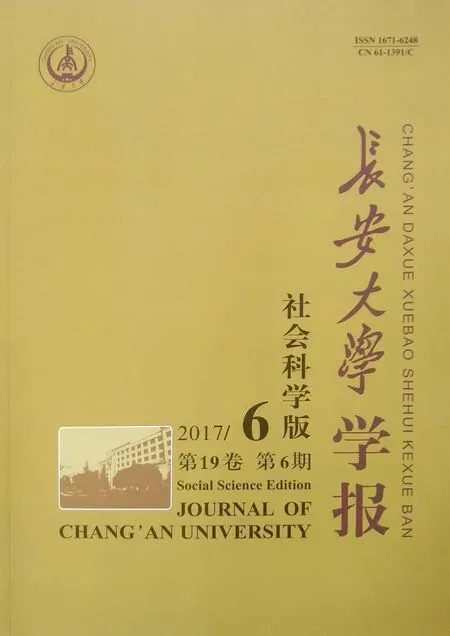意大利華人的城市社會融入度研究
石嘉怡,郝柏年,張群,石磊
(1.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建筑學院,陜西西安 710055;2.哥倫比亞大學工學院,紐約 10027;3.西安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西安 710054)
ability
自1950年起,歐洲國家創立了歐洲聯邦的戰略目標,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形成以及亞太經合組織的產生,標志著全世界范圍的經濟全球一體化進程開始逐步推進。世界各國經濟之間彼此相互開放,形成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的有機體[1]。在此背景下,不僅國家內部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廣泛而頻繁,國與國之間的人口流動也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
近二十年來,中國海外新移民呈加速度遞增趨勢,不僅使世界各地特別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歐洲、非洲等的華僑華人數量急增,而且迅速改變了當地華人社會的格局。北美華人從1990年的200多萬急增至2010年550萬。歐洲華人由數十萬急增至200多萬,非洲由數萬猛增至近百萬。2000年至2010年增長更快,如西班牙華人從2.8萬人猛增至15萬人,美國華人從300余萬人增至近400萬人[2]。這些海外移民必須適應當地的生產生活體系和當地社會互動規范,并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成為適應該社會生活的社會成員,即通常所謂的社會融入或社會融合[3]。而關注海外華人與所在地的社會融入度,對其群體中個人的身心健康與整體海外華人的社會關系轉型有著較為重要意義。
目前,中國學界關于社會融入的研究以及政界對社會融入的關注,主要集中于城鄉移民、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等社會弱勢群體。而事實上,對于普通的、正常的公民,由于社會性資源的不一致或文化差別以及自身條件的限制和束縛,也會導致其在與當社會互動的過程中或多或少出現社會問題[4]。然而海外移民這一群體數量的日漸龐大,使我們不得不考慮其融入度與整個社會發展的影響。中國現有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論架構與綜述上,缺乏對實際案例深入的社會調查。本文針對海外移民城市社會融入問題,以在米蘭長期居住(3年以上)的華人為樣本,在總體描述其融入當地社會現狀的基礎上。以“是否愿意長期定居”為因變量,以性別、年齡、文化程度,家庭狀況等個人因素;熟悉環境程度與社會角色等社會外部因素;職業滿意度、就業收入等經濟因素為自變量,通過建立多元Logostic回歸模型對可能影響其融入當地社會的因素進行實證分析,期望通過對不同可能影響融入社會因素的探討與分析,對整體海外華人的社會轉型有一定的指導與借鑒作用。
一、數據來源
根據意大利統計局的人口普查統計,米蘭市的華人人口數量排意大利所有市級城市第一,約為18 918,占居民總人口的1.43%,具有一定的數量基礎。本次調查采取類型抽樣法,從一個可以分成不同子總體(或稱為層)的總體中,按規定的比例從不同層中隨機抽取個體進行調研[5]。調查時間為2017年4月,調查對象為16歲至60歲在米蘭長期居住(3年以上)的華人。調查地點為米蘭市9個行政區,其中由于第八區是華人聚集地,故調查頻率更高。本次調查共發放523份調查問卷,收回520份,其中有效問卷為516份。調查內容包括4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個體基本信息,其中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文化程度、家庭狀況等;第二部分為經濟狀況,包括收入水平、職業滿意度、是否有固定居所等;第三部分為社會外部影響因素,包括是否能與當地居民交流、是否參加社會組織、熟悉環境程度等。第四部分為考量因素,將對現狀的滿意度化為“是否愿意長期定居”,共分為兩個等級:0為不愿意,1為愿意。
二、米蘭華人社會融入現狀
伴隨著移民人口的大規模流動及相關社會問題的凸顯,西方學界逐步將移民的社會融入作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納入到其研究議程當中,并進而將其形成的研究性知識傳遞到實際的社會治理、政治決策等層面。移民融入的理論研究與政策治理之間相互影響,最終深刻地影響到了西方現代工業社會的結構塑造、演變路徑、政治實踐等。本文通過楊格·塔斯提出的“三維度”模型,將社會融入分為多維度概念。此即具體通過結構性融入、社會-文化融入以及政治-合法性融入來分析在米華人社會融入現狀[6]。
(一)結構性融入
在海外華人的結構性融入主要是由如教育、勞動力市場與收入方面組成,所以以“是否接受當地教育”“職業”“收入水平”來反映結構性融入概貌。
在調查“是否接受過當地教育”時,按照是否有子女,將目標群體分為兩類。調查數據顯示,無子女的受訪者中有46%的人回答“正在接受當地教育”;有22%的人回答“曾經接受過當地教育”;而剩下的32%的人則表示“沒有接受過當地教育”。而有子女的受訪者中,76%的受訪者表示“子女正在當地接受教育”,21%表示子女沒有在米蘭生活,3%的受訪者則回答“子女在米蘭生活且沒有受到當地教育”。由此可以看出,在米生活的華人接受當地教育的比例較大。
從在米華人的職業來看,種類較為多樣。但根據美國賽特的職業地位分層來講,職業社會地位并不高。其中,學生占16%;非熟練體力勞動者,例如清潔工,搬運工等占11%;半熟練體力勞動者,例如售票員、服務員等占24%;熟練體力勞動者,例如美容理發師,廚師等占29%;小企業所有者和經營者,如服務業主、小零售商、小承包商等占19%;而工商業者與專業人員,例如大產業主、大工商企業家、藝術家、教師等僅占1%(圖1)。
在米華人工資結構一般分為兩層:一方面為向政府的報稅工資,另一方面為由雇主直接支付的非報稅工資,兩部分總和為實際工資。由于學生群體無收入,因此不計入有效受訪者中;并利用分層抽樣法調查當地意大利裔居民收入水平進行對比。由圖2可知,在米華人整體收入水平不高,且整體收入水平普遍低于當地意大利裔居民。其中,年收入8 000歐元以下的華人占總人數的15%,意大利裔人數只有6%;年收入為8 000歐元至16 000歐元的華人為19%,意大利裔為10%;16 000歐元至24 000

圖1 在米華人職業分布
歐元的華人占20%,意大利裔為16%;24 000歐元至32 000歐元的華人占36%,而意大利裔占45%;年收入為32 000歐元以上的華人為10%,意大利裔為23%(圖2)。
由上述數據分析可知,在米華人的結構性融入困境主要集中于收入水平 。而導致這種困境的原因并不僅僅是由于自身較低的職業資格(對從事某一職業所必備的學識、技術和能力的基本要求)造成的。楊格·塔斯認為,在所有的西方國家中,隨著工業制造業已經被服務業所替代,其勞動力市場也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個體的要求已經不僅僅是更高的職業資格,而是更好的就業彈性(靈活性)。具有更強的社會適應能力與溝通能力、更好的自我調適能力,是新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然而,移民群體,特別是移民青年卻缺乏相應的能力,面臨一系列的社會經濟融入機會的限制。許多少數族群背景的青年拒絕社會中的諸多基本性的制度,導致結構性融入度低[7-8]。
(二)社會-文化融入
在“三維度”模型中,社會-文化融入主要體現為人們對于各種社會組織的參與、與外來群體進行人際溝通能力的發展以及按照東道國的行為模式進行行動的過程。楊格·塔斯認為,社會-文化融入有多個測量指標,其中最明顯的就是人群間的隔離程度與語言使用[9]。
所以在此次調查中,以“參加社會活動頻率”、“是否能與當地人交流”來反映社會-文化融入度概貌。
在“是否參加社會活動”這項調查中顯示,大多數在米華人群體均有一定程度的參與不同社會活動,其中包括體育比賽、社會募捐及宗教活動等。
由圖3可知,20%的受訪者一周會參加少于2次的社會活動;而參與2~3次社會活動的受訪者比例占總人數的48%;3~5次的社會活動占23%;而5次以上的占9%。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社會活動屬于宗教活動。在受訪者中,近30%的華人表示,在日常社會活動中,會有穩定的宗教活動。在進一步的調查中發現,在米華人經常參與的社會活動中,參與人群大多為華人群體,與當地人群的溝通與交流較少。
從是否能與當地人語言交流上來看,58%的受訪者表示能與當地人在語言上順利交流;34%的受訪者表示在語言交流上存在著一定的困難,但可以通過第三種語言(多為英語)交流;7%的人表示在語言交流上存在著較大的困難;其中1%的人表示甚至完全無法與東道國的人交流。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雖然受訪者的社會參與頻率較高,但參與人群單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大多數的華人在語言溝通方面沒有太大困難,但由于傳統觀念及民族聚集性的影響,在米華人群體在意大利社會-文化融入度還處于比較低的水平。
(三)政治-合法性融入度
楊格·塔斯的三維模型明確提出了政治與合法性的融入,強調了移民的政治權利在社會融入度中具有很強的重要性。故在此次調查中,以“是否具有當地合法身份”“是否有選舉權”,來反應政治-合法性融入度概貌[10-11]。

圖2 在米華人與意大利裔工資情況

圖3 在米華人參加社會活動頻率
在“是否具有當地合法身份”調查中顯示,有12%的受訪者表示已經加入了意大利國籍;24%的受訪者具有意大利政府頒發的永久居留證;而擁有暫時居留證的人數占到58%;6%的受訪者不愿意透露自己是否擁有合法身份,經推斷,這些人為非法滯留者(圖4)。
從是否具有選舉權上來看,只有加入意大利國籍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擁有選舉權。其余受訪者均表示沒有選舉權(圖5)。
從上述數據中,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米華人的政治-合法性融入度水平很低。少數移民族群總是被流入地政府和本地的市民作為二等公民,成為社會歧視和種族主義的目標。要改變這種狀況,就必須有正式的法律測定標準如種族法律,來保障移民作為公民的平等權利,要重新思考基本的公民權利觀念、簡化移民程序,賦予相關的政治權利,建立專門的指導機構來促進少數族群的融入[12-13]。

圖4 在米華人當地身份情況

圖5 在米華人擁有選舉權情況
在米華人的社會融入是一個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乃至心理等諸多層面的系統工程。拋開在米華人社會融入所面臨的政治制度性障礙這一關鍵制約因素,在米華人的“留城意愿”能夠綜合反映其經濟能力、社會適應、文化認同乃至心理歸屬等眾多的影響因素。因此,考慮從在米華人“是否愿意長期定居”的角度,分析其在社會融入過程中的影響因素[14]。
(一)變量設定
我們將因變量設置為“是否愿意長期定居”,其中“愿意長期定居”設置為1,“不愿長期定居”為0。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在有效的516份問卷中,回答“愿意長期定居”的有156份,占總數的30.23%。為了能夠從多方面、立體、詳細地分析影響在米華人融入米蘭社會情況的因素,我們將自變量分為3組,分別為個人情況、職業情況與社交情況。其中個人情況包含性別、受教育情況、在當地居住時間與家庭狀況等4個變量。職業情況包含收入水平、每周工作時間與職業種類等3個變量。社交情況則包含參與社會活動頻率與語言溝通情況兩個變量。如表1所示,我們將使用4個模型對所收集到的數據進行二元Logistic分析。其中模型1~模型3分別分析個人情況、職業情況和社交情況對在米華人社會融入情況的影響。之后將模型1~模型3中通過顯著性檢驗的變量引入模型4,全面分析這些因素是如何影響在米華人融入米蘭社會的。

表1在米華人社會融入影響因素二元Logistic分析結果
注:*為p<0.1,**為p<0.05,***為p<0.01
(二)結果分析
從表1的分析結果來看,模型1~模型4的卡方顯著性均小于0.05,說明4個模型均是顯著的,具有統計學意義。其中,模型1中的受教育程度,模型2中的收入水平與職業種類,模型3中的語言溝通情況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它們對在米華人是否能夠融入米蘭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有影響。在模型1中,受教育程度這個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它的影響系數在模型4中由10%的顯著水平提高至1%。分析結果顯示,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與沒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相比,明顯能夠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而在意大利接受高等教育相比于在外地接受過高等教育對人們在社會融入方面則有更加顯著的正向作用。第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與傳統就業者相比,在城市融入的長線發展上擁有更廣闊的前景和經濟收入,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在城市融入中二者的社會地位差距,更容易得到當地居民的心理承認[15]。第二,相比于在外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在意大利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除了具有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優勢之外,更加具有文化方面的優勢,他們在當地接受高等教育期間,能夠充分地接觸當地的文化環境,更加有利于他們未來融入當地的社會氛圍。
在模型2中,受調查人群的收入水平與工作種類兩個變量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其中收入水平的影響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工作種類則由模型2中的5%提升至模型4中的1%。通過觀察收入水平這個變量,當人群的年收入高于24 000歐元時,則對該人群的社會融入程度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收入越高,這個影響越大。根據前文的收入統計情況,可知米蘭當地意大利裔居民的年收入中位數正處在24 000~32 000歐元的范圍內。由此可以發現,當在米華人的收入達到甚至超過當地主流水平后,他們將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一方面,高收入代表著更強大的經濟實力,這能夠幫助在米華人贏得更多的社會尊重與關注;另一方面,具有高收入的人群也有更強的生存能力或者一技之長,這些能力是在一個社會立足的必要條件。而在工作種類這個變量中,相比于學生,非熟練勞動者(如清潔工、搬運工等)更不容易融入當地社會,而大產業主、工商企業家、藝術家與教師則更容易融入當地社會。這是因為非熟練勞動者所從事職業的社會地位、技術性工種與收入較低,同時工作強度較大。這使得他們在難以得到社會尊重與關注的同時,又沒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去進行有利于社會融入的自我提升,如一定的娛樂社交活動和學習新的技能。而相比于非熟練勞動者和學生,企業家、藝術家與教師則有更高的收入和社會地位,這使得他們在社會融入方面有著更大的優勢。
在模型3中,語言溝通情況這個變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并且在模型3與模型4中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分析結果顯示,相比于能夠與當地居民使用意大利語順利溝通的人群,能夠用第三語言溝通的人并沒有在社會融入方面有顯著的劣勢。而語言溝通困難則對華人在社會融入方面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這是因為良好的語言溝通能夠減少在米華人的生活障礙,并使得他們更容易與當地人交流,進行文化溝通,并獲取更多的信息。而參與社會活動的頻率對在米華人的社會融入并沒有顯著影響,是由于在米華人的社會活動主要存在于華人社區中,并不能增加在米華人的文化交流和社會尊重,對融入米蘭社會并沒有太多的幫助[16-20]。
四、結語
綜上可知,對在米華人的社會融入狀況的影響因素主要為受教育程度、收入情況、工作種類與語言溝通狀況。而參與社會活動次數、是否有家庭等因素則沒有影響。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對于已經身處米蘭的華人,一方面,應當更多地致力于提升自己的個人文化水平,提升語言能力或者習得一技之長,提升自己與當地居民的溝通能力,更好地與當地居民進行文化溝通與交流,適應當地生活氛圍,獲取更多的社會尊重與認同;另一方面,在米華人應當致力于自身職業發展,積極提高收入以及提升職業社會地位。第二,對于未身處米蘭但將來有留米意向的華人,應當盡力爭取在當下所在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與工作能力,在定居米蘭之前做好充分的準備,以確保在未來進入米蘭生活時能夠有足夠社會地位與經濟實力,進而確保在將來獲得足夠的社會關注與尊重,以便于更好地融入社會。
[1] 李彬.淺析經濟一體化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J].現代商業,2013(28):143.
[2] 清華大學華商研究中心.中國僑資企業發展年度報告2010~2011[R].北京: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2011.
[3] 王佃利,劉保軍,樓蘇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融入——框架建構與調研分析[J].中國行政管理,2011(2):111-115.
[4] 何建寧,賈涵.“村改居”群體城市社會融入的影響因素研究[J].西部論壇,2015,25(3):9-15.
[5] 馬奔,劉澤忠.對定量包裝商品抽樣檢驗的探討[J].品牌與標準化,2011,9(18):38.
[6] 梁波,王海英.國外移民社會融入研究綜述[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10(2):18-27.
[7] Josine Junger-Tas,Ethnic minorities,social integration and crime[J].European Journal on Criminal Policy and Research ,2001,1(9):5-29.
[8] Birgit J.Migrant integr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 of new settlement countries: thematic introductio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ulticultural Societies,2007,9(1):10-21.
[9] Snel E,Engbersen G,Leeres A.Transnational involve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J].Global Networks,2006,6(3):267-276.
[10] Heisler B S.The futur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which models?which concepts? [J].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1992,2(2):624-645.
[11] Wuthnow R ,Hackett C.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practitioners of non-western relig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J].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2003,42(4): 651-667.
[12] Jacobs D.Introductio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J].Journal of ethnicand migration studies,2004,3(30):419-427.
[13] 張琴琴.城市少數民族融入主流社會的研究 [D].北京:中央民族大學,2011.
[14] 向華麗.女性農民工的社會融入現狀及其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湖北3市的調查[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23(1):103-110.
[15] 于夢,張瀛木,李峰,等.大學生跨區域就業與城市融入——基于大學生與當地居民群際關系 [J].教育教學論壇,2014(50):41-42.
[16] 陳麗竹.21世紀以來丹麥移民子女教育政策述評[J].人生十六七,2017(33):107.
[17] 劉騫.對德國穆斯林移民社會融入的再思考——以宗教認同與公民身份互動為視角[J].國際政治研究,2017,38(5):86-103.
[18] 楊菊華,賀丹.分異與融通:歐美移民社會融合理論及對中國的啟示[J].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17(5):72-80.
[19] 黃紀凱.在地化影響下的中國海外移民行為特征探析[J].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7(3):67-74.
[20] 劉春燕,王鐳衡.相依共融:加拿大華人社團組織對華人移民融入的作用[J].貴州師范學院學報,2017,33(5):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