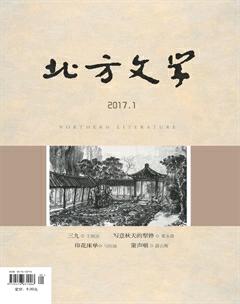中國古文論中的風格成因說
潘佳佳+潘瑩+肖梓怡
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史上,關于風格的成因有諸多種說法,將他們歸納起來并作一些分類是有意義的。一方面可以較為清楚地明了中國古人對這一問題的思考和認識;另一方面也可以為今人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提供借鑒。大致說來,中國古文論中認為風格紛繁多樣的原因有四:一是社會生活的變化,尤其是政治的衰榮、朝代的更替,這以《毛詩序》為代表;二是創作主體作家的個性氣質,持此說的主要有孟子、韓愈和曹丕;三是不同文體對風格有不同的要求,從曹丕到陸機再到劉勰都對此有過論述;四是語言文字、音韻節奏對風格的影響,持此說的主要是清代劉大櫆。
《毛詩序》是漢代文學理論的典型代表,它的核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關于文學的本質、功能作用的觀點主要繼承荀子并有所發展。它認為,文學藝術是民風民俗、百姓心聲的反映,而民風民俗又是政治得失的具體表現。它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①在《毛詩序》的作者看來,文學藝術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是與現實政治相聯系的,并反映著政治的得與失。當“治世”之時,文學會呈現出昂揚向上、奮發有為的風貌;當“亂世”之時,朝政黑暗,百姓水深火熱,文學則多表現諷諫時政,批判現實;當“亡國”之時,作家處于國破家亡之際,感情是哀痛與悲傷的,則此時所創作的文學作品多哀婉纏綿、悲戚感人。《毛詩序》關于時代變化、政治明暗對文學風格的影響的論述在中國文學史上能找到諸多鮮活的例子作為佐證,而在前后生活完全迥異的作家身上則表現得尤為顯著。南唐后主李煜,前期身為帝王,生活于溫香軟玉之中,心情閑適舒暢,所創作的詞多輕快明朗,即便偶有哀愁之作也是無病呻吟,成就也自然不高。等到他為宋朝的帝王所虜,成為階下囚時,經歷了國恨身辱之后,這種感情就顯得更為真實和感人,發而為詞,必然高出一層境界。唐代的雙子星座李白與杜甫也可為證。李白生活于大唐王朝蒸蒸日上、一派繁榮的氣象中,正處于“治世”之時,所以他的詩歌更多表現為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豪情壯志,他筆下的意象多為“大江”、“黃河”、“蒼鷹”和“泰山”等具有宏大崇高的特點。即便對仕途不如意、人生無常所發的牢騷也是“白發三千丈”式的灑脫和豪邁。而杜甫親身經歷了“安史之亂”,他親眼目睹了大唐王朝的由盛而衰,同時他又以詩人的獨特敏銳感預想到鼎盛江山的一去不復返,因而他無論寫對國家前途命運的擔憂,或是個人身世榮辱的感嘆還是對親朋好友的思念都帶有一種深沉抑郁的悲傷,那種沉郁之情渾厚而無法消散,充斥于字里行間。
在中國古代文論中,另一派認為文章風格主要是由創作主體個性所決定的,持這種觀點的以孟子、韓愈和曹丕為代表。在《孟子》中有這樣一段對話:(公孫丑)“‘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②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老師:“您有什么特長?”孟子的回答是兩句話,第一句是“我知言”,意義是我善于觀察別人,通過對方所說的話我就能斷定他的道德修養;第二句是孟子對自己的評價:“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那么這種“浩然之氣”是什么呢?他的解釋是“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的“氣”是“配義與道”,是“以直養”的,具有“至大至剛”的特點,也就是通過自己后天的道德修養和人格鍛造從而形成一種強大的自我意志。前面已提到,孟子還說了“我知言”,這樣,我們前后聯系看,孟子的意思即,從事文章寫作的人,首先要加強自身的道德修養和人格鍛煉,用儒家的道義來充實自己,使自身具有一種正直之氣。這樣,發而為文,自然具有一種“至大至剛”,無法阻攔的“浩然之氣”,反之則“餒也”。這是對儒家先道德后文章的具體、完整的表述。孟子的文章正如他自己所說,給人一種勢不可擋,“塞于天地之間”的磅礴之氣,這除了他文章所用的大量排比句式、比喻句和反問句等修辭手法外,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自身所擁有的剛強、桀驁的個性,而他的這種個性一方面是與生俱來的,另一方面則來自他對正義、公平的絕對信仰和追求,以及他對自身道德修養的嚴格要求。
韓愈以重振朝綱、再現盛世的面孔出現,他始終以儒家的道德要求自己,并以正統儒學傳人自居,蘇軾說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他雖處于儒、道、釋并存的唐朝,但他是與孟子一樣的真正的純儒。韓愈的文論觀主要來源于儒家,他關于文章寫作與主體的道德修養、人格鍛煉的關系更是緊步孟子后塵。在《答李翊書》中,他說:“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他將創作主體比為樹之根,燈之膏;將文章,即“言”喻作樹之實,燈之光,根茂則其實碩,膏沃則其光曄。那么,創作的主體有良好的道德修養,以儒家仁義作為人生信條,他的文章自然充實豐富,充滿陽剛之氣。他還說:“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運用的還是比喻的方法,氣猶如水,言猶如物,當水大則物大小畢浮。那么,當氣盛則言無論短長、聲無論高下皆宜。我們將前后兩句話連在一起來看會發現,他所說的涉及三個要素:人、氣、言,三者的關系完整的表述是,創作主體的人要用儒家的仁義道德作為立身之本,不斷加強修養,有了這種修養則自然有了剛毅、頑強的性格,即盛氣,有了這種性格發而為文,則“其言藹如”,“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同樣認為文章風格是由創作主體的氣質個性所決定的還有曹丕,然而同中有異,他所指的氣質個性是先天的,與生俱來的,而非后天的修養、鍛煉所得。因此先天稟賦不同的作家創作的文章風格也不可能一樣,是無法通過后天的學習、修養所能改變的。在《典論·論文》中,曹丕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因“不可力強而致”,那么不同作家長于不同的文體,顯現出不同的風格也就無可厚非了。“王粲長于辭賦,徐干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琳、瑀之章表記,今之雋也。應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辭。”
最早對文體對文章風格的要求進行思考并明確提出來的是曹丕,他說:“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他第一次指出不同文體有不同風格的要求,并將純文學的詩、賦列入考慮范圍,這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分類。后來陸機在曹丕的基礎上,指出了更為具體、細致的分類,并對每種文體的風格特征作了更明確的規定。在《文賦》中,陸機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曄而譎誑。”陸機較曹丕的進步之處在于,他不僅將詩和賦兩種文體分開,并對這兩種不同文體的風格特征分別提出了要求,他認為詩應“綺靡”,賦該“瀏亮”,這比曹丕以“麗”字作簡單的概括更為具體、準確。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的這種規定不是武斷式的,而是建立在各自所表現對象的不同的基礎之上。詩主要是用來表達感情,因而它應纏綿、悲戚;賦主要用來描寫景物,因此它得清明、光亮。在學習、借鑒曹丕、陸機關于文體對風格的要求的基礎之上,劉勰作了總結性的概述。在《定勢》篇中他重點研究了不同的文學體裁由于其內容和形式的不同特點,從而決定了其不同的風格特征。他說:“是以括囊雜體,功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頌賦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于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勢”本是指事物內在的一種客觀的規律性,劉勰說:“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文學作品不同的“體”有不同的“勢”,即一定的文體有與之相適應的一定的風格特點,這是文學作品體裁本身具有的必然性。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峰,他是方苞和姚鼐之間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他關于文學的理論主要體現在《論文偶記》中。在《論文偶記》中,他一方面認為文章的內容是最重要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也要有主有次,在這一點上劉大櫆的觀點與方苞相一致,正基于此,誠如郭紹虞先生所說:“劉氏所論乃是“義法說之具體化”。③但同時,他又認為文章的形式具有相對獨立性,不重視“設施”即寫作技巧,是寫不好文章的。他說:“蓋人不窮理讀書,則出詞鄙倍空疏。人無經濟,則言雖累牘,不適于用。故義理、書卷、經濟者,行文之實,若行文自另是一事。譬如大匠操斤,無土木材料,縱有成風盡堊手段,何處設施?然即土木材料,而不善設施者甚多,終不可為大匠。故文人者,大匠也;神氣、音節者,匠人之能事也;義理、書卷、經濟者,匠人之材料也。”④義理、書卷、經濟是作者進行文學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對這些材料如何設施、安排,則又是另一回事,不是有了材料就一定能寫好文章。所以,他又說:“當日唐虞記載,必待史臣。孔門賢杰甚眾,而文學獨稱子游、子夏。可見自古文字相傳,另有個能事在。”這里所謂的“能事”,是指文章寫作的本領和能力,也就是文章寫作中的藝術技巧和方法。這樣明確地、突出地強調文章寫作的形式技巧的重要性,不僅是對方苞思想的重大發展,也是對唐宋以來古文家理論思想的重大突破。
那么文章究竟要達到怎樣的境界才算是會設施,可稱為“能事”呢?在劉大櫆看來,一篇文章好不好、美不美關鍵在于是否能達到神、氣的自然流露。他說:“行文之道,神為主,氣輔之。曹子桓、蘇子由論文,以氣為主,是矣。然氣隨神轉,神渾則氣灝,神遠則氣逸,神偉則氣高,神變則氣奇,神深則氣靜,故神為氣之主。”這正是以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傳統的神氣說作為文章寫作的最高美學標準。對于劉大櫆所說的神、氣的含義各家的解釋大致相同。郭紹虞說,“氣在更多的地方,可以說,是指語言的氣勢;而神則是‘氣之精處,是形成一種獨特風格的不可少的東西,亦即作者性格特征在藝術上完滿而成熟的表現。”張少康說,“神是指文章中自然天成、不落痕跡,又能充分展示作者精神面貌特征的化工境界,氣是指文章中具體體現這種化工境界、帶有作者個性、氣質的行文氣勢。”大體上神是就文章所表現出來的帶有作者個性色彩的整體風貌、境界而言,氣則是蘊藏于字里行間的氣勢、文風,相對比較具體。關于神與氣的關系,劉大櫆也有相當精辟的論述,他說:“神者,文家之寶。文章最要氣盛;然無神以主之,則氣無所附,蕩乎不知其所歸也。神者氣之主,氣者神之用。神只是氣之精處。”神是氣的歸宿,氣是神的表現。他非常贊賞李翰的話:“文章如千軍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認為“此語最形容得氣好。”重氣實際上也就是重神,他又說“氣最重要。”“今粗示山崩,如峽流,覺闌當不住,其妙只是個直的。”
坦誠地說,神氣說并非劉大櫆的創見,而是古已有之的。他的貢獻在于提出因聲求氣,指出神氣、音節、字句三者的關系,使神氣不再玄妙莫測,而變得具體可以探求。《論文偶記》中有一段關于他對神氣、音節、字句三者關系的精彩論述:“神氣者,文之最精處也;音節者,文之稍粗處也;字句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而至于字句,則文之能事盡矣。蓋音節者,神氣之跡也;字句者,音節之矩也。神氣不可見,于音節見之;音節無可準,以字句準之。”在他看來,神氣并不是抽象而難以把握的,它可以通過文章的音節體現出來;而音節之美又可以落實到文字上來。文字有四聲、平仄的不同,有清濁、輕重的差別,因此完全可以通過文字的不同排列組合去表現音節之美。他說:“音節高則神氣必高,音節下則神氣必下,故音節為神氣之跡。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為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櫆第一次清晰地指出,可以通過語言文字的不同組合,音節的轉承變化來達到“如山崩,如峽流,覺闌當不住”的神氣,即“求神氣而得之于音節,求音節而得之于字句”,這是他對中國古代文論的貢獻所在。但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劉大櫆的神氣、音節、字句之說有過分強調文字技巧的缺陷。正如張少康在《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所說,“從文學創作來說,神氣不都體現在音節上,它首先是與意象的構成和意境的創造密切相關的,自然音樂美也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從一般非文學的文章來說,神氣也是和思想內容、邏輯力量等有直接關系的,也不全在音節、文字上。”
通過以上的梳理,我們會發現,從漢代《毛詩序》到清代劉大櫆近二千年的時間里,中國古人從未停止過對風格問題的思考。從《毛詩序》中可以看到政治變遷、時代變化對風格的影響;從孟子、韓愈和曹丕,我們知道了創作主體的精神境界和性格特征對風格的巨大作用;從曹丕、陸機到劉勰,我們明白了不同文體對風格自身的要求;從劉大櫆,我們又獲悉語言文字、音韻節奏對文章風格的成效。應該說,古人的思考是建立在自身認識和實踐不斷深化的基礎上的,有其成熟性,對我們今天的文藝理論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和借鑒意義。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這種認識還存在片面,有待完善。創作主體性格的不同必然反映到所寫的文學作品中,從而形成風格迥異的作品,如魯迅的辛辣批判、冰心的溫文爾雅、錢鍾書的詼諧幽默。在同意主體性格特征對文章風格的決定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應注意兩點:一是,作家不同性格的形成一方面是先天稟賦的,與生俱來的,這居首位;另一方面也與后天的人格修養、見識學力、勤奮練習分不開,恰如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篇》中所指出的,形成作家個性的因素既有才、氣,又有學、習,其中才和氣是先天的,各人因稟賦不同而各異;學和習則是后天的,是與作家的努力相聯系的。二是,文學作品作為社會生活的一面鏡子,時代的變遷、政治的盛衰必然會反映在作品中,但這種反映不是自動的也不會千篇一律、異口同聲的,它與作家對現實的關注程度、自身的生活經歷以及使命感、責任感不無關系。同樣處于晚唐時代,李商隱詩中的失落、悲戚、哀傷、飄零之感遠較溫庭筠濃厚、誠摯。如果說作家先天的稟賦和后天的修養、學習以及一定的社會環境對他的影響屬于主觀因素,它對風格的形成起著決定作用,那么文體以及語言文字則屬于客觀因素,它同樣對風格有著巨大影響。詩歌、散文、小說、戲曲是各不相同的文體,也有著各自的語體要求,作為文體和語體最高體現的風格自然也各相迥異。白居易的《長恨歌》被改寫為《長恨歌傳》,原先的那種纏綿情意、飄逸文采則不復見;元稹的《鶯鶯傳》被改為戲曲《西廂記》則多了詼諧色彩和戲劇成分,讓人們在拍手稱快中也永遠記住了那位“志誠種”的張生。同樣以京都為對象,同樣用大賦文體,司馬相如的賦和張衡的賦風格則不盡相同,這除了時間因素、作家思想見地的不同外,與他們所選的對象、謀篇布局、遣詞造句也不無關聯。
注釋:
①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頁。
②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65頁。
③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頁。
④劉大櫆、吳德旋、林紓著《論文偶記·初月樓古文緒論·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第55頁。
參考文獻:
[1]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65.
[2]郭紹虞,王文生.《中國歷代文論選》(一卷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65.
[3]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59.
[4]劉大櫆,吳德旋,林紓著.《論文偶記·初月樓古文緒論·春覺齋論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