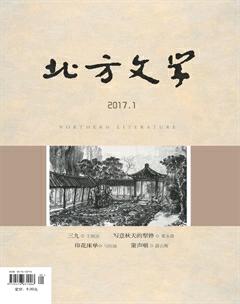從《地之子》看臺靜農對魯迅小說的繼承與發展
杜淑文
摘要:五四以后,在魯迅的帶領下,一批成長在鄉村,寓居于京滬大城市的知識分子,透析了現代都市文明和宗法制鄉村的巨大差異,懷著對鄉村的眷戀與“改造國民性”的渴望開始了鄉村文學的創作,如臺靜農、徐欽文、彭佳煌等。其中臺靜農是魯迅頗為贊賞的后起之秀。魯迅是鄉土文學的拓荒者,臺靜農是在魯迅直接關懷幫助下成長起來的鄉土作家,他所創作的《地之子》也是二十年代鄉土文壇上的代表作品。
關鍵詞:臺靜農;鄉土小說;繼承;發展
一、《地之子》的創作對魯迅的繼承
(一)從婚喪嫁娶到封建迷信的風俗沉淀
在作品中臺靜農用風俗描繪重現了兒時的故鄉皖西葉家集鎮,也就是小說中的羊鎮。多描寫了封建鄉村落后閉塞的生活,物質匱乏,精神迷信。《拜堂》中汪二和嫂子成親的場景,僅準備了香、燭和黃表,因為沒有紅氈子,不得已將汪大嫂床上的破席子拿出來鋪在地上。汪二也穿了一件藍布大褂,將過年的洋緞小帽帶上,帽上的小紅結,系了幾條水紅線。從異常簡單樸素的一場婚禮中,不難了解到當時落后鄉村的貧瘠與樸實。
(二)相似的人物塑造
臺靜農與魯迅在鄉土文學的創作中視角相似,人物塑造自然也有魯迅筆下的影子。不論是農村女性形象的塑造,還是聊以自慰的阿Q形象的打磨,還是對冷漠的看客形象的鞭笞,二者之間總有一種無形的共性在延續。以農村女性形象為例,臺靜農的作品中的農村女性形象都有著悲慘的命運和不堪的人生經歷,其中也不乏祥林嫂的影子。較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是《新墳》中的四太太,也是丈夫早逝,在亂世之中女兒被大兵奸死了,兒子被大兵打死了,四太太受不了如此大的刺激后精神失常,所有家產也被人卷走,流落接頭,像祥林嫂一樣逢人便不停的念叨,幻想兒子和女兒已經成婚的喜樂,最終死在兒子的浮厝旁。她們都是生不逢時的女性悲劇形象,作者通過描寫她們的悲慘命運,體現了下層女性在封建思想和道德禁忌的壓迫下步履維艱的生活,以引起療救的注意。
(三)藝術手法的共性延伸
在藝術手法的應用上臺靜農與魯迅一脈相承。魯迅追求表達的含蓄、節制,以及簡約凝練的語言風格。臺靜農在對人物和風景的描寫上多吝嗇筆墨,繼承了魯迅白描的藝術手法。如在《紅燈》中全篇只有一句景色描寫“南山陰雨,河水暴漲,沙灘已深深湮沒。”魯迅借鑒西方小說的藝術形式,不重情節的完整,注意結構的嚴謹,采擷生活的某一橫斷面來加以創作,臺靜農的作品中也延續了這一創作手法臺靜農受魯迅的影響,與魯迅的小說常以酒肆、茶館等下層人們的集聚地為背景相似,臺靜農也常以茶樓、飯館、十字街、水井邊等場合為背景,營造一種生活的日常氛圍,在人物的語言和行動中將場景直接展示給讀者。鄉村語言的靈活運用也是二者創作的共性所在,臺靜農的小說中也充斥著皖西口語的樸實靈動。人物交互,情節推動多以口語的形式呈現,簡潔明快,朗朗上口。且語言貼合人物形象。
二、《地之子》對鄉土文學發展的貢獻
(一)更為貼近鄉村的寫作
仔細研讀魯迅的文章我們不難發現,作品中雖有鄉村風景的描繪,卻缺少了細致的鄉村民間的生活圖景如干農活的瑣碎程序,雖有提及也只是類似于簡單幾筆的帶過,原因還是歸結于魯迅對于鄉村實際生活經歷的缺失。而臺靜農自幼在皖西鄉村的成長經歷,讓他有更多鄉土文學創作素材的積累,從婚喪家娶到鬼神祭祀到農時勞動,創作起來更信手拈來。并且臺靜農的作品中語言對話占很大比重,平實的鄉間口語讓他的文章更親切生動,真實感人。可以說,在魯迅之后,臺靜農的鄉土文學創作離鄉村更近了一步。
(二)愈深的人道主義關懷
臺靜農寫出了這個殘酷的社會,愚昧的風氣,森嚴的等級制度是怎樣壓垮了他的人民,是以一種悲慟的情緒去關懷他筆下的窮苦大眾,相比魯迅笑罵的“怒其不爭”,臺靜農更多的是“哀其不幸”的悲天憫人,充滿著人道主義的關懷。在《棄嬰》中當“我”看到棄嬰被野狗撕咬吞食時,“我”揮去手杖,不惜被咬傷了腿,“我”凄涼的自責,認為自己是這罪過的主人了,文章中對主人公寢食難安悲痛不已的心理描寫,體現了我對這個陌生小生命的人道主義關懷。臺靜農的文章中雖都是悲劇性的描寫,但作者更多的是向世人展示這個人的生存空間被極大壓抑的鄉土社會,渴望有新的力量來改變這一切,他懷有博大的同情去記錄去講述,通過寫實祈求達到喚醒的目的,這也是“大地之子”對他所眷戀的那片鄉土上的人民的深深愛意。
參考文獻:
[1]臺靜農.《地之子》[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2]嚴恩圖.《魯迅與臺靜農》[J].安徽師大學報,1987.
[3]夏明釗.《臺靜農小說集<地之子>述論》[J].寧波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