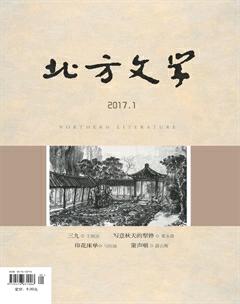試從《行影神》看陶淵明立身處世的方式
劉旭春
摘要:漢末以來儒學(xué)紀(jì)綱松弛,加上魏晉時(shí)期社會(huì)動(dòng)亂,人們思想既有漢時(shí)印記又發(fā)生了變化。重視個(gè)體感性生命的社會(huì)思潮,玄學(xué)虛無的辯論以及對(duì)功業(yè)的渴望都深刻反映到文學(xué)作品中。生于這一時(shí)期的陶淵明必定會(huì)受這些思想的影響,其《形影神》組詩展現(xiàn)出陶淵明在出世和歸耕田園的處世方式之外找到了“委乘運(yùn)化”的方式,在歸耕的同時(shí)也自礪道德,既安時(shí)處順又任情自適。
關(guān)鍵詞:《形影神》;陶淵明;處世方式
一
鐘嶸在《詩品》中稱陶淵明是“古今隱逸之宗”。“隱逸人格在本質(zhì)上必然體現(xiàn)為對(duì)理想社會(huì)和理想生活狀態(tài)的追求,隱逸文化的精義也就在于以文化理想來批判現(xiàn)實(shí),否棄現(xiàn)實(shí),抗衡現(xiàn)實(shí)和校正現(xiàn)實(shí)。”①陶淵明并沒有忘卻對(duì)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注,淡忘事世,因此他所寫的詩歌才帶著對(duì)社會(huì)、人生的感嘆。而他對(duì)歲月易逝感到無奈、傷痛并非懼死則是建功立業(yè)未遂引起的,因此他要努力把握現(xiàn)實(shí),積極進(jìn)取,而不是在道虛無縹緲的世界里體味人生。他在《影答神》中言:“存生不可言,衛(wèi)生每苦拙。誠愿游昆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shí)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生命如白駒過隙“影”用“立善遺愛”來反對(duì)“形”消遣時(shí)光的態(tài)度。
二
“影”是陶淵明求善揚(yáng)名的儒家思想的化身,那么“形”則代表陶淵明另一宗處世態(tài)度——自得其樂,試著看其《形贈(zèng)影》“天長地步?jīng)],山川無改時(shí)。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dú)復(fù)不如茲;適在適見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shí)豈相思。但余平生物,舉目情凄洏。我無騰化術(shù),爾必不復(fù)疑。愿君取吾言,得酒莫茍辭。”面對(duì)人最終會(huì)“托體同山阿”這一問題,“形”采取飲酒——自得其樂的方式來處理。當(dāng)他面對(duì)違反自己性情的事用回避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本性,辭官歸田,乞求以退求得自適怡情。試想把農(nóng)耕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方式,在躬耕中找到自適。陶淵明有種“自然”的思想,在這種自然思想的指導(dǎo)下他離開了黑暗的官場(chǎng)。前面提到“形”代表陶淵明自得其樂的處事方式,那么如何得樂呢?那就是走自己的價(jià)值之路。“寧困窮以濟(jì)世,不委曲而累己。”②因此他放棄了建功立業(yè),從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轉(zhuǎn)向個(gè)人情志的滿足。陶淵明在田園歸隱中展現(xiàn)出生命本真狀態(tài),在躬耕中找到了真的我。在《歸去來兮辭》中說:“質(zhì)性自然,非嬌麗所得。”在戰(zhàn)伐不斷、人心奇詭的政壇有了覺今是而昨非之感,回到田園就像久在樊籠的鳥回歸到了大自然的懷抱之中。《歸園田居》(其三)“種豆南山下,草勝豆苗稀。晨興理慌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田園生活不僅使他解決溫飽問題,還從田園中獲得自我的實(shí)現(xiàn),此時(shí)于田中躬耕是他不能在仕途上實(shí)現(xiàn)自我的一種轉(zhuǎn)移。陶淵明的勞作也是他獲得自由的一種方式。
三
官場(chǎng)上的那套是他所摒棄的,而田園生活又不能完全消除他建工立業(yè)的愿望。朱熹在《朱子語類》中說:“隱者多是帶有性負(fù)氣之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又好名。”③陶淵明回歸田園生活后既想以功業(yè)實(shí)現(xiàn)自我價(jià)值的思想又企慕自由的生活,“形”和“影”代表兩種處世態(tài)度,這兩種處世態(tài)度時(shí)常交戰(zhàn),心生痛苦讓他有了解脫的欲望,尋求一種能讓他暫時(shí)忘卻痛苦和悲哀的良藥。如何超越苦難世界和越過生死大關(guān)這個(gè)問題正由于并不能在物質(zhì)世界中現(xiàn)實(shí)地實(shí)現(xiàn),于是落在某種精神——人格理想追求上。于是他有了一種新的處世方式——任自然。看其《神釋》“大鈞無私力,萬物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jié)托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圣人,今復(fù)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能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fù)數(shù)。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俱?立善常所欲,誰當(dāng)為汝譽(yù)?甚念傷吾身,正宜委運(yùn)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yīng)盡便須盡,無復(fù)獨(dú)多慮。”作者在這里將自己所經(jīng)歷的和肯定過的并在前面所采用的兩種處世態(tài)度一起否定了,陶淵明意識(shí)到飲酒傷身,立善無益,都不是正確的處世態(tài)度。人生的最高境界仍在于保持內(nèi)心的寧靜,用委運(yùn)任化的態(tài)度處世,作者在經(jīng)歷長期苦悶后,終于獲取新方式來對(duì)待生活。陶淵明認(rèn)為天道不受人支配,人只能順從“天道”也就是“自然”。自然無可改,順應(yīng)自然是一種明智之舉,身處亂世不被異化的一種方式。用“形”、“神”的處事態(tài)度來面對(duì)實(shí)際人產(chǎn)生困惑苦惱時(shí),“神”的這種方式可以解其惑,獲得一種不喜不懼的寧靜。
注釋:
①冷金成.《中國文學(xué)的歷史與審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
②袁行霈.《陶淵明詩文箋注》北京:中華書局
③朱熹.《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參考文獻(xiàn):
[1]古典文學(xué)資料匯編·陶淵明卷[M].北京:中華書局,1965.
[2]袁行霈.陶淵明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
[3]冷金成.中國文學(xué)的歷史與審美[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9.
[4]袁行霈.陶淵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
[5]朱熹.朱子語類[M].北京:中華書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