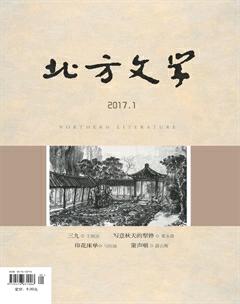從聲調演變史看方言中調值變化現象
李琰
摘要:聲調是依附在音節上的超音段成分,主要由音高構成;現代普通話中,全部字音分屬四種基本調值:高平調、高升調、降升調、全降調,聲調調值變化主要是由聲母的變化造成。從中古音到現代漢語,聲調變化可以總結為:平分陰陽,濁上歸去,入派四聲。
關鍵詞:聲調演變史;調值;音韻
普通話中,大約有400多個基本音節,因此,聲調在區別意義方面有重大作用,聲調與聲母、韻母的地位同樣重要,漢語是一種有聲調的語言,這也是與世界其他語言具有區別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聲調是指有區別意義作用的音節高低升降變化,調值指依附在音節里高低升降的音高變化的固定格式,也就是聲調的實際音值或讀法,一般采用趙元任創制的“五度標記法”來標記聲調。調值的語音特點有二:第一,調值主要由音高構成,音的高低決定于頻率的高低;比如,男女生理結構不同,聲帶有別,男生聲音更加低沉粗重,女生聲音更加高亢尖細,因此,雖然讀同一個詞語音高格式相同,但是,具體數值卻不同。第二,構成調值的相對音高在讀音上是連續的、漸變的,中間沒有停頓,沒有跳躍。
考察上古聲調主要是《詩經》用韻,從押韻的角度看,《詩經》主要是同調相押,表現出聲調之別。從《詩經》用韻看,聲調大體為平上入三聲,而去聲猶在萌芽,尚未形成一個獨立的調類。王力先生提出上古音調可分為舒促兩類,舒聲有平聲、上聲,促聲有長入、短入。中古時期,聲調有“平、上、去、入”四聲,而《切韻》、《廣韻》等都是按照四聲分韻。在我國南朝齊梁之際,受佛教轉讀佛經聲調影響,開始用宮商角徽羽五音讀音,隨后,出現平上去人四聲,并且廣泛應用于詩歌創作和韻書編制等各個領域。因為平聲長且平,而其它三聲或轉折或急促,所以又被分為平仄兩大類;在古代詩詞創作中有規律地交替使用這兩大類,可使詩詞音調抑揚頓挫,悅耳動聽,使人有音樂旋律的美感。周德清在《中原音韻》中明確指出,近代音的聲調分為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這與現代北京話四聲大體相同。概括地講,近代音聲調特點是:平分陰陽,濁上歸去,入派三聲。在《廣韻》時代只有一個平聲調類,到現代分化為陰平和陽平兩個調類,這就是“平分陰陽”。平聲分化以聲母的清濁為條件,清聲母字(包括全清和次清)變成了陰平,濁聲母字(包括全濁和次濁)變成了陽平;而古清聲母平聲字今為陰平調,古清聲母平聲字今為陰平調,古次濁聲母平聲字今為陽平調。“濁上歸去”這里的“濁”指全濁聲母,不包括次濁聲母;全濁上聲變為去聲,早在唐代已經開始,在宋代成為一種規律普遍開來。全濁上聲變為去聲之后,上聲字減少了,去聲字增多了。所以今天普通話中上聲字較少,其中更是罕見古全濁聲母字。隨著入聲韻的消失,入聲字歸到陰聲韻,它們的入聲調也就消失了,分別歸入了平聲(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這就是所謂的“入派三聲”。總的看來,古全濁的入聲字變入今天普通話陽平、次濁入聲字變入去聲,清音聲母的入聲字分別派入陰平、陽平、上聲及去聲,沒有十分嚴格的規律。
在中國方言中,調值是有區別的。以北方方言中的吉林地區為例,長春的陰平為44,陽平為24,陰上為213,陰去為52,沒有入聲;白城的陰平為33,通化的陰平為323,其余相同。
研究表明,聲調與聲母變化是互相影響的,聲調的變化是由于聲母的變化造成的。由上古音到中古音,聲母發生轉變,具體如下:第一,輕唇音產生,早期聲母系統沒有“非敷奉微”四個輕唇音,到三十六字母時代,輕、重唇音才分開。第二,舌上音產生。第三,莊組與章組合流。第四,喻三(云)、喻四(以)的合流。中古音在《中原音韻》產生分并,聲母系統特點如下:第一,濁音清化,漢語共同語的聲母系統趨于簡化,其中最普遍的一個規律是濁音清化,即除了次濁聲母外,所有的全濁聲母都變成了清音。第二,輕唇音非敷奉合并,中古音系里,輕唇音還未從重唇音內分化出來,到了《中原音韻》時代,非敷奉合并為唇齒擦音[ f ]。第三,零聲母字增加,中古時代零聲母只有一個影母,而在《中原音韻》里疑、影、云、以聲母增加為零聲母,明代蘭茂的《早梅詩》更是確定了這幾個零聲母。第四,知、莊、章三組合流。第五,見、精系三、四等字尚未腭化。從近代到現代聲母也發生變化,舌面音產生,微母消失。從此,現代漢語普通話聲母系統形成。
正是因為聲母系統在不斷變化,導致聲調調值的變化,二者互相影響,互相推進;在演變過程中,由于地域性原因,或保留,或丟失一部分的內容,所以,不同地區有不同方言,不同方言之間的調值也存在著差異。因此,分析聲調演變史,從而了解其中規律,如此一來,對看待方言中調值變化有著重要的意義。通過諸如此類的研究,把握不同地區,不同方言間包括調值的差異等等問題和方向,對不光方言乃至整個語言學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正如前文所述,由于聲母系統在不斷變化,導致聲調調值的變化,二者互相影響,互相推進;在演變過程中,地域性原因,導致聲調調類的一些變化,這恰好體現了文章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