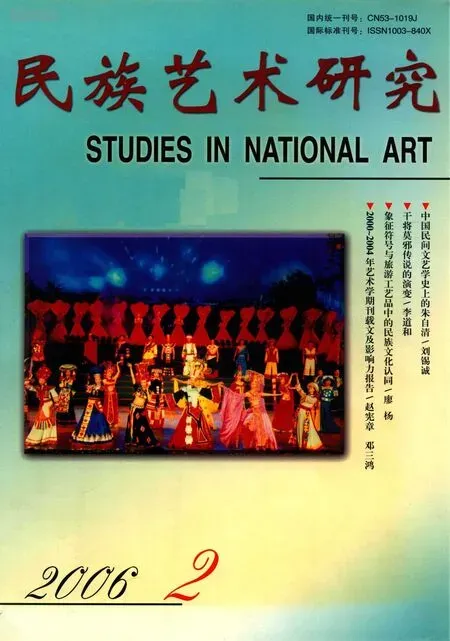中國傳統舞蹈批評特征及模式芻議
慕 羽
中國傳統舞蹈批評特征及模式芻議
慕 羽
中國傳統舞蹈批評與西方傳統舞蹈批評相比,中國古代舞評與“新聞業”并無關系,同時還存在一種差異很大的現象:即舞評與整體性文論不可分割。本文嘗試以國際視野來探討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旨在從歷史中探尋出規律,即找尋出中國傳統舞蹈批評的模式,這既能夠與古時中國的舞蹈藝術形態相符,也有對現代批評的邏輯架構分析在其中。由于中國傳統藝術批評模式有其特殊性,并沒有形成“作品-世界-藝術家-觀眾”那樣明確且成體系的螺旋式循環結構,所以回顧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本文總結出五種模式:倫理道德批評、“泛宇宙生命化”批評、“本體論”批評、“人化”批評、社會批評等。
舞蹈批評;模式;新聞業;傳統文論;艾布拉姆斯
舞蹈,是一種憑借人類與生俱來的身體來揭示人類情感和精神領域的特殊的藝術活動;舞蹈批評既包括揭示其身心靈合一的內部規律分析,也與闡釋它和人類其他社會實踐聯系的外部規律研究密切相關。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中國的傳統舞蹈批評。文中“傳統”二字是針對“批評”而言的,即中國新聞出版業“舞評”肇始之前的舞蹈批評。中國對樂舞進行評論的歷史有它自己獨特的模式和傳播方式,也比西方的芭蕾舞評早兩千余年。由于歐洲浪漫主義芭蕾時期,正值商業報刊時代的到來,古典芭蕾的舞評便與新聞業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雖然中國的活字印刷術比歐洲早四百年,但是這種聯系在中國并沒有建立起來。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對于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模式的研究,筆者借鑒的是艾布拉姆斯關于文藝批評的邏輯,以作品的存在為核心,連接世界、作者、讀者,便可以建立起舞蹈批評模式的諸坐標。雖然并不能直接將它套用于研究中國古代舞蹈批評模式,但我們仍能夠從中發現一些規律。
一、中國古代舞蹈批評與新聞業無關
對比中外舞評史,有一種關系差異很大:即舞評與新聞業的關系。雖然造紙術和印刷術都是中國古人發明的,但出于非拼音文字等原因,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術卻難堪大用,加之信息傳播受君主專制完全主宰,以及故步自封的社會意識等本質原因,中國古代雖有“印刷業”,卻沒有產生真正意義上的“新聞業”,所以中國古代文藝批評與“新聞業”并無關系。中國古代新聞主要靠官方“手寫”、驛站傳送。中國早期的印刷品多為佛經經咒,所謂的“新聞”則只是服務于朝廷的“手寫官報”。而古代的“邸報”并未衍變為近代報紙,近代出現的報刊其實是西方的“舶來品”。然而,15世紀西方的印刷業從《圣經》開篇,最終觸發了新聞傳播業,以及相繼到來的藝術批評行業,也見證了西方古典芭蕾重要的轉型和發展歷史。當然,中國正統的樂舞歷史更加源遠流長,因此我們要追溯的“舞評”歷史也就更為久遠。
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有一個很著名的命題——“軸心時代”。在《歷史的起源與目標》(1949)一書中,他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時出現在中國、西方和印度等地區的人類文化突破現象稱之為“軸心時代”,這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
不幸的是,中國正統的古典樂舞沒有完全得以在歷史中延續;但幸運的是,中國兩千余年的樂舞文化卻是實實在在的,且有哲人先賢的“記錄在案”為起點,稱頌、質疑、寄語,他們的思想也一直影響著中國樂舞文化。還有那些寶貴的詩詞歌賦,尤其是部分同文人雅趣及其生活空間有密切聯系的舞蹈詩歌,共同構成了中國人的舞蹈記憶。
雖然有墻上題詩,還有抄寫和刻印,但中國古代詩歌、小說主要靠的是“口耳相傳”。即便印刷術宋代發明了,唐詩傳到明代,也已失傳了不少。“孤篇壓全唐”的張若虛難道就只寫了《春江花月夜》等一兩首詩嗎?還是其早已隨歷史煙消云散?我們不得而知。這里要特別感謝那些歷史上慧眼識珠的“編輯們”,中外歷史上都有這樣的“發現家”,他們結集付梓或秉承遺志,或肩負歷史使命,或堅守畢生信念。比如明代的藏書家、文學家胡震亨,十年時間編了一本《唐音統簽》,才談得上清康熙年間轟動朝野的《全唐詩》,當代學者們才有可能去整理研究《全唐詩中的樂舞資料》(1958/音樂出版社)。
失傳的不只是詩歌,更有無法保留的舞蹈本身。舞蹈這門時間的藝術,永遠都只存于瞬間就不復存在的“當下”。就像宋人感慨“今日所舞《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①沈括:《夢溪筆談·樂律一》。,可如今呢?正如泰戈爾所言,“天空不留痕跡,飛鳥已經掠過。”②泰戈爾《流螢集》的第101篇。
進行廣義上舞蹈史的研究,考察的研究對象除了活態的“遺存”,還可以有文字記載、壁畫、石刻、磚刻、拓片、器皿的形象,對于舞蹈批評史的考察則主要集中于文字記載。后代舞蹈學者對于古代舞蹈史的研究都很多,而專門論及舞蹈批評史的角度還是比較新的。中國傳統舞評(或因子)的存在形態豐富多樣,比如:先秦諸子的語錄文集、專論、漢賦、唐詩、宋詞、類書、史書、專著等。切忌深文周納,借鑒一些方法論,考察舞蹈文本在特定語境中的原初含義,還是很有意義的,這也算是研究中國舞蹈批評史的起步。
晚唐時期,理論家張彥遠在中國第一部繪畫通史《歷代名畫記》的編著中就涉及過批評史的內容;民國時代,我國也已有學者撰寫出版過現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而且涌現了一批學貫中西的學者從事文學批評和批評史的研究。但是,中國藝術和各門類批評史的研究還沒有形成規模。對中國舞蹈批評而言,我們不僅要研究西方文藝批評和舞蹈批評在中國的影響,更應該著墨于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論和文學中,尋出古代舞蹈批評的形態,這也是中國現當代舞蹈批評的文化基石。換句話說,我們研究中國舞蹈批評史,不是去陳述文論史、詩歌史,而是從浩如煙海的資料中找出符合“舞評”特點的篇章,總結出中國傳統“舞評”的規律,以及有關對現當代舞評會產生學術影響的理論根據。
二、中國古代舞蹈批評與文論的關系
相對于舞蹈史論研究總結歸納宏觀創作特點和規律,舞蹈批評常常對微觀創作展開描述、分析、判斷或評價,這并不是說理論家和歷史學家不做這樣的事情,但是他們往往基于不同原因。可以說,舞評即便關注的是歷史上的作品,也要突出“當代”和“現在進行時”,也更為強調舞評人的主體視角。
在一定意義上,舞蹈史是宏觀性的舞蹈評論,豐富的舞蹈史知識則為舞蹈理論和舞蹈評論的發展提供厚實的學術根據。舞蹈批評不但為舞蹈理論提供啟示,還為舞蹈史提供資料的積累和評價的參照。舞蹈理論是實踐的升華,也對舞蹈批評和舞蹈史研究產生指導的作用;舞蹈批評運用理論(原理和外延理論)對舞蹈作品進行分析,同時還可檢驗、論證理論,必然也面臨著舞蹈理論研究方式的轉型和創新,或是重新發現。
比如:如今我們評判中國古典樂舞作品重建或創作,距今一千五百年歷史的謝赫之“六法論”仍不失為衡量古典舞蹈創作和評論的重要法門之一。“謝赫六法”并不止于成為古代美術作品品評的標準和重要美學原則,它完全可以生發出我們對傳統樂舞意境的一種解讀,還可能產生當代意義。而一些頭腦中“不分中西古今”的當代藝術家、理論家則可以對六法中“氣韻生動”的理念,或根據主客相融的體驗,或基于“主體間性”的考量進行新的運用。
筆者希望嘗試探尋舞蹈的文脈,即特殊藝術學——舞蹈學研究中舞蹈批評的歷史蹤跡,這是對歷史上的具體舞蹈作品和現象的直接探討,并不側重探尋中國傳統樂舞藝術的一般規律。換句話說,中國舞蹈批評史(傳統部分)關注的文章,是對“正在上演”或“同時代”的樂舞、舞蹈或戲曲作品及其現象進行的分析闡釋、評價,重視“舞評人”的主體性。比如:
對于舞蹈作品的描述和藝術評價彰顯了舞蹈人和觀舞者怎樣的心境,結合了怎樣的哲學或美學理論?(文藝評論共性/舞評的對象和理論坐標的關系)
從“樂”到“戲曲”,中國古代舞蹈在多數情況下并沒獨立存在,對于綜合形態下的舞蹈,先哲或文學家們都給予了怎樣的關注?對舞蹈發展產生了怎樣的深遠影響?(中國舞評特性)
中國古代舞蹈史上,何時何地何因讓何人寫了相對獨立的“舞評”?是否有獨立性的舞蹈批評范疇?(舞評本體和主體)
中國舞蹈史上,不同歷史時期的“舞評”是以怎樣的方式出現并存在的?(舞評本體)
中國舞蹈史上,何時何地何因讓何人寫了現代意義上的“舞評”?(舞評本體)
你認為中國舞評有無取得與文學批評、書畫批評、音樂批評、戲劇批評等相匹配的地位?為何?歷史上是如何互動的?特定朝代或時代中,舞蹈是否圍繞著同樣的文化命題展開?
正如學者指出,“中國的文學批評著作實際上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史著作,它們把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混為一談,成就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混合史。”[1](P3)其實,這種現象在西方也存在,被認為是文藝批評寶典式的專著卻叫作《文學理論》(韋勒克、沃倫),只是門類批評仍然是獨立而顯性的。
可以說,對比中外舞評史,還有一個差異很大的現象:即舞評與整體性文論的關系。而且中國古代文論還有“文史哲不分家”的特點,中國舞蹈批評史也是如此,武舞同源,詩書畫論也呈一體,尤其是漢代以后,樂舞與書畫在抒情寫志的許多理念上都是貫通的。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畫論、書論對中國舞蹈審美和舞評范疇有直接影響。“樂記”“樂論”“詩品”“書品”“畫品”“曲律”“琴況”“藝概”……與“舞學”都有整體性文化淵源。而南朝齊梁劉勰(約465-520年)《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學批評上則有其特殊地位,“六觀說”對各門類藝術批評都有很好的參考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留日歸來的王國維(1877-1927)超越中國固有的批評傳統,將西方哲學、美學觀念和邏輯思維融入中國詩論傳統中,形成了獨特的中國批評體系。學者認為,王國維的藝術批評是中國現代藝術批評的開篇和發軔。[1](P539)
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舞蹈大多因“媚權”(禮樂)或“媚俗”(女樂)而存在。對于“禮樂”和“女樂”這兩種最具代表性的宮廷樂舞,古代先賢們從各自不同的角度進行評述,值得我們今天重讀品鑒。而所謂“天樂”“上樂”通常只是圣人君子雅士的理想,現實無跡可尋。“禮樂”奠定了中華的“禮儀之邦”,卻因“禮崩樂壞”而失傳,其后只能陷入隨“改朝換代”而來的復興與衰落的循環中,被不斷改造,而且距“為仁由己”的“禮樂之情”已經相距甚遠。“女樂”才是中國傳統樂舞的主流形態。中國古代舞蹈史中許多舞蹈家都是帝寵、王寵。唐代也是樂伎舞蹈的全盛時期,白居易等人就曾對宮中“雅音替壞”“鄭聲奪雅”現象表示過不滿,寫詩借樂舞來諷喻現實,其實他本身非常熱衷樂舞,自己也家養樂伎。當時能歌善舞的樂伎遍及社會的各個階層:宮廷有宮伎、軍營有軍伎、官府有官伎、私家有私伎。女舞人需要依靠自身的美色和技藝來謀生。女樂為中國舞蹈藝術的初步形成創下卓著功勛,但在當時的社會中,女樂的地位很低下,常被當作玩賞娛樂或作為政治陰謀的工具,并不被正統文化所接納和肯定。
而舞蹈這一體裁的轉型,歸根到底是被中國市民文化轉型決定的。戲曲已經不只是服務于王公貴族、豪門內府、文人雅士的“樂舞”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作為一種市民文藝開始日漸“商品化”和“職業化”。
所以,當我們以國際視野來探討中國舞蹈批評時,既需要借鑒學科分類觀,還要注意到中國傳統樂舞和戲曲的自成一體,而且相關歷史、理論和評論還與文學和其他門類藝術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
實際上,有學者認為,與士大夫作為創作主體,“詩詞散文等傳統文學與繪畫書法等精英藝術”不同,舞蹈等主要由下層民眾參與創作的藝術,屬于“通俗性、技藝性的文藝門類”,而諸如“宋學理想人格的影響力主要作用于精英文藝(例如詩文繪畫等雅文化),投射進民眾文藝領域就相對淡薄(或有謳歌理想人格的話本或戲劇)。”[2]
到了元代,一些受到現實排擠的落魄儒士,只好選擇醉心于雜劇的創作中,讓通俗化的民間文藝承載知識分子的現實吶喊,但這個時期的舞蹈已經轉型為“雜劇”的一個元素了。元雜劇的表演已是以演員的“唱”為本位。首次論及戲曲表演的胡祗遹(1227-1295)之“九美說”中,涉及形體動作表演的只有“分付顧盼,使人人解悟”。①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八《黃氏詩卷序》。明代戲曲評論家、詩人潘之恒(約1536-1621)提出的戲曲表演“度、思、呼、步、嘆”的幾個方面中,所謂“步之有關于劇”,②潘之恒《鸞嘯小品》之《與楊超超評劇五則》。“步”可以看作是與古代樂舞有流變關系的戲曲舞蹈,更是“合規矩中節奏”的戲劇行動。十分難得的是,明王室成員——有“律圣”之稱的朱載堉(1536-1611)在不興舞的年代提出了“論舞學不可廢”,成為中國古代雅正樂舞系統研究并實踐的集大成者。
此后,便鮮有人問津了。“古之君子,生而未嘗不學舞,燕(宴)而未嘗不起舞”,不過社會各階層越來越“恥于樂舞”,也不愿與舞人“為伍、坐作、進退”。③朱載堉《樂律全書》卷十九《律呂精義外篇》卷之九《論舞學不可廢》。其后又引用了《宋史·樂志》中的一段史實,說明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年),曾下詔“選國子生教習二舞”,但人們都“恥于樂舞”,皇帝也不得不作罷。對于文人而言,正如明末清初詩人、醉心于戲曲創作的吳偉業(1609-1672)所言:“今之傳奇,即古者歌舞之變也;然其感動人心,較昔之歌舞更顯而暢矣。”④吳偉業為明末清初李玉的《北詞廣正譜》作的序。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從古時對女樂沉湎到近代戲曲評論,基本是以“品賞色藝、玩味伶人”為核心特征的。[3]難怪舞蹈學者發出感慨:“自清以降,稍有名氣的文士似乎都不屑于歌舞了;我們能憶起的,大約只有聞一多。”[4](P144)其實,民國時代,林語堂對鄧肯現代舞的關注仍是可圈可點的。值得一提的還有1934年,在上海從事書籍裝幀設計工作的錢君匋(1907-1998)出版了《中國古代跳舞史》一書,在西方舞蹈風靡之際,讓曾“以舞為恥”的國人重新回望古代,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錢老后來成為集詩、書、畫、印熔于一身的藝術家,有著這樣一位藝術家重新審視歷史,也算舞蹈之幸。
三、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模式探討
進入20世紀后,現實中的中國舞蹈要成為一門獨立的劇場藝術,還有一段路要走。因為舞蹈這位“藝術之母”一直努力尋求獲得應有的尊重,既不是作為政教工具,也不是作為享樂工具,而是與人類精神生活和生命觀相通的一門藝術。從古至今,都可以尋出一條軌跡。比如我們可以去探討中國歷史上所出現的三次思想高峰,即春秋百家爭鳴、宋代理學、清末民初的啟蒙民主思想等不同時期里,舞蹈的現實與理想的關系。我們還可以探討中國古代舞蹈發展的高峰(西周和漢、唐)與文化發展的關系問題等。
相對而言,中國傳統藝術的基礎為哲學,西方傳統藝術的基礎為科學,但對于舞蹈藝術的研究,中西都偏向于“哲學式”。值得一提的是,中西對“哲學”的認知本身又是不同的。西方人的“哲學觀”源自古希臘人的“愛智慧”,“哲學家”不僅僅“有智慧”,或才華超群,而是一些超越現實名利而摯愛智慧的人。古希臘人還將這種思考自然與人生的“愛智慧”方式體系化了,后又經過發展轉化,形成了嚴密邏輯系統的宇宙觀。中國有許多先哲都曾做過哲學性探討,但中文中的“哲學”是19世紀日本學者的發明,中國古人稱其為“道”“道術”“經學”“玄學”“道學”“理學”“心學”等,確未形成系統而思辨的注重論證的哲學。對此,中國哲學泰斗馮友蘭先生也是有定論的。[5](P7)
中國人自己的儒學觀、道家觀、佛學觀,以及儒釋道的融合也致力于研究天人關系和歷史規律,尤其重視世界觀與倫理的聯系,深信“內圣外王”之道,內圣即立德,外王即立功[6],因此注重“實用理性”(李澤厚語)的中國哲學自成一派。后人將中國古代哲人的思想進行理性思辨和形而上學的分析整理,也逐漸形成了可以與西方對話的哲學和美學體系,比如本體論、方法論、認識論、價值觀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自先秦形成的文藝批評有兩大特點:一是具有從現實出發的品格;二是從整體性文化批評出發來進行具體的文藝批評。[7]
中國傳統批評文論中體現出了兩條主線,即儒家和道家文藝批評思想,馮友蘭將其類比為西方文藝思潮中的“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8](P19)但二者本質不同,文藝思潮歸根結底是一種藝術現象,它體現了藝術自身內部的規律性運動和發展。中國古代只存在一些代表個人意識覺醒的文藝思想作用于舞蹈。
有意思的是,中西歷史上對于傳統舞蹈的批評,思想家和文學家們都是動用了強大的直覺感悟,并以詩化的語言和形象化比喻來詠嘆舞蹈。在中國古典文論、樂論以及詩歌中,不乏精妙絕倫的樂舞過程的描繪和詩人的體悟。那么,我們可否探尋出作品(或現象)與宇宙、作家、讀者,以及作品內部等西方批評形態結構的共通點與不同點呢?筆者希望論及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時,要在各門類藝術批評和文學批評集合中尋找出一些既符合中國舞蹈在古時的藝術形態,也有現代批評的邏輯架構在其中的規律。
美國當代著名文學批評理論家——艾布拉姆斯(M.H.Abrams,1912-2015)的名作《鏡與燈》(1953)看似只是論述西方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實際上艾氏關于文學四要素:作品、世界、作者、讀者(work/universe/artist/audience)的勾勒,以及藝術批評結構系統的理論,可以看作是西方文學批評形態研究的另一個典范,對舞蹈批評學的形態建構也很有啟發性。
學者蒲震元將此種研究稱為“藝術批評模式”,“是特定民族(或民族群體)的文化模式及深層審美心理結構在藝術批評理論領域中的反映與應用”,并指出:“中國傳統藝術批評存在深度模式與潛體系,它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大宇宙生命和諧理論為哲學根基(特別是以‘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這一重要理論認識為基礎),在象(藝術形象、藝術符號及與之有關的大量‘事象’)、氣(氣韻)、道(生命觀)逐層升華而又融通合一的多層次批評中,體現中華民族深層人生境界及大宇宙生命整體性特征的東方藝術批評模式。”[9]即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從中發現一些批評模式的區分,強調著“樂”的社會功能和“人格本體”。其實,稱得上“妙品”“神品”的舞評即便寫舞也都不為寫舞本身,而隱含著更多的人情、人性和社會之思。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傳統的藝術批評模式更有其特殊性,比如“六觀說”“形神論”“氣象說”“意象說”等都涉及全方位的探討。因為中國美學要求藝術作品的境界是一全幅的天地,葉朗表示,中國古典美學的秘密不在表現論或模仿說,而在“元氣論”。[10]
老莊哲學的根本在于“道”,而《周易》的實質是“象”“易者象也”“圣人立象以盡意”“取象比類”“觀物取象”。探求“象”的方法,不在于西方“模仿論”那樣的“鏡子說”,而是在天地萬物的觀察與模仿中,模擬世界的“簡易、變易、不易”,尋求精神之象,規律之象,“天人合一”之象,可以看作中國古代的“表現說”,不過又根本不同,其中必少不了“元氣”。中國的傳統藝術本來就具有符號化、抽象化的特點,而舞蹈就像是“身體書法”,供表演者和觀賞者聯想的空間非常大。在“現實主義美學”為主體的當今中國舞蹈界,回望祖先的歷史日漸可貴。
可以說,與現代批評模式不同,中國傳統樂舞批評模式并沒有形成“作品-世界-藝術家-觀眾”那樣明確且成體系的螺旋式循環結構,大都側重于作品(或樂舞現象)與世界關系的宏觀探討,但同時也會涉及與“作樂者”以及與“接受者”的關系,卻根本不同于“模仿論”和“接受批評”。
另外,中國傳統舞蹈批評注重直覺與經驗,甚至是不可言傳、只可意會的妙悟,少有邏輯闡釋。加之我國古漢語詞匯蘊含豐富,先哲帝王雅士文人各有各的理解和解釋,理論性和系統性不強。
回顧中國傳統舞蹈批評,筆者總結出了以下幾種模式:
其一,制禮作樂:倫理道德批評。對中國樂舞而言,儒家學說主導著中國宮廷樂舞發展的主流。儒家先哲的樂舞批評模式實際上就是倫理道德批評模式,是內外部結合的批評,著眼點是樂舞與世界的外在關系,即“人倫”。它以一定的道德意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倫理關系作為規范來評價作品,以善惡為基本尺度來決定批評對象的取舍。[11](P356)樂舞批評的標準隨時代的變化而呈現出差異性,樂舞批評的對象既有具體的作品,也有“禮樂”和“女樂”現象。
其二,天人合一:“泛宇宙生命化”批評。雖然儒家美學千百年來深深植根于中國正統舞蹈的發展中,但不容否認的是,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審美的確審視出中國藝術精神的一種純粹美,這是一種觀念形態批評。有意思的是,先秦儒家后期的代表人物荀子的《樂論》中已經呈現出了天人觀的基本立場,儒道兩種思想在“天人合一”上殊途同歸了。
其三,抒情顯志:舞蹈“本體論”批評。漢代樂舞創作實踐十分豐富,雖然并未產生具有像《樂記》般研究“樂”的系統著作,也未有軸心時代的千年大師出現,但門類藝術理論、批評,比如畫論、書法理論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甚至出現了與現代意義上的藝術批評性質契合的文章。值得一提的是,漢代也出現了專門的舞蹈批評,而且還是文學藝術性極強的“賦”,辭藻華麗、意象壯美、氣魄宏大。對此,宗白華是這樣評價的:“在傅毅《舞賦》里見到漢代的歌舞達到這樣美妙而高超的境界。中國古代舞女塑造了這一形象,由傅毅替我們傳達下來。它的高超美妙,比起希臘人塑造的女神像來,具有她們的高貴,卻比她們更活潑、更華美、更有神。”[12](P170)中國古代的“本體論”舞評以描繪見長,也包括了闡釋、評價,有抒情顯志的特點。東漢時期,中國的書法、樂舞都超越了現實的實用功能,審美價值凸顯,說古代舞蹈藝術創作曾走向“自覺”,也是不夸張的。只是書畫創作和賞鑒可以被賦予“人化”的想象,但讓文人雅士真正面對女樂,卻是不容易超越感官層面的。
其四,人物品藻:“人化”批評。雖然“感物而動”“情動于中”“致樂治心”的儒家樂舞觀已經涉及人的本性,但仍然是從現實關懷為出發點的,側重于作為社會人自身品格修養的完善,與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主體性意識并不一樣。而莊子超越現實功利的“天樂觀”可被看成是一種觀念形態的文藝批評,雖是理想人生,卻具有強烈的現實反思精神。這兩種人文精神脈絡一直持續至兩漢,影響著文學與藝術批評。
這里借用了“人化”批評一詞,源于錢鐘書先生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一文。人化批評是“移情作用發達到最高點的產物”,中國文人雅士畫人、畫山水,吟詩詠詞實際上是在表達他們自己,精、氣、神、骨、肉、血無不游走于文藝家的筆端,而這種文氣風骨也同樣能感染到品詩、品書、品畫之人。但是,中國古代能在舞蹈著的真正的人身上體悟到“人化”的文人雅士還真不多,若只是體驗到文武健軟、剛柔相濟的審美,當然還談不上是“人化”,筆者認為“人化”的核心與生命內涵相關,尤其關乎精神自由,才能達到錢鐘書先生所言“文跟人無分彼此,混同一氣”的境界。
比如:在唐朝,能被稱為思與神合之“神品”舞評的,怕是只有唐中期李白那些“大音”或“天樂”理想的詩篇,正所謂“大音自成曲,但奏無弦琴”,①李白詩《贈臨洺縣令皓弟》,被選入《全唐詩》的第168卷第28首。或是“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②李白詩《草書歌行》。李白對懷素的書法評價極高。從古至今,萬事到了極致的水平都要靠天生的才能。何必要像張旭一樣,要觀看公孫大娘《渾脫》劍舞才有所啟發呢?后人對《草書歌行》是否系李白所作,一直存在爭論。……而且,李白(701-762)也有不少十分率性地描寫自己“起舞拂長劍”③李白詩《酬崔五郎中》:“起舞拂長劍,四座皆揚眉。”的詩歌。這個“太白星”下凡的神仙是以出世之心、行入世之道嗎?實際上,自號“青蓮居士”的李白就是一位不出家的信佛者,在詩作中也體現了儒、佛、道三種思想的自然融合。不同于唐后期以禪宗南宗“頓悟”的思想為主,李白“鐵杵磨針”的故事仿佛折射出了他的禪宗北宗“漸修”觀。
其五,人生態度:社會批評。唐詩舞評中給筆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表演與體驗都成為對于各自生存意義的現實領悟和生命的直覺體驗。《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杜甫)、《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白居易)這兩篇堪稱中國舞蹈批評的古典范本,竟然出自現實派詩人之手。換句話說,唐代“劍舞”與唐代書法、繪畫追求“道家”風范是一體的,《霓裳羽衣舞》也是唐玄宗為祭獻老子所作,而舞評既體現了詩人的直覺,傳遞出了劍舞崇尚自然的自由意象,更直通詩人彼時的真實心境,道出了世道滄桑。
如果說,倫理道德批評模式更多體現為“上以風化下”,社會批評模式則體現為“下以風刺上”。而在天人合一的“泛宇宙生命化”批評模式中,對道家而言的“天樂”,對儒家繼承者而言,則逐漸成為“天理”,化為制禮作樂的依據,“樂”與“禮”猶如硬幣的兩面相互依存,即所謂“禮樂相須以為用”。④《禮記·月令》:“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對禮樂的“舞學”探討也成就了其本體論意義。
除了對舞蹈本體的提點,“抒情顯志”和“人物品藻”的批評模式因其“去意識形態化”而成為中國傳統舞蹈批評的亮點,不過,它們雖觸及了舞蹈表演者(也有可能是編創者)的身份或心理,關注了人格、性情因素,但側重表達的仍是作品(或樂舞現象)與接受者的關系,而一切又著實為了表達與世界的關系,這在某種程度上又回歸了社會倫理道德批評。可以說,中國傳統舞蹈的“本體論”批評尚未充分開掘,而涉及舞蹈創作主體的“主體論”批評則基本缺席,當然這也說明了中國傳統樂舞并不具有真正的創作“主體性”。
(責任編輯 唐白晶)
[1]凌繼堯主編.中國藝術批評史[M].沈陽:遼寧美術出版社,2013.
l ing Jiyao(eds),History of Chinese Artistic Criticism,Shenyang:l iaoning Fine Arts Publishing House,2013
[2]虞云國.唐宋變革視野中文學藝術的轉型[J].社會科學,2010,(9).
Yu Yunguo,The Transformation of l iterature and Ar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ang-Song Revolution,Social Sciences,No 9,2010
[3]張潛,龔元.“劇評”的興起——現代話劇史“劇評”問題研究[J].戲劇藝術,2015,(1)
Zhang Qian and Gong Yuan,The Emergence of Opera Review:Study of the Issues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Opera Review,Drama Arts,No 1,2015
[4]于平.中外舞蹈思想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
Yu Ping,General on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and Foreign Dance,Beijing:People's Music Press,2002
[5]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
Feng Youlan,Chines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ume one),Shanghai:Eastern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0
[6]柴文華.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觀——紀念馮友蘭先生誕辰110周年[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2(1).
Chai Wenhua,On Feng Youlan's Chinese Philosophy View:On the110 Anniversary of Feng Youlan's Birth,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ical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No 32,Vol 1,2005
[7]袁濟喜.論魏晉南北朝文學批評與藝術批評的互滲[J].中國文學研究,2012,(3).
Yuan Jixi,Inter-influences between l iterature Criticism and Artistic Criticism in the Wei,Jin,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No 3,2012
[8]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Feng Youlan,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Beijing:New World Publishing House,2004
[9]蒲震元.中國藝術批評模式初探[J].文藝研究,1999,(3).
Pu Zhenyuan,Prelim inary Discussion on the Chinese Artistic Criticism Patterns,Literature and Arts Studies,No 3,1999
[10]朱平珍.美學要關注人生關注藝術——美學家葉朗訪談[EB/Ol].文藝評論官網,2013-01-21.
Zhu Pingzhen,Aesthetic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People and Art:Interview with AestheticistYe lang,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Website,21 Jan.,2013
[11]童慶炳,李衍柱,曲本陸,等.文學理論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Tong Qinbing,l i Yanzhu,Qu Benlu,Cao Yanhua and Wang Yichuan(eds),Tutorial of Literature Theory,Beijing:Higher Education Press,2008
[12]宗白華.美學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Zong Baihua,Mei Xue San Bu(Roaming in Aesthetics),Shanghai:Shanghai People's Press,1981
[13]艾布拉姆斯(Abrams).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M].酈雅牛,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M.H.Abrams,TheMirror and Lamp: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trans.by l i Yaniu et al.,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3
[14]M.H.Abrams.Orientation of Critical Theories[A].In David lodge(ed).20thCentury l iterary Criticism[C].london:longman.1953,1-23.
Prelim in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Dance Criticism
Mu Yu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dance criticism in China,this paper argues that ancient Chinese dance criticism had no connection to“journalism”,but itwas very closely interlinked with the integrity of philosophical ideas,aesthetic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riticism pattern according to four critical theories from the view point of M H Abrams and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aesthetics and philosophy.Chinese traditionalartcriticism has itsown particularity,which is not in Abrams'frame of artist,work,universe and audience,but is on its own track.This paper is concluded with five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dance criticism in China.
dance criticism,patterns,journalism,traditional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M H Abrams
J705
A
1003-840X(2017)02-0127-08
慕羽,北京舞蹈學院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音樂舞蹈藝術委員會委員。北京100081
http://dx.doi.org/10.21004/issn.1003-840x.2017.02.127
2017-02-26[本刊網址]http://www.ynysyj.org.cn基金課題:本文系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2013-2016)《中國舞蹈批評》的部分成果。
About the author:Mu Yu,Professor at Beijing Dance Academy,Committee Member of the Music Dance Art Committee of China Association of l iterary Art Critics,Beijing 100081
The paper is funded by the follow ing:Part of the results ofMinistry of Education New Century Talent Supporting Plan(2013-2016)Chinese Dance Critic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