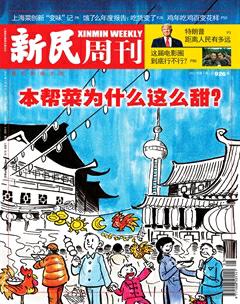地圓說面對的“祖制”堅冰
禾刀
相較于馬戛爾尼的倨傲個性,以及過于突出國別身份對等等禮儀和明確的來訪意圖,利瑪竇等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則顯得靈活得多,更接中國思維地氣。
1793年,急欲敲開中國貿易大門的英國,以為乾隆祝壽為名,派遣使臣馬戛爾尼,帶著數千件禮物(包括不少科學發明),率領龐大的使團不遠萬里來到京城。結果乾隆一句“奇技淫巧”,便將馬戛爾尼帶來的、原本有可能打開中國科學智慧之門的諸多發明深鎖宮廷庫房,僅供個人業余玩樂。
而比馬戛爾尼早192年抵達中國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則憑“一己之力”,讓自己攜帶的科學知識作品——世界地圖在中國廣受歡迎。當然,這并不表明明朝就比清朝開明,只是利瑪竇選擇了一條完全不同于馬戛爾尼的輸入策略。本書正是追溯從明末到清中葉,以利瑪竇等人為代表的西方傳教士將地圓說引入中國的艱難歷程。
“利瑪竇原以佛教僧侶的面貌出現在中國,但在得知僧人的社會地位低下后,便換上儒服。”除了喬裝打扮套近乎,利瑪竇還發現,當時中國上層社會對于基礎科學認識較為膚淺,大都只是用作茶余飯后的談資,利瑪竇于是“將西方的歷算知識轉化為文人清玩,借著士人把玩地圖之際,使這些新知識滲透到士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利瑪竇除了換了身對中國人頗有親近感的儒服外,在宣傳上更是費了好一番腦筋。他“將西方認為地不動的概念和中國傳統‘以德為靜的概念相結合。他以中國的典籍作為回旋的空間,使其地圓的說法可以證諸中國古代的經典”。這樣做雖有悖科學事實,但利瑪竇這一“引經據典”的做法,愣是將地圓說與中國歷史文化掛起鉤來,自然符合當時精英階層中盛行的“西學中源”邏輯。
相較于馬戛爾尼的倨傲個性,以及過于突出國別身份對等等禮儀和明確的來訪意圖,利瑪竇等來到中國的傳教士則顯得靈活得多,更接中國思維地氣。明代科學家李之藻就認為利瑪竇等人是“不婚不宦的傳教士,無所求于世,類似得道之士,他們所說的話應當可信”。
利瑪竇對中國人的準確拿捏處處可見。他為1602年版世界地圖所寫的題詞指出,“天地本身便是一本大書,只有君子能通讀,而參與天地之化育”。甫一看去,這有點《皇帝的新裝》的味道。盡管如此,從官場至民間,中國人對利瑪竇這樣的解釋普遍極為受用。
作為利瑪竇等人輸入“地圓說”的堅定反對者,明末清初的楊光先嚴格意義上并不能算是科學家,更像一位“腐儒”。楊光先包括后來的王夫之等人的反對意見之所以在當時有一定影響力,并不是因為他們在地球形狀的認識問題上真能更勝一籌,而是他們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蓋天”與“渾天”等“祖制”不顧一切的堅定擁護。
就“蓋天”與“渾天”之說受到一些士人的瘋狂支持,祝平一直言不諱地指出,“當時的士人們都意識到了一個新的問題: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秩序已受到挑戰”,“面對西方傳教士,當時的士人不但需要為中國在新的世界觀中定位,也需要護衛天朝秩序賴以奠基的文化傳統”。地圓說最終之所以能被康熙接受,得益于清初學者梅文鼎將歷算定位為純技術問題。梅文鼎的技術化策略,本質上是對“祖制”傳統的智慧剝離。
讓科學的歸科學,這個在今天看來不值一提的問題,在地圓說的輸入過程中卻倍顯艱難曲折,這顯然不能視為一般意義上的傳播學。利瑪竇等人雖肩負傳教重任,但地圓說的科學性本身不容質疑。也并非他們的解釋不能說服眾人,而是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封建傳統思維首先突出的不是積極吸收新知識,而是本能地按照是否有助于固化統治的標準予以取舍。原本有機會搭上西方工業革命快車的乾隆,面對英國使臣遠道送上門的數千件科學發明錯失良機,真正原因應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