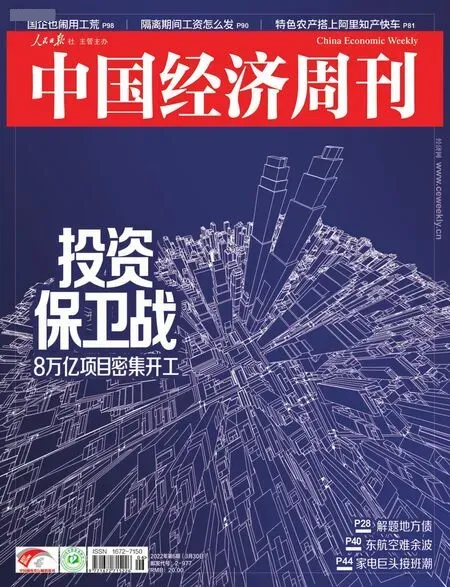臨汾:如何從花果城變成了霾都
張燕
2017年春節,山西臨汾沒怎么聽到煙花爆竹聲。
年初,這個內陸小城“意外”戴上了全國“污染重鎮”的帽子。
1月,臨汾二氧化硫濃度屢屢“爆表”。1月9日、1月12日、1月13日、1月14日,臨汾市南機場附近二氧化硫小時濃度都曾“破千”,可說是“酸霧”鎖城。
環保部督察組、環保部與省政府組織專家組先后深入臨汾調查。
隨后,控硫治污攻堅行動開始,所有工業企業要最大限度地限產限排;所有使用潔凈焦的居民嚴禁燃用散煤,嚴禁燃用和摻混劣質煤,減少二氧化硫排放;市區露天攤點、沿街門店嚴禁使用劣質蜂窩煤及劣質煤焦;市區中心城區155平方公里范圍內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燃放煙花爆竹等等。
據說,臨汾這次受到環保部的通報批評和約談,累計追責了好幾百人,上任沒多久的環保局長也被免了。
春節期間數次親友相聚,酒過三巡,菜過五味之后,“酸霧”都是當之無愧的熱門話題。大部分臨汾土著也是才意識到家鄉的“霾”和其他地方比還很不一樣。
老實說,土著們對這種天氣甚至“都習慣了”。記憶中的天常常是灰蒙蒙一片,夏秋還好,一到了冬春時節,常是濃霧蔽日,不見藍天,空中彌漫著刺鼻的碳味兒,很多人患上了鼻竇炎。“我去武漢上大學后,鼻竇炎自然而然好了。”在新年聚會的時候,一位同學說。
那時,“霧霾”這詞甚至還沒被發明。

圖片來源Iwww.linfen365.com
在煤炭的黃金十年中,臨汾曾是山西省經濟總量排名第二的城市。以煤、焦、鋼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一度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也產生了嚴重的環境污染。2003至2006年,臨汾連續成為中國內地城市的污染前三。
而這些年,正貫穿了我們這一輩人的少年時代。
“說起來,我們一直都是綠蘿。”另一位同學調侃道,大家隨即開始嘻嘻哈哈。
玩笑背后更多的是無奈。長久的霧霾籠罩之下,大家竟也不怎么關注空氣監測值了,口罩也不戴了。如果愿意,人真是可以適應任何一種環境。
造成“酸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臨汾環保部門發布了五大原因:除了焦化、鋼鐵等工業企業存在跑冒滴漏、違法排污外,對散燒煤、燃煤鍋爐污染管控不力是空氣中二氧化硫嚴重超標的重要原因。市區建成區及周邊行政事業單位的86臺、130蒸噸以上燃煤鍋爐基本上無脫硫措施;東城集中供熱沒有安裝在線監測,脫硫裝置形同虛設,等等。
這一點,“業內人士”堂哥比較有話語權。“咱們這兒,市區周邊焦化、鋼鐵企業比較多。從全市整體水平來看,工業燃煤量達到80%~90%以上,基礎濃度高。但實事求是地說,破千和老百姓燒煤關系非常大。”
“工業排放有個特點,是持續穩定地排。假設夜間違規偷排,不會挑重污染天氣排。而且工業排放的影響面要大,全市五六個(觀測)點都要破千,不會是一兩個點破千。但恰恰是其他點都還不是太高,就是南機場那個點破千了,這和民用燒煤關系非常大。” 堂哥說,這個不能回避。
“你看,盡管這兩天(監管)力度非常大了,工業排放控制得比較不錯,路上車這么少,不讓燃煤不讓放炮,但大年三十以后,部分點還是有爆表的情況。”堂哥說。
其實,與2005年前后污染頂峰時期相比,臨汾的空氣也有過一些好轉。2006年開始,市區大量取締周邊煤焦企業,進行城中村改造,上集中供熱、“城中村”燃氣改造等項目。2012年,臨汾還評上了山西省環保示范城市。
“應該說越治理越好,但為啥污染越來越重?”他反問我。
堂哥說,現在是城郊、城中村污染比較厲害,“老百姓燒的煤多了,居住面積也大了,用量增長很快,原來哪舍得燒鍋爐呢?”市區4萬多戶城中村居民沒有集中供暖,也不能不燒煤。市政府花大筆費用配送潔凈焦置換散煤,還是架不住有人“轉手就賣了”,然后偷燒煙煤。
“產業結構、氣象條件不用說了,城市建設跟不上,環保也比較被動。”堂哥感嘆道,“這也是城市病吧,咱小城市病。”
新年總是那么短暫,我又踏上了返京的高鐵,看著窗外昏黃依舊,我心里堵堵的。
其實,記憶中的童年何嘗不是“藍天、白云、紅太陽”。上世紀80年代,臨汾市區規劃種植了柿子樹一條街、石榴樹一條街、梨樹一條街等多條果樹一條街。1982年,《人民日報》曾以“臨汾城被譽為黃土高原花果城”為題對臨汾市做了報道。“花果城”的美譽,一直讓臨汾人引以為傲。
然而如今,柿子樹光禿禿的枝丫上,只剩幾個泛黑的柿子。誰又不想回到那個曾經呢?
希望今年春節能成為家鄉人識霾治霾的一次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