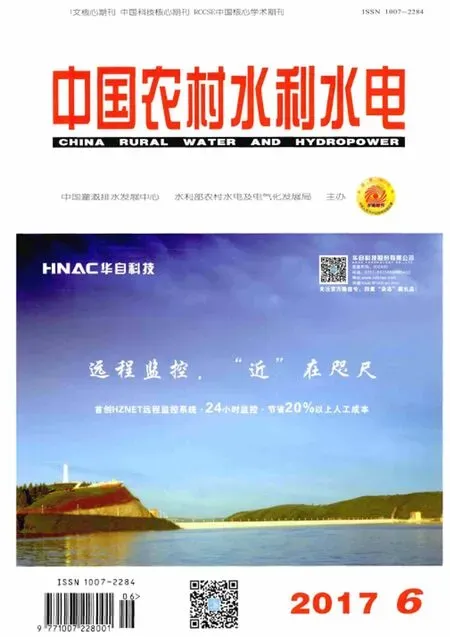襄陽市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評估分析
甘 容,左其亭
(1.鄭州大學水利與環境學院,鄭州 450001; 2.鄭州大學水科學研究中心,鄭州 450001)
河湖水系作為水生態環境的重要載體,是水循環形成的基礎,同時也是流域生態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支撐[1]。然而,受自然營力、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共同作用,河湖水系不斷改變著原有的面貌,對自然生態環境改善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影響較大,這種影響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隨著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人類對水資源的需求越來越高,為了滿足日益增長的用水需求,河流的開發程度也越來越高,使得原有的河湖水系空間格局不斷發生演變。目前,已有國內外學者對不同地區的河湖水系開展了相關研究。陳德超等[2]通過分析上海50 a間的河網水系演變歷程發現,城市化等人類高強度的土地開發,是導致河流消失的直接原因;河道消亡將直接導致河湖水系結構的弱化,進而降低河湖水系的調蓄能力,加重雨洪災害。Seal和Newson認為60%的河湖水系的變化是由城市化引起的[3]。河道疏浚和防滲面的增加使河道徑流量增加,導致干流變寬;而河道淤積和城市化將導致支流逐漸變窄甚至消失[4,5]。陳睿智等[6]提出通過河湖水系連通工程改變天然的水系空間格局,進行跨流域的大范圍水資源時空上的重新分配,是解決我國水資源配置不均的新途徑。河湖水系連通戰略可以提高水資源的統籌調配能力、改善水生態環境、防御旱澇災害,有效解決水多、水少、水臟三大問題,最終實現人水和諧[7]。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與經濟社會發展格局不匹配將是未來研究的挑戰之一[1]。盡管很多學者定性描述了河湖水系的演變,但在高強度人類活動影響下,缺乏從多角度系統揭示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及其影響因素。
襄陽市位于“南水北調”中線水源地丹江口水庫的下游,是鄂西北重要的交通和物流中心,有著承東啟西、暢南接北交通的重要作用。襄陽市境內河流縱橫,水系發育,先后修建水庫943座,總庫容48.7 億m3,大小塘壩4.36萬處,泵站3 228座。盡管大規模的水利工程建設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區域水資源供需矛盾,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但從長遠利益看,可能會對水生態、水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有必要開展襄陽市近年來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特征及其驅動機制研究。
本文以襄陽市為研究區,以遙感和地理信息技術為支撐,從河網水系的數量、結構和連通等方面構建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評估指標,分析新中國成立以來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的演變特征,闡述其影響因素,以期為本市流域水資源的科學管理及河湖水系的均衡管控提供參考依據。
1 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襄陽市位于漢江中游,是湖北省西北部的省城副中心城市,地處東經110°45′~113°43′和北緯31°14′~32°37′之間,總面積1.97 萬km2。襄陽市的地貌,基本呈現“三山六崗一平原”的地形分布。屬于北亞熱帶大陸性季風氣候區,具有南北過渡型氣候特征,四季分明,光熱充足,雨熱同期,冬季寒冷干燥,夏季炎熱多雨。襄陽市境內有大小河流649條,流域面積100 km2以上的有50條,長度在10 km以上的有228條,主要屬于漢江和沮漳河2個流域,見圖1。河湖周圍的人口密度較大、耕地較多、城鎮分布較集中,人水關系密切而復雜。襄陽市地表水資源豐富,全市供水主要依賴地表水資源,地表水供水占總供水量的比例高達94%。

圖1 襄陽市位置及水系分布圖Fig.1 Location of Xiangyang City and river distribution
1.2 數據來源
本文采用盡量沒有云層覆蓋的高空間分辨率的衛星數據,具體數據源為1987年9月、1996年10月、2006年10月的Landsat 4-5 TM及2015年5月Landsat 8 OLI_TIRS遙感影像數據,分辨率為30 m;20世紀60年代、70年代襄陽市地形圖;1985年和2005年《襄陽市水利志》;2005年襄陽市1∶20萬水系圖;Google earth衛星影像圖;DEM(90 m分辨率)。同時先后兩次在襄陽市參加實地考察、資料收集工作,在此過程中對研究區的水系現狀、植被分布、水庫建設、地下水水位和水質等方面進行調查,獲得該區域的第一手資料和襄陽市水利規劃設計院等有關單位提供的多年統計資料。
1.3 研究方法
1.3.1 非遙感數據處理
由于國內可以利用的遙感影像數據主要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為了分析從20世紀50年代到現在襄陽市河湖水系的演變特征,本研究將在2005年襄陽市水系圖及歷史時期地形圖的基礎上,根據水利志及相關資料查詢到的關于襄陽市蓄水工程、引水工程、提水工程及水電工程建設情況,逆推1950、1960、1970及1980年不同時期的水系圖。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1)在ArcMap中加載含有河流水系地形圖的掃描圖,經配準、設置坐標系和投影后,以面或線表示水系相關要素,進行數字化,并完成水系的分級。
(2)以該圖為底圖,結合《襄陽市水利志》記載、不同時期水利建設圖、資料介紹等數據源,分別勾畫出襄陽市1950、1960、1970和1980年的水系圖。
1.3.2 遙感數據處理
使用遙感影像處理軟件ENVI對不同時期的遙感影像進行預處理,采用多波段運算和決策樹分類方法對選取的影像進行處理,進而得到襄陽市不同時期的河湖水系圖。多波段是利用水體在各個波段具有不同的光譜信息,進而進行組合運算來增強水體的影像信息。具體操作步驟如下。
(1)遙感影像幾何校正。以襄陽市地形圖為基準,選取控制點,分別對不同時期的遙感影像進行幾何校正。
(2)研究區遙感影像提取。襄陽市跨越3個遙感影像條帶,先將3個條帶合并,以襄陽市的矢量圖作為邊界,把矢量圖變成ROI的感興區域,利用感興區域對衛星圖像進行裁剪,得到研究區的遙感影像數據。
(3)利用波段計算和決策樹分類得到初步的襄陽市水系圖。利用改進的水體歸一化差異水體指數來進行多波段的運算,改進的歸一化差異水體指數的公式為[8]:
MNDWI=(Green-MIR)/(Green+MIR)
(1)
式中:Green為綠光波段;MIR是中紅外波段,在Landsat TM影像中,分別為2和5波段。
根據提取出來的影像圖進行決策樹分類,即對MNDWI的數值進行分類,把MNDWI>0分為一類,把MNDWI<0分為一類,進而提取出初步的襄陽市河湖水系圖。
(4)對提取的襄陽市河湖水系圖進行后期的處理。把經過ENVI提取出來的水系圖輸出到ArcGIS中進行積水、池塘等刪除處理,并將結果疊加到Google earth上進行檢查和核查,得到襄陽市1987、1996、2006及2015年4個時期的河流水系矢量圖。
1.3.3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指標體系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可以通過水系的物理屬性來體現,包括描述性指標和復雜的綜合性指標。描述性指標主要有河流長度、河流數量、河流分支、河流等級和水面積等,很少直接使用;綜合性指標主要有河網密度、河頻率、水面率、河網發育系數、干流面積長度比、分枝比等,近年來被廣泛采用[9]。河網密度反映河流長度發育程度,其值越大,流域切割強度越大,對降水的水文響應越快,與研究區的巖性、植被覆蓋、氣候等有關。水面率是單位面積上河流的面積,其值越大對蓄滯洪水、削減洪峰越有利。主干河流面積長度比體現河流面積與長度發育的不同步性,面積長度比小,河道較窄,過水能力弱。河網發育系數表示各級支流的發育程度,河網發育系數越小,主干化越明顯。河網密度以及水面率反映河流的長度和面積變化情況,為數量特征指標;主干河流面積長度比和河網發育系數表征河網組成部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可為結構特征指標。
河湖水系連通研究近年來受到廣泛關注,水系網絡連通性源于景觀生態學中的景觀生態網絡連接度的概念,可借助于圖論的計算原理對水系的連通性進行計算,采用的指標有節點連接率和水系連通度。節點連接率表征一個節點與其他節點聯系的難易,水系連通度反映河道之間的實際結合水平。
為了從不同角度全面體現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特征,又能反映出與其他類型河網的差異,而且各指標相應數據容易量化,方便獲取,本文將從數量特征、結構特征和連通特征3個方面,構建表征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的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計算方法[10]見表1。

表1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評價指標體系Tab.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he evolution of spatial pattern of river and lake networks
2 結果分析
2.1 不同時期河湖水系空間分布
按照上述處理方法,綜合運用遙感影像及水利志等數據源,分別獲得襄陽市1950、1960、1970、1980、1987、1996、2006及2015年8個代表時期的水系圖,受篇幅長度的影響,僅列出部分時期的圖,見圖2。
襄陽市河流縱橫,河網發達,總屬長江水系,再分各屬漢江、沮漳河水系,最終入匯長江,絕大部分屬漢江流域,西南部屬沮漳河流域。漢江流域主要支流有唐白河、小清河、南河、北河、蠻河等,沮漳河流域主要支流有沮河和漳河。1960年相對于1950年,襄陽市水系的流向基本不變。漢江襄陽市河段河道屬游蕩性分汊型河道,區間匯入河溪較多,河谷開闊,河道寬淺,洲灘密布,河水分汊,水流散亂。1950-1960年間修建了官溝、石河畈、沙河、馬鞍山、姚棚、團湖及鯉魚橋水庫,水系的變化主要在滾河及北河水系,其他水系變化較小。到1970年隨著灌溉面積的增加,襄陽市水系變化較大,進一步修建了西排子河、華陽河、熊河、三道河、云臺山、張河、潭口等大中型水庫,主要在唐白河、滾河及清河流域。到1980年,鄂北崗地地區河流的水系特征變化比較明顯,河流的流程、流向由于引丹灌區的修建,有所變化,支流數量增加。引丹工程灌區西北毗鄰丹江口水庫,北接河南南陽盆地,東以唐白河為界,南臨漢江,覆蓋老河口、棗陽、襄陽、樊城等4個市(區)及襄北農場,總面積2 980 km2。該工程由渠首共引渠,清泉溝隧洞,引丹總干渠及排子河渡槽、馬張河渡槽,6條干渠,清泉溝泵站等組成。1980-1987年期間,襄陽市水利建設發展相對較慢,修建了清潭水庫、黃沖水庫和南河水庫,水系變化較小。到1996年,主要為河堤加固,漢江干流堤防防洪能力有了較大程度提升。1996-2006年間,漢江及其他主要河流修建梯級開發及水電工程,小型水庫下游小的天然河流部分變為農田。2006-2015年間,水系空間格局基本不變。

圖2 1950、1980、1987、2015年襄陽市河湖水系圖Fig.3 The river system of Xiangyang City in 1950、1980、1987 and 2015
2.2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分析
為了進一步分析襄陽市水系格局所發生的變化,把以上得到的全市8個時期的河流水網圖導入到ArcGIS中,進行水域面積和河流長度等的計算,并統計不同時期的節點數和河流個數,從而計算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評價指標,得到的結果見表2。

表2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的各指標計算結果Tab.2 Results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for the representative periods
數量特征演變:由表2可以看出,襄陽市的河網密度呈增加的趨勢,到1980年后基本保持不變;水面率特征指標呈先增加后衰減的趨勢,1996年水面率達到最大為0.06,相比1950年增加了100%。隨著研究區河道整治、水庫建設、特別是灌區大規模發展,襄陽市基本形成以丹江口水庫和漢江干支流為主要水源、蓄引提相結合的水資源配置體系,導致河網密度及水面率的增加。2000年之后,水資源需求量大,而水庫的庫容系數均較大,達到1.2~1.4,降雨均被攔截,水利工程攔截蓄水后造成水庫下游河流水量減少,部分小河道已被用來耕種,水面率減小。
結構特征演變:主干河流在水系結構和功能上均具有重要作用,襄陽市主干河流面積長度比在1950年最小,在1996年最大,干流面積長度比增大表明干流平均寬度在增大,即河網主干化程度增加,過水能力增加。就河網發育系數而言,呈增加的趨勢,主要是由于人類活動的影響,增加了支渠,支流長度增加。
連通特征演變:從指標節點連接率及水系連通度可以看出,兩指標均呈減小的趨勢,說明該地區水系結構連通性變差。1980年以來,境內漢江干流建成老河口王甫洲水利樞紐、崔家營航電樞紐工程,南河干流建成馬橋一級等9座梯級電站,唐河改建大崗坡泵站取水口工程等,區間補給水量進一步減少,境內河段河勢仍處在不斷變化之中。
2.3 空間格局演變影響因素分析
襄陽市河湖水系變遷主要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自然因素主要有地形地貌變遷、洪水、河床淤積、氣候變化等,在這些自然營力的作用下,襄陽市河湖水系始終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漢江及唐白河等兩邊多為沙礫石、黏土構造,黏土層在上,結構較緊密;沙礫層在下,結構較松散,常被河水波浪沖刷,容易形成崩岸。河道年內流量、洪水漲落及河水水位變幅較大。
人為驅動因素是近年來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的主要因素。隨著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人類涉水活動日益劇烈,水資源供需緊張、人水關系失衡。襄陽市通過修建水庫、閘堤、渠系、運河等水利工程實現對水資源時空分布的重新分配,這些水利工程,將本不連通的河湖水系連通,或者將原本連通的河湖水系連通阻斷,最終形成了新的河湖水系空間格局。人工調蓄作用改變河道原有的徑流過程和蓄泄洪區狀況。
近年來,襄陽市城鎮化率每年提高一個百分點左右,截止到2014年,襄陽市的城鎮化率達到56%。城市化改變了下墊面的條件,極大的影響中小洪水的產匯流關系,使得進入河流的水量變少。同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土地利用類型發生劇烈的變化,道路修建、住宅區開發、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活動大量占用、填埋流域內中小河道,在流域水面積減少的同時,不透水面積也不斷增加,從而影響了區域的水文循環。
實際上,經濟社會發展是人類涉水活動的直接驅動力,也是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研究區不同時期河湖水系演變的主要事件見表3。1980年以前,在國家發展的需要下,襄陽市修建了大量的水庫、電站,使襄陽市的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1980-1987年間由于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水利建設相對停滯[11],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相對較小;1988-1996年間,由于前期的水庫攔蓄及氣象干旱,出現了部分河道小型水庫下游的河渠變成了農田,自然河流長度減小;1997-2006年間,漢江干流建成老河口王甫洲水利樞紐、崔家營航電樞紐工程,南河干流建成馬橋一級等9座梯級電站,唐河改建大崗坡泵站取水口工程等,區間補給水量進一步減少,境內河段河勢仍處在不斷變化之中。2006-2015年間,城市化擴張使流域水面積有所減少,同時因提倡生態水利,濱岸修復保護及濕地公園建設加強,水面面積有所增加。

表3 不同時期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特征表Tab.3 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 and lake networks in different periods
3 結 語
本文基于遙感影像圖、水利工程建設數據及GIS空間分析平臺,得到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襄陽市不同時期的河湖水系圖,襄陽市河流縱橫,河網發達,呈五縱五橫分布,并從數量特征、結構特征和連通特征3個方面構建了表征 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的評價指標體系,對新中國成立以來襄陽市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特征及影響河湖水系空間格局的關鍵因素進行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
(1)構建了包含數量特征、結構特征及連通特征3個方面的河湖水系空間格局演變評估指標。襄陽市的河網密度呈增加的趨勢,水面率特征指標呈先增加后衰減的趨勢,1996年水面率、主干河流面積長度達到最大;河網發育系數呈增加的趨勢;節點連接率及水系連通度均呈減小的趨勢。
(2)不同時期經濟社會發展需求是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的根本驅動因素。20世紀70年代以前,在國家發展工農業生產的需要下,修建了大規模的水利工程;80年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水利建設相對停滯;90年代大江大河整治,水面率達到最大;21世紀以來,發展清潔小流域,提倡人水和諧,河湖水系空間格局變化較小。
□
[1] 李原園,酈建強,李宗禮,等.河湖水系連通研究的若干問題與挑戰[J]. 資源科學,2011,33(3):386-391.
[2] 陳德超,李香萍,楊吉山,等.上海城市化進程中的河網水系演化[J].城市問題,2002,(5):31-35.
[3] Sear D A,Newson M 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river channels: a neglected element, towards geomorphological typologies, standards and monitoring[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2003,310 (1):17-23.
[4] Vanacker V,Molina A,Govers G,et al. River channel response to short-term human-induced change in landscape connectivity in Andean ecosystems[J]. Geomorphology,2005,72(1):340-353.
[5] Gregory K J. The human role in changing river channels[J]. Geomorphology,2006,79(3):172-191.
[6] 陳睿智,桑燕芳,王中根,等.基于河湖水系連通的水資源配置框架[J].南水北調與水利科技,2013,11(4):1-4.
[7] 左其亭,馬軍霞,陶 潔,等.現代水資源管理新思想及和諧論理念[J].資源科學,2011,33(12):2 214-2 220.
[8] 徐涵秋.利用改進的歸一化差異水體指數(MNDWI)提取水體信息[J].遙感學報,2005,9(5):589-595.
[9] DENG X J,XU YP,HAN LF,er al.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river systems in the plain river network region of the Taihu Basin, China[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2016,392:178-186.
[10] 徐 慧,楊姝君.太湖平原也圩區河網演變模式探析[J].水科學進展,2013,24(3):366-371.
[11] 左其亭.中國水利發展階段及未來“水利4.0”戰略構想[J].水電能源科學,2015,3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