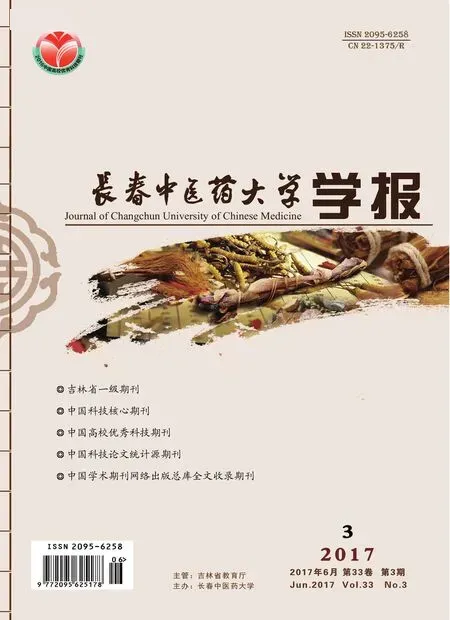氣至與針感
張立志,許能貴,易 瑋
( 廣州中醫藥大學針灸康復臨床醫學院,廣州 510405)
氣至與針感
張立志,許能貴*,易 瑋
( 廣州中醫藥大學針灸康復臨床醫學院,廣州 510405)
針灸氣至與針感概念有異,“氣至”應是指針刺前后的脈象變化,通過檢查迎寸口脈的變化來辨別病變是在經筋還是經脈以及確定補瀉后“氣至”與否。《靈樞·終始》中提出人迎、寸口脈針法,選擇五輸穴中2個陽經穴和1個陰經穴位進行針刺補瀉的操作,使人迎脈與寸口脈的大小趨于相等,可以取得“風之吹云”般的療效。
針灸療法;氣至; 得氣;針感
《標幽賦》“氣之至也,如魚吞鉤餌之沉浮;氣未至也,如閑處幽堂之深邃。氣速至而速效, 氣遲至而不治。” 楊氏在《針灸大成》里注解為:氣既至,則針有澀緊,似魚吞鉤,或沉或浮而動;其氣不來,針自輕滑,如閑居靜室之中,寂然無所聞也。言下針若得氣來速,則病易痊,而效亦速也。氣若來遲,則病難愈,而有不治之憂。故賦云:“氣速效速,氣遲效遲,候之不至,必死無疑矣”。后世很多醫家認為“氣至”就是扎針、行針過程中酸麻脹熱等針感傳導至有癥狀的部位,只要“氣至病所”就會取得療效。而筆者認為針灸氣至與針感概念不同,“氣至”應是指針刺前后的脈象變化,通過檢查人迎與寸口脈的變化來辨別病變是在經筋還是經脈以及確定補瀉后“氣至”與否。
1 氣至與針感概念
縱觀當代《針灸學》教材,大多數將“得氣”與“氣至”二詞并稱為一個概念,而文獻研究則將二者解釋得紛繁,尚不能完全理解二者之區別[1],重溫《靈樞》,發現針感與氣至的內涵應有所不同。《靈樞·終始第九》對“氣至”含義解釋得非常清楚。“氣至而有效者,瀉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瀉則虛,痛雖不隨針,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后可得傳于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明確指出是根據脈象的變化來判斷針灸是否氣至而不是患者的酸麻脹熱等針感。《靈樞·九針十二原》曰 : “凡將用針,必先診脈,視氣之劇易,乃可以治也”。因此診斷針刺前后的脈象變化對判斷氣至與否有至關重要的作用[2]。
在2012年出版的高等醫學院校教材《刺法灸法學》中定義或解釋“氣至”為:“今人又稱“ 針感”,是指毫針刺入腧穴一定深度后, 施以一定的手法,使針刺部位獲得一定的經氣感應。包括患者對針刺的感覺與反應以及醫者的手下感[3]。“針刺者可在得氣時感到針下沉緊等感覺, 而被刺者則能體會到酸、麻、脹等各種不同的感受”。但在臨床針灸治病的過程中,一些針刺可能并不使患者產生無酸麻脹痛重感, 但受刺者同樣產生舒適感,這其實已經屬于得氣狀態,如:腹針、腕腹針、浮針、腕踝針等不強調針下的酸、脹、麻的感覺,也能取得良好臨床療效[4]。而且,臨床上即使針后病人自覺某些癥狀改變或感覺舒適,若脈象未變,經脈依然未調。反之,針后即使疼痛癥狀未減,只要脈象已經出現“補則實、瀉則虛”,則“病必衰去”。說明得氣不完全是指針感,針感的概念與氣至和得氣均有交疊之處,而氣至的概念應包含得氣[5]。由此也說明針刺療效的評判——“氣至”與否,應從患者脈象入手,而非“得氣”時施術者或者患者所獲得的針感[6]。
2 “氣至”標準
古人在《靈樞》中將《經脈》《經筋》分述,目的就是告訴臨證時當辨別經脈病與經筋病[7]。《靈樞·衛氣失常》:“筋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指出經筋的病變無虛實的變化,也沒有陰陽脈的變化,臨床病變針刺僅隨病邪所在處而施治。故臨床必須辨明是經筋病還是經脈病,或是筋脈同病;然后再辨寒熱虛實,根據不同的證型施以不同針法,才能做到對癥施法,法到病除[8]。《靈樞·經筋》曰:“治在燔針劫刺,以知為數,以痛為輸”,即治療經筋病癥,“以痛為輸”,采用“燔針劫刺”之經筋刺法,能“以知為數”般地快速感知療效。也就是經筋病以按到的痛點為腧穴,燔針和劫刺都是以病人的感知為度[9]。針刺十二經筋時臨床多以隱性感傳或者疼痛方式發揮作用[10],而經脈病變時則有脈象的變化。《靈樞·經脈第十》:“胃足陽明之脈,……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所以首先辨別病變是在經筋還是經脈,主要依據人迎寸口脈有無變化以及三部九候脈。只有確定了病變在經脈還是經筋,才能正確的使針刺迅速的氣至。以疼痛為主癥的經筋病臨床治療效果判斷多以病人主訴為依據,而針刺治療臟腑經脈病變,針后取效首先反映在脈象上,所以針刺補瀉后,脈象得到改善,是獲得穩固療效的標志,而非以患者的主觀感受為依據。
3 氣速至而速效
《靈樞·九針十二原》:“刺之而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而氣至,乃去之,勿復針。至而有效,效之信,若風之吹云,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即“氣速至而速效,氣遲至而不治”[11]。《靈樞·終始》篇首先提出脈診的重要性,在開篇中首先提出在針灸臨床中認識臟腑、經脈陰陽的重要性[12]。指出:“終始者, 經脈為紀, 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余不足, 平與不平。”認為通過診察寸口脈、人迎脈象, 即可了解經脈陰陽之氣的盛衰變化,從而為針刺補瀉提供依據。因此,脈象的變化是判斷氣至與否以及 “氣速至而速效”的客觀評價指標[13]。說明針灸不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經驗醫學,而是通過檢查病人人迎與寸口脈或三部九候脈的變化來確定補瀉后“氣至”與否,而不是依據病人的感覺。《靈樞·終始》篇:“邪氣來也緊而疾,谷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 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 以養其脈, 獨出其邪氣。”即經過針刺治療,原本“盛 ”“虛”以及上下脈象不相應等異常脈象皆趨于正常,即虛弱之脈者,針刺須使其充實;堅實之脈者,針刺須使其平緩,即所謂“氣至而有效 ”[14]。
如何達到“氣速至而速效”的臨床效果,筆者認為,利用人迎寸口脈法不僅可以判斷人體陰陽的盛衰,還可以快速知曉病變所在的經脈,繼而有針對性地針灸,臨床價值極高,根據人迎、寸口脈的盛衰對比,便可確定逆亂、壅滯發生在哪一道經脈環路的陰經或是陽經,確定具體的經脈,并加以施治[15]。
《靈樞·終始》曰:“人迎一盛,瀉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二瀉一補脈口三盛,瀉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瀉”。即人迎一盛,足少陽實證,瀉足少陽補足厥陰;人迎二盛,足太陽實證,瀉足太陽補足少陰;人迎三盛,足陽明實證,瀉足陽明補足太陰。 寸口一盛,足厥陰實證,瀉足厥陰補足少陽;寸口二盛,足少陰實證,瀉足少陰補足太陽;寸口三盛,足太陰實證,瀉足太陰補足陽明。概括而言,經文里先根據人迎脈與寸口脈的盛衰,判斷疾病所在的三陰三陽系統,再根據脈的“躁”與“不躁”區分出手足,最后通過兩刺陽經一刺陰經也就是取3個穴位,2個陽經穴、1個陰經穴位進行針刺補瀉的操作。《靈樞·禁服第四十八》:“通其滎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瀉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故主要選擇五輸穴針刺,行先補后瀉,當人迎或寸口一盛(少陽或厥陰)時,每日一次;人迎或寸口二盛(太陽或少陰)時,二日一次;人迎或寸口三盛(陽明或太陰)時,一日二次。使得人迎脈寸口脈的大小趨于相等。針刺使得人迎脈寸口脈的大小趨于相等,即可治療人體之疾[16]。
4 氣遲至而不治
《靈樞·九針十二原》指出:“刺之要, 氣至而有效。”強調氣至是針灸取效的關鍵。得氣與否不但直接影響到針刺的療效,得氣的快慢也可以反映出起效時間的長短和疾病的預后[17]。一般而言,針刺氣至迅速,多為正氣充沛、經氣旺盛的表現。正氣足,機體反應敏捷,脈象的變化快,疾病易愈。若針后經氣遲遲不能使脈象平和(人迎寸口脈、三部九候脈、寸口脈),多是正氣虛損的表現。說明患者機體功能狀態的差異是影響氣至的重要因素,不同體質的患者, 機體本身的正氣的狀態不同。故筆者認為應從脈象的變化來理解“氣遲至而不治”的內涵。
《靈樞·終始第九》提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瀉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巳者因而瀉之,則五臟氣壞矣”;提示陰陽俱不足時,人迎、寸口均摸不到時,不能針刺。同時《靈樞·禁服第四十八》:“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死不治”“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提出人迎或寸口超出三倍(盛)以上,以及人迎和寸均超出三倍(盛)以上的情況下,不能針刺。
5 結語
筆者認為,針灸不是一個非常主觀的經驗醫學,應從脈象的變化來理解“氣速至而速效,氣遲至而不治”的內涵。通過檢查病人人迎與寸口脈或三部九候脈的變化來確定補瀉后“氣至”與否。主要通過收集患者臨床癥狀→參考各經脈病變“是動病”“是主”部分→確定病變經脈→檢查人迎與寸口脈的大小→確定病變經脈的虛實。最后根據《靈樞·終始》提出的人迎寸口脈針法,選擇五輸穴針刺使得人迎脈寸口脈的大小趨于相等,通過調節陰陽(相表里)兩經之間這個小循環的平衡,以小循環的平衡帶動大循環(十二經脈及十四經脈)的平衡,從而取得“風之吹云”般的療效。
[1]劉農虞. 得氣“與”氣至[J]. 中國針灸, 2014, 34(8): 828-830.
[2]武峻艷,王杰,張俊龍.《黃帝內經》中的”得氣”與”氣至[J]. 中醫雜志, 2015, 56(7): 544-546.
[3]王富春. 刺法灸法學[M].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 2005: 195.
[4]黃濤, 孔健, 黃鑫, 等. 有關得氣的誤解:從歷史回顧到實驗研究[J]. 中國針灸, 2014, 34(4): 414-416.
[5]林馳,馬良宵,苑鴻雯,等.“得氣”“氣至”“針感”概念之我見[J]. 中華中醫藥雜志, 2014, 29(9): 2892-2894.
[6]黃偉新, 黃彬, 許春燕, 等. 淺析得氣與氣至[J]. 新中醫, 2016, 48(5): 11-13.
[7]劉農虞. 談“以知為數”[J]. 針灸臨床雜志, 2013, 29(6): 67-70.
[8]肖紅, 郭長青. 十二經筋與十二經脈關系探討[J]. 中華中醫藥雜志, 2013,28(10): 2860-2862.
[9]田文. 《靈樞》經筋病的治法:燔針劫刺再解[J]. 中國針灸, 2012, 32(11): 1028.
[10]張愛軍,盛燮蓀. 影響氣至病所的因素初探[J]. 浙江中醫雜志, 2012, 47(12): 899-900.
[11]黑龍江祖國醫藥研究所. 針灸大成校釋[M].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84: 182.
[12]章海鳳, 劉未艾, 劉金芝, 等. 《黃帝內經·靈樞終始第九》針灸學術思想探源[J]. 中醫藥學報, 2014, 42(1): 125-127.
[13]存志. 試析《靈樞》對氣至的認識[J]. 遼寧中醫雜志, 2003, 30(3): 172-174.
[14]邢玉瑞. 《黃帝內經》“氣至而有效”詮釋[J]. 陜西中醫學院學報, 2008, 31(3): 1-3.
[15]孫晨耀, 胡佳奇, 楊夢珍, 等. 從“經氣雙向循行”角度闡釋人迎寸口脈法[J]. 環球中醫藥, 2016, 9(9): 1069.
[16]王棟, 常虹, 劉兵, 等. 《黃帝內經》人迎寸口脈法的解讀與思考[J]. 中華中醫藥雜志, 2014, 29(3061): 3059-3061.
[17]楊恩達, 王穎. 論針刺、得氣與療效關系[J]. 遼寧中醫藥大學學報, 2016, 18(2): 130-132.
Arrival qi and needling sensation
ZHANG Lizhi , XU Nenggui*, YI Wei
(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of Acupuncture and Rehabilitation,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405, China )
Arrival qi and needling sensation have different concepts in acupuncture fi eld, “arrival qi” should refer to the pulse changes before and after acupuncture,By exam ining the changes in the Cunkou pulse to identify lesions in the divergent meridians or meridians and determ ine whether or not “arrival qi” after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According to the proposed Lingshu Shizhong renying Cunkou pulse acupuncture, fi ve transport points in two yang meridians and a yin meridian acupuncture reinforcing and reducing the operation, the Renying Cunkou pulse size tends to be equal, thus making the w ind blow ing cloud like effect.
acupuncture therapy; arrival qi; getting qi; needling sensation
R245.3
A
2095-6258(2017)03-0396-03
2016-10-09)
10.13463/j.cnki.cczyy.2017.03.017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81230088)。
張立志(1991-),男,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針灸推拿專業方向研究。
*通信作者:許能貴,男,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電子信箱-ngxu8018@gzhtcm.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