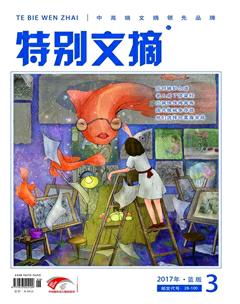青山不老
梁衡
窗外是參天的楊柳。院子在溝里,山上全是樹,所以我們盤腿坐在土炕上談話就如坐在船上,四圍全是綠色的波浪,風一吹,樹梢卷過濤聲,葉間閃著粼粼的波。
但是我知道這條山溝以外的大環境,這是中國的晉西北,是西伯利亞大風常來肆虐的地方,是干旱、霜凍、沙暴等一切與生命作對的怪物盤踞之地。可是就在如此險惡的地方,我對面的這個手端一桿旱煙的瘦小老頭,他竟創造了這塊綠洲。
我還知道這個院子里的小環境。一排三間房,就剩下老者一人,還有他的棺材。那棺材就停在與他一墻之隔的東屋里。老人每天早晨起來抓把柴煮飯,帶上干糧扛上鍬進溝上山,晚上回來,吃過飯,抽袋煙睡覺。他是在65歲時組織了七位老漢開始治理這條溝的,現在已有五人離世,卻已綠滿溝坡。他現在已81歲,他知道終有一天早晨他會爬不起來,所以那邊準備了棺材。他可敬的老伴,與他風雨同舟一生,也是在一天他栽樹回來時,靜靜地躺在炕上過世了。他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在城里工作,三番五次地回來接他出去享清福,他不走。他覺得自己生命的價值就是種樹,那邊的棺材就是這價值結束時的歸宿。他敲著旱煙鍋不緊不慢地說著,村干部在旁邊恭敬地補充著……十五年啊,綠化了八條溝,造了七條防風林帶,三千七百畝林網。這是一個多么了不起的奇跡!但他還不滿意,還有宏偉設想,還要栽樹,直到他爬不動為止。
我們就在這樣的環境中談話,像是站在生死邊界上的談天,但又是這樣隨便。主人像數家里的鍋碗那樣數著東溝西坡的樹,又拍拍那堵墻開個玩笑,吸口煙……
在屋里說完話,老人陪我們到溝里去看樹。楊樹、柳樹,如臂如股,勁挺在山洼山腰。看不見它們的根,山洪涌下的泥埋住了樹的下半截,樹卻勇敢地頂住了它的兇猛。這山已失去了原來的坡形,而依著一層層的樹形成一層層的梯,老人說:“這樹根下的淤泥也有兩米厚,都是好土啊。”是的,保住了這些黃土,我們才有這綠樹;有了這綠樹,我們才守住了這片土。
看完樹,我們在村口道別,老人拄著拐,慢慢邁進他那個綠風蕩蕩的小院。我不知怎么一下又想到那具棺材,不覺鼻子一酸,也許老人進去就再也出不來了。作為政治家的周恩來在病床上還批閱文件;作為科學家的華羅庚在講臺上與世人告別;作為一個山野老農,他就這樣來實現自己的價值。一個人如果將自己的生命注入一種事業,那么生與死便不再有什么界線。他活著已經將自己的生命轉化為另一樣東西;他死了,這東西還永恒地存在。他是真正與山川共存,日月同輝了。老人是這樣的坦然,因為他的生命已轉化為一座青山。
老人姓高,名富。這個普通的人讓我領悟了一個偉大的哲理:青山是不會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