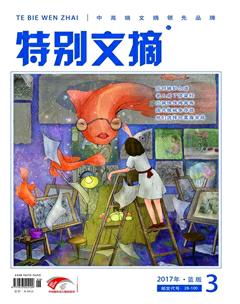外交辭令不簡單
補壹刀
大多數人可能會覺得,外交部發言人的話語“套路滿滿”。“關注”“關切”“遺憾”“不滿”“反對”“抗議”——這些詞匯真的像你所想的那樣千篇一律沒有什么實際內容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外交辭令有輕有重
比如去年12月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說:“我們敦促美國新一屆政府和領導人充分認識臺灣問題的高度敏感性。”
“敦促”是典型的外交辭令。和“抗議”“反對”比起來,想必你也能體會到“敦促”相對溫和,而外交辭令都是倍經考究的,僅用了“敦促”是因為當時特朗普還沒真正上臺,只是在推特上和接受采訪時說說,算不上外交政策和行為。
外交辭令在本質上反映的是一國的外交立場,其中每個詞都輕重可酌,它能反映不同程度的態度和政策。
比如我外交部對在韓部署“薩德”等問題,常表示“堅決反對”,而在韓國決定接受部署前外交部用的是“嚴重關切”。
機智的你一定已經體會出“堅決反對”比“嚴重關切”要重很多。這種變化的根源在于問題的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確定要部署“薩德”再結合事件已經涉及中國的戰略利益,比如安全問題、統一問題,表態肯定要更強烈一些。
事實上,外交交涉中最常見的表述,依事件的嚴重程度,主要有“關注”“關切”“遺憾”“不滿”“反對”以及“抗議”。其中,“抗議”是最嚴重的等級。而如果“抗議”都還不能完全表達中國的立場,那么還可以在其前面加上“強烈”。
現在,中國的外交辭令越來越精細,這實際上反映出中國外交的豐富內涵。在使用它們時我們也更加謹慎了,以便給處理復雜尖銳的國際問題預留空間。
外交辭令并非一成不變
外交辭令是一成不變的嗎?顯然不是。即使是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含義。其實一個詞就可以看出中國外交的變遷。
“悍然”,《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蠻橫的樣子”,在中國當下一向謹慎斟酌的外交詞匯中,一般很少使用。
“悍然”最早出現于1965年3月12日,當時中國政府發表聲明,強烈譴責“美國政府悍然派遣海軍陸戰隊進入南越”。
此后的兩年里,我們也經常用這個詞。比如,印尼政府“悍然”宣布“暫時封閉”新華社駐雅加達分社,日本佐藤政府“悍然”宣布拒絕中國人民外交學會代表團入境,以及越戰期間美國戰斗機“悍然”侵入中國領空并投彈進行“猖狂的戰爭挑釁”。
而2006年中國把這個詞用在了朝鮮的身上。當年10月9日,朝鮮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我外交部發表聲明,其中寫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無視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實施核試驗,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這份被媒體稱為“空前強硬”的聲明在中朝交往史上算是史無前例了。當時的國際政要也都關注到了這一點,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說這份聲明“使用了前所未有的嚴厲詞匯”。
對朝鮮使用這個詞匯,說明了新中國外交的大轉變——我們真正做到了以是非曲直而不是友誼關系,來決定我們的立場。
影響外交辭令的因素
對于中國而言,影響外交辭令的還有哪些因素呢?
一是事情本身的性質,二是當事國與我國的關系,三是我們的外交內核,四是國力變遷和地位變化。
現在,中國的國力更強大,大到既可以影響別人,也會可能影響到自己。以前我們時常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但現在影響大了,自然會限制自己的行動。原來有些能說的,現在中國會更加謹慎。
而除了外交交涉的詞匯,國家間的稱謂也反映出國家間關系的變化。
比如中國原來稱蘇聯為“老大哥”,是同在社會主義陣營的絕對親密關系。但中蘇關系一遇阻,外交用語就猛地轉向,比如“敵人”“修正主義”都被冠之于曾經的“老大哥”身上。
美國也是一樣,原來我們是要“打倒美帝國主義”,美國是“我們最大的敵人”。中美關系正常化后,兩國也漸漸成了“朋友”。
蘇聯和美國無疑是兩個比較極端的例子,而中國和周邊國家如東盟國家,通常都是“三好關系”,即“好鄰居、好朋友、好伙伴”。在“三好”的基礎上,我們和越南多了一層“好同志”關系,顯示我們和越南都是社會主義國家。
而我們常說的“巴鐵”,更是和中國多了一層“好兄弟”關系。這關系杠杠的。
外交辭令的力量取決于國力
中國的外交辭令從開始發展到如今,既有一以貫之的東西,又有發展變化的成分。一以貫之的是我們堅持獨立自主,從不看別人臉色。另一方面,我們現在也同樣強調相互依存了,這意味著中國的外交辭令的變化更加豐富,也更復雜了。
比如,去年12月中方捕獲美方無人潛航器,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卻說,日方希望迅速解決該事件,并認為中方有必要就該事件向國際社會做出解釋。
對此,華春瑩回應:“日方太操心了,這件事與日方有關系嗎?”
總而言之,沒有國家的綜合實力做支撐,即使外交辭令再強硬,可能都無人理睬,甚至會引來不屑的目光。而中國無論說點啥,都不可能石沉大海。其中的原因,你懂的。
(摘自《華聲》 圖/黃煜博)本欄編輯:李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