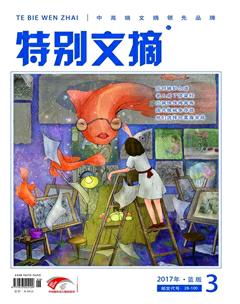他們選擇向霧霾宣戰
青山、綠水、一望無際的草坪,還有大片的森林,這是德國隨處可見的畫面,似乎德國從未有過霧霾一樣。
其實不然,德國也有過嚴重的霧霾。以魯爾區為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而魯爾區就是德國機械制造及重化工業中心,煤炭、鋼鐵、化學、機械制造等行業高速發展,讓該區霧霾不斷肆虐,成了空氣污染的重災區。除了魯爾區之外,當時西德的多數地區也未能幸免。著名的萊茵河曾經一度是條魚類無法生存的“死河”,慕尼黑、斯圖加特、法蘭克福、科隆等城市上空也一直籠罩著迷霧。
面對如此嚴重的環境問題,德國人不是去購買抗霧霾口罩,也沒有往家里搬空氣凈化器,更沒有安裝防霧霾紗窗。當然,也沒有去找一個“國際科研團隊”來論證德國霧霾是中性的,與倫敦奪命大霧成分不同。
令人吃驚的是,霧霾很快從這個國家神奇地消失了。自1991年之后,德國再也沒有響起霧霾警報。到了2007年,曾經一度困擾德國的二氧化硫濃度下降到每立方米8微克。空氣中懸浮顆粒物濃度明顯下降,2012年魯爾工業區所有空氣質量監測站監測到的PM2.5含量最高只有每立方米21微克。那么,德國人為此到底做了什么?
他們選擇了主動向霧霾宣戰,而不是被動地自我保護。1971年,大氣污染治理首次納入聯邦政府的環保計劃。1974年,德國第一部《聯邦污染防治法》頒布,對二氧化硫、硫化氫和二氧化氮開始執行嚴格的排放標準。該法經過多次修改和補充,已成為德國最重要的法律之一。
在治理霧霾的過程中,德國政府積極促進能源結構轉型。國家對新型能源提供補貼,給風能和太陽能發電提供更好的入網條件,提高新能源的利用率。
作為汽車大國,德國對汽車尾氣設立嚴格的排放標準,大幅降低汽車尾氣中的氮氧化物和顆粒物濃度。另外,盡管德國高速公路不限速,但城區一般都規定車輛速度不得超過每小時50甚至30公里。
德國法律法規的實施從不打折扣,在環保領域更是明顯。德國垃圾分類極其嚴格,公民對家庭的垃圾進行分類是項義務,同時政府的垃圾回收站對各類垃圾也專車回收,絕對不會把民眾已經分類的垃圾又倒入同一輛垃圾車。
同時,德國的城市規劃也處處反映出環保理念。大城市幾乎看不到高樓大廈,也沒有復雜的立交橋,成片的森林在城市隨處可見。即便是德國房價最高的城市慕尼黑,其市中心竟然也修建了一個很大的森林公園,充分證明了德國人“讓森林擁抱著城市,讓城市依偎著森林”這樣一種試圖讓環境和人相互融合的城市規劃理念。
硬性的法律法規和有力的行政措施,如果沒有民眾的全力配合,效果不會如此明顯。民眾對環保的支持,來自于根深蒂固的環保意識。德國是最早提出環境教育的國家之一,從孩子到成人,都有大量的機會接觸環保課程。一位居住在慕尼黑的朋友說,他曾經和上幼兒園的女兒開了個玩笑,散步時故意把一張廢紙扔在地上,她女兒馬上在后面拾起并“教育”他:幼兒園阿姨說不能隨便丟棄垃圾。為了不讓爸爸再亂扔那張廢紙,她一直把它拿在小手中,直到發現公共垃圾桶才把它扔進去。當他女兒上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老師開始講授垃圾分類知識,并帶全班同學到垃圾處理站、堆肥廠、污水處理廠參觀,讓他們體會垃圾分類的重要性,家庭作業則是幫助家長進行家庭的日常垃圾分類。
為了保護環境,德國人愿意放棄一些享受。例如,私家車盡量選擇排量小、污染小的車輛,而不是大馬力的豪車。短途一般會騎自行車或步行,有人騎半小時甚至一小時自行車去上班。許多德國城市的街道上都有自行車專用通道,騎車的人很多,在森林小道更是自行車成隊出動。
通過長期持續的宣傳教育,環保觀念深入人心,保護環境也成了每個德國人的生活習慣,讓肆意排污的行為沒有了生存的土壤。民眾環保意識的增強,倒逼政府提高環保標準。2006年德國KGM集團計劃在帕德博恩修建一座垃圾焚燒廠,由于符合排放標準,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但民眾表示反對,于是議會轉變立場。2008年,帕德博恩議會通過了一項名為“發展項目凍結”的政策,規定在新發展規劃未出臺前,禁止建設任何大型工程項目,這實質上是對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喊停。在公眾和議會的壓力下,帕德博恩市政府不得不制定了更嚴格的排放標準,重新對該項目進行評估,從而讓焚燒項目流產。
嚴格的法律和有力的措施,再加上民眾強烈的環保意識,是霧霾從德國神奇消失的深層次原因。
(摘自“楊佩昌看德國微信公眾號” 圖/子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