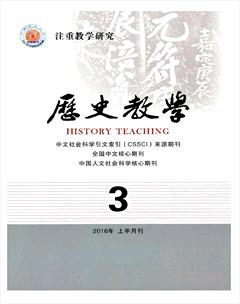論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在中國東南的起源
徐曉望
[摘要]由于中國東南水上人家疍家人的活動,早在石器時代就建立了環中國海交通網絡,漢晉之時朝廷使者對東南亞的探索,是這一交通網絡的延續。唐宋之際,東南經濟文化大發展,絲織業、制瓷業等行業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于是,聯絡東南城市及北方沿海的海上貿易興起,并向海外發展。這股力量與西亞、南亞及東南亞東向力量的結合,構建了自中國東南出發,經東南亞到南亞、西亞的海上絲綢之路主干道。
[關鍵詞]東南區域,海上絲綢之路,疍家人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6)06-0010-10
早期的“絲綢之路”是聯絡中國與西亞、歐洲國家的陸路貿易之路,唐宋之際,“海上絲綢之路”興起,逐漸成為中西貿易的主流。在國際學術界,許多人認為:中國人不太擅長航海,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主要是來自西亞的商人“發現了”中國。筆者認為:中國東南民眾自古有航海傳統,唐宋以來,隨著東南區域經濟的開發,東南民眾積極從事海外貿易,是創立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力量。聯絡中國與西方的海上絲綢之路,既是西方航海家向東航行的結果,也是東方海上力量向西進發的成就,本文主要探討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國東南起源。
一、中國東南的疍家人:
一個“以船為家”的民族
《論語·公冶長》記載了孔子的一句話:“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從人類學的角度分析孔子這句話,可知當時山東半島的沿海區域有一些水上人家,他們以筏為家,航行于海上,乃至引起了孔老夫子的興趣。孔子的時代,正是越王句踐稱霸的春秋末期。句踐打敗吳國之后,為了與中原諸國聯系,率越國水師從長江出海口航行到山東半島的瑯琊山下,建立了越國的據點,以便與中原諸國交往。越國人北上瑯琊,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的重要航海活動。這都說明,早在春秋時期,中國東方沿海的夷人和越人,都有其海上生涯。
臺灣“中研院”的陳仲玉研究員長期在福建沿海的馬祖列島從事考古發掘。近年來,他們團隊最重要的貢獻是在馬祖列島的一個小島上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兩具“亮島人”遺骸。經德國和美國的兩個實驗室對其DNA進行檢測,其結論讓人驚訝;其中一具遺骸表明,他與山東半島的古人基因類似,而另一具遺骸,則似東南沿海的古人。為什么中國東南小島上新石器時代的遺骸會與山東半島的古人基因相似?難道在那么遙遠的龍山時代,就有山東半島的居民航海到東南沿海島嶼?可以作為印證的另一現象是:發現于龍山文化中的黑陶器,同樣發現于福建的新石器遺址中!這只能說明,早在遠古時期,中國沿海各民族就在進行海上交流。他們海上活動的規模和水平,遠遠超越今人的認識。
傳統古籍記載,自古以來,東南沿海就有一支生活于水上的人家。宋代的《福州圖經》記載:“閩之先居于海島者七種,泉水郎其一也。”他們生活在福建、浙江、廣東沿海,以船為家,過著打魚為生的生活。三國時期,東吳割據東南,以水師著稱于世。但其水師中有不少人來自閩中。左思的《吳都賦》云:“篙工楫師,選自閩禺。習御長風,狎玩靈疍。責千里于寸陰,聊先期而須臾。”這說明在吳國時期,來自閩粵的水手是極為出色的。隋朝滅陳之際,隋朝大將楊素率軍進入東南,擊敗南安豪強王國慶部。“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日游艇子。智慧、國慶欲往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效。國慶乃斬智慧于泉州。”其中的“游艇子”,便是這類海上人家,他們主要生活于閩浙沿海。
宋初的《太平寰宇記》記載:“泉郎(一說白水郎),即此州之‘夷戶,亦曰‘游艇子,即盧循之余。晉末盧循寇暴,為劉裕所滅,遺種逃叛,散居山海,至今種類尚繁。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義童遣使招撫,得其首領周造麥、細陵等。并受騎都尉,令相統攝,不為寇盜。貞觀十年(636年),始輸半課。”以上記載表明,唐朝統一閩中之后四年,“游艇子”歸屬朝廷,貞觀年間更成為朝廷的納稅戶。9唐五代的疍家人在福建分布很廣。顧況的《酬漳州張九使君》一詩詠及:“薛鹿莫徭洞,網魚盧亭洲。”“地理志,莫徭,夷蜒名。自云其先祖有功,常免徭役,故以為名。薛鹿即殺鹿。集韻莛與殺同音同義,此省為薜也。盧亭者居海島,赤身無衣,常下海捕魚,能伏水中三四日不死。相傳為盧循子孫,亦名盧余。漳郡唐初所開,固當以此入詠。”這條史料說明漳州沿海有較多的疍家人。對于這些水上人家,唐中葉劉禹錫說:“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與華言不通。”其中“家浮筏者”,讓人聯想起孔子所說的“乘桴浮于海”的那一種人。可見,自春秋以來,中國沿海一直有一批生活于海上的人家,他們或是“以船為家”,或是“以筏為家”,漂沒于沿海島嶼。因中國東南沿海多島嶼,而且氣候溫暖,尤其適合水上人家,所以,自唐五代以后,中國的水上人家大都生活于東南沿海島嶼之間,而北方沿海則較為少見。
在中國東南生活的水上人家,又被稱為疍人。他們的生活富有特點。宋初的《太平寰宇記》記載:“其居止常在船上,兼結廬海畔,隨時移徙不常。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名曰‘了鳥船。”疍家人以打魚為生,宋代蔡襄的詩詠道:“潮頭欲上風先至,海面初明日近來。怪得寺南多語笑,疍船爭送早魚回。”疍家人的生活方式極為獨特,如蔡襄所說:“福唐水居船,舉家棲于一舟。寒暑食飲,疾病婚姻,未始去是。微哉其為生也!然觀其趣,往來就水取直以自給,朝暮飯蔬一半,不知鼎飪烹調之昧也溫衣葛服,不知錦紈粲粲之美也;婦姑荊簪,不知涂脂粉黛之飾也;蓬雨席風,不知大宇曲房之適也。”由此可知,宋代疍家人的生活極為簡樸,他們很少吃肉,沒有華麗的衣裝。元代,朝廷曾經下詔免除“福建疍戶差稅一年”。疍家人一生在船上生活,漂泊于東南沿海各地。從他們在中國沿海的分布來看,北自舟山群島,南至廣東西部沿海,都有疍家人的船只,他們出沒于東南各地的港灣,以船為家,相互通婚,創造了獨特的疍家海洋文化。
在中國古代,疍家人一直被南方陸地民眾視為賤民,但從海洋文化這一點來看,疍家人才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海洋族群,也是世界歷史上極為罕見的海洋族群。他們不像大多數民族一生主要生活在陸地上,而是以船為家,以海為家,對這種生活方式,我們只能以偉大這一詞來形容。要知道臺灣海峽是風暴盛行的區域,每年夏季,都有十余次臺風經過臺灣海峽。臺風的風力一般都在十級以上,有的十二級強臺風,風速達每秒百米以上。臺風中心所過之處,房屋塌倒,大樹連根拔起,海面上巨浪滔天。生活在福建沿海,每當臺風季節我常會想:古代的疍家人是怎么在這種海面上生活的?他們用什么辦法抵抗滔天大浪?能在這一環境中生存的海洋民族當然是偉大的民族。其次,從其生活方式來說,他們才是真正的海洋民族。西方歷史上所謂的的海洋民族,諸如腓尼基人、希臘人,他們實際上不過是住在海岸上,偶爾參加海上航行而已。如果這樣的民族都自稱是海洋民族,那么該用什么詞來形容疍家人?實際上,在世界歷史上,我們還找不出另外一個民族,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給大海,在海洋上生活,在海洋上成長,一生的大多數時間離不開海洋。近代的所謂“海洋民族”,其實都是以陸地為生活基地,以大海為謀生的場所,他們不管在海洋生活多久,最終都是要以陸上的財富與榮譽來體現自己的價值。一個英國人可以闖蕩四大洋,但他們在心理上,還是想回歸英倫三島。只有疍家人才是真正的以海為家。在六朝時期,閩、粵、浙三省的海岸,基本沒有人居住,如果他們要登岸居住,根本沒有人阻擋。問題在于:他們在陸地上,感覺不到漂泊海上的自由,即使偶爾在岸上搭住篷寮,也只是暫時的駐足。他們的生命已經完全交給海洋。因此,疍家人的海洋文化才是真正的海洋文化,這是其他民族所無法比擬的。
二、漢疍民族結合與海洋文化的發展
中國東南原為閩越國所在地,漢武帝征服東南的閩越國之后,將其民眾遷至江淮一帶,這使東南一度成為中國人口最稀少的地方。然而,自漢末孫氏建立吳國以來,東南區域又開始了發展。西晉“永嘉之亂”后,中原民眾大舉南下,導致中國東南人口的增加。西漢時期,從浙江南部到福建遼闊的區域,僅設一個冶縣,隸屬于揚州的會稽郡。隋代的浙江設會稽、余杭等六郡,約10萬余戶,閩中設建安郡,僅轄四縣,約12420戶,廣東設南海、龍川、義安三郡,約4.6萬戶。人口密度遠遠低于內地諸省。然而,自唐代中葉“安史之亂”后,中原區域陷于長達二百年的藩鎮之亂,中原民眾不得不離開家鄉,向東南遷徙,導致東南諸地人口大增。北宋元豐年間,兩浙路人口共計183萬戶,福建路人口為99.2萬戶,廣南東路人口為56.6萬戶。和隋代相比,東南各路人口增加了十幾倍到幾十倍。漢人來到東南之后,逐漸與東南的越人后裔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以漢人為主體的浙人、閩人、粵人等地域人群。疍家人也在這一時代大量融入漢族,他們的海洋文化與漢文化融為一體,并成為漢文化的一個部分。
漢人發展的中原區域是東方各民族的大熔爐,也是各種先進技術的融匯之地。漢人從中原遷徙到東南沿海,也帶來了當時的先進技術,例如以磁石導航,這是海上航行最關鍵的技術之一。又如煉鋼及各種鋼鐵工具制造術的南傳,大大提高了東南一帶的造船術。
漢族是木構藝術的大師,自古以來,中國人的主要建筑物都是由木材建造的,而且,這些木建筑的華麗,從來不亞于西方的石建筑。當我們回想古代阿房宮、近看明清故宮之類的大型宮殿,就不能不贊嘆古人的絕代才華,展望世界各地,沒有一個民族再能展示同樣等級的木建筑才藝。這一偉大的木構藝術有什么意義呢?它不只是展示古代中國人陸上建筑的才藝,同時還是古代中國人發展海上建筑藝術的強大后盾。打一個比方,一座大型木船,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宮殿,沒有精致的木構技術,也就無法建造大型木船。而漢族恰恰是一個最擅長木建筑的民族,他們將制造宮殿的技術移用于海船,便能制造出大型的木船。這一技術的轉移,對疍家人來說,是突破了小艇時代的關鍵,是從游艇子發展到航海家的關鍵。所以,二者的結合,是唐宋時期福建海洋文化升華的關鍵。觀察唐宋時代的造船術,有幾項的變化值得注意:
其一,在制木中使用刨刀。木匠工具中的刨刀是一項了不起的發明。刨刀的功能是將木材刨平,形成細密的平面。這在木材加工史上有重要意義。因為,只有將木材拋光,才能將木材緊密地接合在一起。以造船來說,若船板之間的接合有縫,海水就會無情地滲透到船內,導致船舶下沉。在陸地上的建筑中,若是不解決這個問題,用木頭做的窗戶會透風。因此,在木匠工具發展史上,刨刀是繼斧子、鋸子出現后第三種最重要的工具,它是木材精加工的基本工具。我看過一部歐洲人的工具史,德國人使用刨刀大約是明代后期,他們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早的刨刀,其實不然。刨刀無疑是中國人最早的發明,它是繼承“錛”這一工具發展而來的。“錛”是最早的木材表面加工工具,約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當時木匠手中的“錛”全以金屬做成,它有一個平整的刀面可以刮削木材表面。它在北方漢人中十分普及。不過,早期的錛較為原始,和后世的鋤頭區別不大,所以后人會將類似鋤頭的石制農具稱為石錛。從出土文物來看,戰國時代的木材表面都有明顯的刮痕,這說明“錛”的精加工能力有限。唐宋時期,錛發展為刨刀。刨刀的奧秘在于將鋼制刀面鑲嵌于平整的木塊之中,木匠可以輕推的方式刨平木材表面,從而獲得加工對象表面平整如鏡的效果。從出土木器來看,唐五代時期的木器表面已經相當光潔,說明當時已經使用刨刀。而這項技術應用于船舶制造,成為中國帆船經久耐用的奧秘。
其二,使用油灰技術填縫。這項技術在當代木工技術中仍在使用。所謂油灰,油是桐油,灰是石灰,提煉桐油和石灰,是中世紀的工業成就。將桐油和石灰粉攪拌在一起,會形成柔軟的油灰,油灰中的水汽蒸發后會變成固體,密不透水。唐宋的匠人用油灰填充船體的細縫,海水無法滲透。在福建海邊,民眾多用海蠣殼燒灰,與桐油攪拌后成為油灰。出海的船只返航后,細心的漁民都會用油灰封死出現的小洞,每年填補一兩次,可使木船完整如新。所以,當時福建的木船可以使用十幾年至幾十年。其時,老式船舶還使用海上的茜草填縫,茜草遇水后膨脹,可將船縫堵死。然而,茜草曬干后又會收縮脫落。所以,使用茜草填縫的船只缺乏長久性。
其三,使用鐵釘鉚接船體。在這項技術發明以前,中世紀流行的船舶制造是用藤條串綁船體。藤條的力量顯然不如鐵釘。唐宋的中國木匠串聯船板有獨特的技術,他們先是竹子制成兩頭尖的竹簽,將木板連在一起。后來是用數寸至一尺多長的鐵釘,將船板釘在一起。
刨刀、鐵釘加油灰,使船舶的木板之間緊密相連,而船舶的耐用度也提高了。這是當時最先進的制船技術,同時代的海外船只,大都處在以藤條串板、以茜草填縫的時代。就連中國沿海也沒有完全普及這一技術。宋代的周去非有《嶺外代答》一書:“深廣沿海州軍,難得鐵釘桐油,造船皆空板穿藤約束而成。于藤縫中,以海上所生茜草,干而窒之,遇水則漲,舟為之不漏矣。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販皆用之。”與宋代的廣東相比,臺灣海峽的造船技術更為完善。1974年8月在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其船板就經過刨平,船板之間以鐵釘連接、以油灰填充,整體性較好。
據徐兢的《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一書,他在寧波港雇傭的福建客舟“長十余丈,深三丈,闊二丈五尺,可載二千斛,其制皆以全木巨枋挽疊而成。上平如衡,下側如刃,貴其可以破浪而行也”。可見,這是一種體形狹長、尖底的海船。泉州后渚港出土的宋代海船是一種橢圓形的船只,與廣東的方形船舶有很大不同。其水下殘長24.20米,最大殘寬9.15米,殘深為1.98米,復原后,其長度應為34米,寬度為11米,深度為4.21米,其特點是船身狹長,上寬下窄,吃水較深。這類船型不怕海浪沖擊,利于遠洋航行。從船型來看,它顯然與疍船有一定關系,《太平寰宇記》記載疍家人的“了鳥船”:“厥所船頭尾尖高,當中平闊,沖波逆浪,都無畏懼。”這正是福建海船的起源。可以說,漢族制造術融入疍家人的傳統造船術,從而使東南沿海區域的造船術有了很大的提高。
唐代以來的中國海船以雄偉聞名。唐代僧人在《一切經音義》中說到當時的船舶“大者二十丈,載六七百人”,名之為“蒼舶”。又說當時的海船:大者受萬斛也。唐代一斛的容量可載110市斤的粟,萬斛船可載貨550噸!阿拉伯人蘇萊曼在其《印度·中國游記》中說:中國唐代的海船特別大,抗風浪,能在波濤洶涌的波斯灣海上航行。其時,阿拉伯商人遠航東方,多愿意乘坐唐船。他還說,由于中國船體積龐大,吃水太深,不能直接進入幼發拉底河。可見,唐代中國的船只稱雄于印度洋上。宋代,“海舟以福建為上”,是流行的評語。《太平寰宇記》一書,將海舶列為泉州、漳州的“土產”。為了抗衡金朝的海上實力,官府曾在福建造海舟700艘,元將高興入閩時,“獲海舶七千余艘”。著名詩人薩都刺在駛往福州時詠道:“三山云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秋水。”可見,他乘坐的是一艘有十面風帆的大船。
唐宋時期的福建海船是世界一流的大帆船,這是中國人在宋元時期最終稱霸海洋世界的基礎。
唐宋時期,沿海疍民大量融入漢族。如果說唐代前期的東南沿海到處都是他們的活動地盤,那么,宋元之后,疍民主要分布于錢塘江、閩江、珠江的下游,福建東南沿海與廣東東部沿海的疍家人在文獻中漸漸“消失”了。其實,他們不是消失了,而是融入到當地漢族中去,成為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中國歷史上,承載中國海洋文化主流的正是泉州人、漳州人、潮州人、福州人。唐宋時期,閩粵人是中國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載者。
發達的造船術和傳統的海洋商路,使唐宋時期中國的海洋文化達到很高的水平。
三、東南經濟區的興起及其歷史地位
中國文化中心長期在中國的西北部,漢唐時期最繁華的城市是西安和洛陽。從漢朝到唐朝前期,中國東南都是人口稀少的區域。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向東、向南轉移。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有其氣候變化的背景。古代中原的氣候,應當類似今日的江南,在唐代中原詩人的詠物詩中,常可見到竹類植物,當時長安、洛陽一線的中原區域,應可生長這類植物,所以會獲得詩人的詠嘆。但是,唐中葉以后,一直到宋元時期,北方氣候逐漸變冷,許多植物無法在北方生長。竹類植物的北方界限,退到了陜南川北。再以柑橘而論,戰國時期,淮河一帶盛產柑橘,所以楚人有柑橘“過淮成枳”之說。北方氣候變冷之后,畏寒的柑橘退到浙南、贛北才能結果。中國文明中心的轉移,應與氣候變化有關。東北、華北的各民族所培育的各種作物在本地難以生長,他們不得不向南尋找適宜種植傳統植物的土地。在他們的驅動下,中原各民族也不斷南移,促成了東南區域的大開發。長江以南的江蘇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部、廣東中部、浙江省、江西省、福建省漸成為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這些區域的發展,其實是中原文明向東南轉移的結果。
東南區域共同的特點是水稻種植區域。唐宋時期,隨著鋼農具和“江東犁”的普及,以精耕細作為特點的南方水稻農業發展起來。南方水稻的畝產量超越北方的麥子、粟米、高粱等作物,“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這是全國最高的大田產量。糧食生產大增,是江南經濟繁榮的基礎。韓愈對福建大加贊語:“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于是,北方移民大舉南下中國東南區域,加速東南的開發浪潮。江南一帶的糧食高產區成為經濟最發達區域,“蘇湖熟,天下足”在此基礎上,金陵、蘇州、杭州、寧波等一批城市成長起來。其他各路也是一樣,以江西農業為背景的南昌,以珠江三角洲為背景的廣州,以及以福建沿海平原為背景的福州、泉州,都成為繁華程度較高的城市。
東南的繁榮,也帶動了南方各項手工業的發展。以絲織業來說,唐代的絲織業遍及北方各地,不論是河北、河南、山西、陜西,都有發達的絲織業。彼時桑樹在北方是很普及的,這是蠶桑業發展的基礎。但隨著北方氣候變冷,北方桑樹的生長遇到障礙,但在江南溫潤的魚米之鄉,桑樹被種于大田,并得到細心的照顧。這類桑樹的桑葉厚潤,營養豐富,蠶蟲吃了這類桑葉之后,吐出的絲更為堅韌,富有彈性,以之織成絲綢,遠勝傳統織品。于是,江南的湖絲名揚天下,擊垮了所有的對手。這樣,中國蠶桑業中心逐漸轉移江南的湖州一帶。
中國瓷器生產的情況更為復雜一些。早在唐代前期,來自南方的龍泉窯就贏得許多人的喜歡。龍泉是浙南的古縣,早期轄地范圍比現在的龍泉縣更大一些。著名的古龍泉窯遺址,多在現今的遂寧縣境。龍泉窯的特點是生產綠瓷,著名的秘色瓷蘊含似有似無的淡綠色,早在唐代即為珍品。秘色瓷失傳許久,今人在西安法門寺地窖找到它的真實面目。這表明龍泉窯早在唐代就很出名,一直是中國重要的制瓷中心,可與北方的五大名窯并列。除了龍泉窯之外,江西景德鎮窯在宋代漸漸出名,成為南方生產瓷器的重鎮。
南方的蔗糖生產也是傳統產業。西漢初年,“閩越王獻高帝石蜜五斛”。其中的石蜜,糖史專家認為是閩粵生產的蔗糖。唐太宗引進西方的制糖術之后,南方制糖業有較大的發展。唐宋時期,產自東南的蔗糖被運往國內市場,成為南方代表性物產。
南方制茶業的發展也值得注意。唐代制茶業興起之時,主要產區是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區域。唐末五代,北方移民南下,其中來自淮南光山縣的茶農移民到福建北部山區,在閩北的建安縣北苑一帶焙制茶葉,北苑茶從此名揚天下。南唐及北宋時期,朝廷在北苑設置御茶苑,北苑龍團茶享譽國內三百年。此外,杭州西湖一帶龍井的茶葉生產,也逐漸出名。
江西北部的饒州和信州,歷來是中國礦冶業中心和制造業中心。這里有發達的冶煉業,出產白銀、青銅、生鐵、鋼材、鉛錫等各種金屬。因礦業發達,金屬出產多,信州等地的制造術也很好。唐宋之際的陶谷說:“上饒葛溪鐵精而工細,余中表以剪刀二柄遺贈,皆交股屈環,遇物如風,經年不營。一上有鑿字曰:儀刀。”江西人王安石主張有些鐵制品可在信州采購。“若以京師雇直太重,則如信州等處鐵極好,匠極工,向見所作器極精,而問得雇直至賤,何不下信州置造也。”可知北宋信州的制造業已經相當有名。此外,饒州的瓷器生產也是非常有名的。聯系明代張瀚的《松窗夢語·百工紀》的話:“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于東南,江右為伙,浙直次之,閩粵又次之。”可知江西手工業的發達是從唐宋一直延續到明朝。
白銀在唐宋之交已經發揮出貨幣的職能。中國白銀生產中心在唐宋時期已經轉移到東南區域,主要在安徽、浙江、福建三省交界區。南宋朝廷每年從福建購買27萬兩白銀。當時中國的商人為了追逐白銀,常到東南諸省貿易,帶動了東南經濟的繁榮。
以上敘述表明:自唐宋以來,中國東南逐漸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不僅有發達的農業,也有發達的手工業和商業。發達的商品生產需要市場,而市場的發展是不分內外的。事實上,隨著東南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東南區域出產的絲綢、瓷器、蔗糖、精鐵、茶葉都大量輸出中原市場和海外。唐宋時期以中國東南區域為源頭的海上絲綢之路之興起,與東南經濟發展是相適應的。
四、東南海路運輸網絡的形成
在東南區域經濟繁榮的背景下,以水路為主的交通網絡興盛起來,其中海路也成為東南運輸網絡的組成部分。
中國人很早就重視水路運輸,在隋朝就開發了大運河,使之成為聯絡江淮與中原的主要水道,也是南北商品流通的主要渠道。唐代揚州、汴梁、蘇州、杭州等城市的興起,與大運河的關系密切。但是,因為山脈分割的關系,這張水運網絡無法在內陸將東南的福建及浙江南部、廣東東部連在一起,而東南海運應運而生。唐代游人入閩,常走海路,孟浩然的詩:“云海訪甌閩,風濤泊島濱。”說的即是這種情況。皇甫冉的詩:“孤棹閩中客,雙旌海上軍。路人從此少,嶺水向南分。”可見,他也是從海路入閩。其時,杭州還是一個海港城市,羅隱的《杭州羅城記》道:“東眄巨浸,輳閩粵之舟櫓;北倚郭邑,通商旅之寶貨。”從福州、泉州到廣東也有海路。五代末,龔慎儀致南漢國的國書中寫道:“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足下國都矣。”唐代成通年間一個官員說:“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刺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可見,當時福建與廣東雷州之間常有海船往來。雷州至今仍為閩方言區,與悠久的兩地關系有關。
通過海路運輸,唐代的水運運輸網絡從江淮擴展到閩中、嶺南。《唐語林·補遺》:“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舊唐書·崔融傳》:“天下諸津,舟航所居,旁通巴漢,前指閩越,七澤十藪,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艦,千舳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這里的水路,不僅是內陸江河的水運,還有東南的海運。
唐代的閩人不斷探航北方航道。唐末五代的閩王王審知派船只北上山東半島。“審知歲時遣使朝貢于梁,阻于江淮,道不能通。乃航海從登萊入汴,使者入海,覆溺大半。”《冊府元龜》記載:“審知每歲遣使朝貢,泛海至登萊抵岸,往復頗有風水之患,漂溺者十四五。”例如:“王保宜者,唐末為閩師持章赴朝廷,道路不通,乃泛海,因溺死。”王審知不顧傷亡繼續探航,是因為這條航線對福建來說不僅有重大的政治意義,而且還有重大的經濟意義。福建對外貿易發達,可是,福建自身的市場有限,只有把從海外進口的奢侈品銷往中原,才能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以故,北方航線實際上是福建商業的生命線,沒有它,福建商業利潤將削減一大半。五代末期,留從效竭力爭取向中原王朝直接進貢,其中也有經濟因素在內。在留從效給北周的國書中,留從效提出要在汴梁置邸,便是想在國都獲得一個商業立足點。后來,宋太祖答應了這一要求,他給留從效的敕書中寫道:“卿遠臨南服……貔虎之師徒甚眾,必資回易,以濟贍供……宜新其邸第,庶有便于梯航……今賜青州荷恩禪院,充卿本道回圖邸務。”這些話再清楚不過地說明留從效向宋朝廷進貢的原因。其時,福建船舶航行至渤海一帶的契丹國和渤海國。徐寅的《折桂何年下月中》一詩的序寫道:“渤海賓貢高元固先輩閩中相訪,云本國人寫得寅斬蛇劍、御溝水、人生幾何賦,家皆以金書列為屏障。”渤海國位于遼寧一帶,當地人并不善于航海,其使者高元固能來到福建,與福建船舶往來于二地之間有關。契丹國里,福建商人亦很活躍,閩國末年,北方后晉與閩國關系惡化,而后修復,其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說法是:閩國使者經常越海通航于契丹,與契丹關系不錯,于是,他說動契丹主向后晉國施加壓力,迫使其釋放閩國使者鄭元弼,這一事件反映了福建與契丹之間的廣泛聯系。五代后期的“北漢”位于山西一帶,此地亦有閩商涉足。“時諸方物產未通,賈客自閩粵來,以橄欖子獻于世祖”。
海運的興起,隨之而起的是海商階層。唐末福建籍名詩人黃滔的《賈客》一詩詠道:“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鯨鯢齒上路,何如少經過?”這首詩反映了中國海商的性格。“劉隱,其祖安仁,上蔡人也,后徙閩中。商賈南海,因家焉。父謙為廣州牙將。”唐五代,閩人常往來于北方與福建之間,楊澈“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于青州之北海”。《嶺表錄異》記載閩人周遇的海上歷程:“頃年自青杜之海歸閩,遭惡風,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此文中所說的“青杜之海”是指山東半島的沿海,他從山東半島航行到福建,是漫長的海上里程。泉州的官員們也經營海上貿易。據出土的唐大中四年(850年)的《鄭季方墓志銘》,泉州官員鄭季方被泉州委任為“浙江東道回易軍賜使”,后死于浙江會稽,這說明他是專門經營福建與浙江海上貿易的官員。當時還發生過閩商與荊楚商人在汴京爭邸的故事:“荊楚賈者,與閩商爭宿邸,荊賈曰:‘爾一等人,橫面蛙言,通身劍戟,天生玉網,腹內包蟲。閩商應之曰:‘汝輩腹兵,亦自不淺。蓋謂荊字從刀也。”這些都說明閩商在北方市場上是很活躍的。因閩人出外經商多獲厚利,唐代中葉,劉禹錫論福建:“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獨孤及評價:“閩越舊風,機巧剽輕,資產貨利,與巴蜀埒富。”這種觀念與北方重農輕商的習俗是不同的。
要注意的是,海商階層是商業資本與航海力量的結合。自古以來,疍家人就航行于東南沿海港口、島嶼之間,商人很自然地雇傭他們的船只經營商業。于是,疍家人很自然地參與海上商業。久而久之,他們也成為海商,自行經營海上貿易。
以上論證說明,中國東南自古以來就存在著一支水上民族,他們航行于東南沿海各地,建立了早期的海洋文化。唐五代時期,北方移民南下長江以南區域,東南州郡獲得很大發展。漢人的制造技術傳入東南,與疍人的航海技術融合,使東南傳統的造船業升華,運輸力量倍增。由于東南海港城市的興起,東南海上貿易逐步繁榮,海商階層崛起,這都是海上絲綢之路發展的基礎。
五、東南海上力量向海外的發展
海上絲綢之路的主線是由中國東南沿海港口到東南亞海域,再延伸到印度及波斯灣。中國與東南亞的海上聯系極為久遠。這是因為,疍家人海洋文化很早就向東南亞傳播。
在中國學者中,最早對中國東南海洋區域的石器文化進行研究的是林惠祥、凌純聲、張光直等人,他們及后繼者的研究表明,在環臺灣海峽與環南海區域,有一個不同于中原、長江流域的考古文化,這就是南島語系的海洋石器文化。它的典型器物是“有段石錛”,或稱“有肩石錛”。石錛是一種掘地耕田的農具,東南亞的這種農具特點是在石錛上留一個“石肩”,可與木棍綁在一起,從而使掘地更輕松些。在福建、臺灣所發現的石錛較為簡單,而東南亞諸島發現的石錛較繁復,器物的發展總是從簡單到繁復,這說明石錛的起源地在福建、臺灣,并在東南亞獲得逐步發展。它說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便有古閩人乘著小船向東南亞諸島航行,從而將始于閩臺的石錛文化傳播到東南亞各地。并從東南亞向西太平洋傳播,從菲律賓群島到印度尼西亞,再到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等地,是為著名的南島語系海洋文化。這一文化的主人乘坐獨木舟與木筏,穿越于群島之間,相互交易手中的物品,漸漸地將他們的語言、工具和文化傳播于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島嶼之間,其東至復活節群島,西至馬達加斯加島,東北至夏威夷群島,顯示了超強的越海能力。這一事實表明:福建南部民眾與東南亞區域及南太平洋地區很早就有海上聯系。迨至青銅時代,中國沿海及環南海區域長期使用黑星寶螺作貝幣,這都說明古老的海洋商業維系著各地的聯系,否則不會有同一種貝幣流行那么廣的區域。事實上,直到明代初年,暹羅國尚使用貝幣:“以海賒代錢,每一萬個準中統鈔二十貫。”當代東南亞諸國的調查也發現,不論是泰國、柬埔寨還是印度尼西亞,都有以船為家的水上人家,他們大都自稱祖先來自中國。
以上這些資料表明,自古以來,環中國海區域的島嶼,都有一支以船為家的水上人家在生活。他們編織了遍及環中國海區域的海上網絡,以貝幣為交易媒介,常有船只往來于島嶼之間。這是東方海洋文化的成就。
迄至漢代,中國東南部與東南亞諸部建立了經常性的海上聯系。
漢朝的軍隊消滅嶺南的南越國之后,將其疆土擴展到中南半島的林邑、日南等地,一般認為,這些地方即為越南南部及柬埔寨一帶。從漢代到唐代,越南北部的交州一直屬于中國政權管轄。當時中國本土與交州的聯系即有水路,也有陸路。《后漢書·鄭弘傳》記載:“舊交阯七郡貢獻轉運,皆從東冶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系。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于是夷通,至今遂為常路。”該文中的東冶,今為福州,早在漢代,福州就是海路要津。又如葛洪的《神仙傳》記載,東漢時,候官人董奉在交州士燮處作客多年,一日欲離開交州,“燮問曰,君欲何所之,當具大船也”。這也說明當時閩中與交州的交通主要用船。漢朝曾派遣使者探航南海及印度洋的黃支國等許多地方。《漢書·地理志》說:“蠻夷賈船,轉送致之。”這句話可譯作:“蠻夷和商船,輾轉送漢使到達諸國。”其中“賈船”二字,應是指中國商人的船舶。三國時期,東吳也曾派康泰、朱應等使者出使南海國家,可參見康泰的《扶南傳》《吳時外國傳》等書。
唐代交州仍是唐朝的領土。唐代咸通年間唐軍在交州作戰,糧食供應成為一個問題。有個臣僚建議從福建運糧:“臣弟昕思曾任雷州剌史,家人隨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只可致千石,自福建裝船,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致三萬石至廣府矣。”糧食到廣州之后,又可沿海路向安南運輸。這反映了交州與福建廣東等地的聯系。其時,東南亞諸國多到廣州貿易,據說黃巢進入廣州之前,廣州有數萬胡人。福州、泉州的對外貿易也很發達。大歷時詩人包何詠泉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還珠入貢頻。”說明泉州已是外商進貢中國的主要通道之一。其時,波斯的商品也進入了福建。“饒江其南,導自閩,頗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這說明唐代福建港口即有波斯貨銷售,并可轉運上饒等地。唐代福建的福州、泉州二港與廣州、揚州并稱為對外貿易的三大區域,唐文宗曾下令撫恤沿海胡商:“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從唐文宗的詔書看,當時的東南海港已經是對外貿易的主要港口。
有來必有往,從閩粵出海的船舶也不少。《范太史集·王延嗣傳》評價閩王王審知:“招來蕃舶,綏懷海上諸蠻。”當時福建的沿海,多為“平湖洞蠻”等南方民族占據,王審知安撫這些民族,使之為閩國效力,并讓其與海外諸國通商,由是取得了“貿易交通,閩俗康阜”的結果。閩國泉州刺史王延彬在任上發展對外貿易,“每發蠻舶,無失墜者,時謂之‘招寶侍郎”。所謂“蠻舶”就是由福建沿海“蠻夷”駕駛的海船。他們原來就航行于東南沿海,對海道十分熟悉,泉州刺史王延彬以商業資本驅動他們到海外經商,并獲得成功。王延彬之后,留從效、陳洪進等泉州統治者,都很注意征發當地富戶參與海外貿易。史稱留從效“陶器、銅鐵,泛于番國,收金貝而還,民甚稱便”。宋代泉州設置市舶司之后,為了確保每年的賦稅,“每年冬津,遣富商請驗以往,其有不愿者,照籍點發”。許多商人活躍于海外,《宋史》記載:“今主舶大商毛旭者,建溪人,數往來本國,因假其鄉導來朝貢。”洪邁的《夷堅志》記載:“泉州人王元懋,少時祗役僧寺,其師教以南蕃諸國書,盡能曉習。嘗隨海舶詣占城,國王嘉其兼通番漢書,延為館客,仍嫁以女,留十年而歸,所蓄奩具百萬緡,而貪利之心愈熾,遂主舶船貿易,其富不貲。”乾道三年(1167年),福建“本土綱首陳應等,昨至占城蕃”。有些商人在海外獲得政治上的發展。宋初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后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晉江東石人)為主”,開創李氏王朝。南宋末,李氏王朝滅亡,開創陳朝的陳日煲,原為福建長樂人,他在廣西從事邊界貿易時,被越南人看上,后在越南做官,最終當上皇帝。宋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本土商人積極赴外經商有關。
福建人中也有赴朝鮮的,《宋史·王彬傳》記載:“王彬,光州固始人,祖彥英,父仁侃,從其族人潮入閩。潮有閩土,彥英頗用事。潮惡其逼,陰欲圖之。彥英覺之,挈家浮海奔新羅。新羅長愛其材,用之,父子相繼執國政。”唐宋以來,福建商人常到高麗貿易。宋唏根據朝鮮人鄭麟趾的《高麗史》的記載統計,自1012-1278年的266年間,宋商人赴高麗者達129回5000余人。又據日本學者木宮正彥《日中文化交流史》的歸納,唐代有不少中國船只航行到日本做生意。著名的鑒真大師七次渡日,多次乘坐商人的船只。
綜上所述,中國東南沿海的閩浙粵諸省一直存在著一支水上人家,他們繼承了古代夷越人的海洋文化,以船為家,一生漂泊于海洋。他們的海洋網絡遍及臺灣海峽及南海周邊國家和島嶼。中原漢族南下東南區域之后,與當地族群融合,使疍家人的航海技術大大提高。唐宋之際,東南經濟崛起,東南諸省成為中國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區域,商品經濟發達。區域之間的貿易使海運業興起,傳統的疍家人發揮其所長,成為海運業的主要從業者,并逐漸融入當地漢族。因中國沿海自古與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保持著海上聯系,東南經濟的發達,從事海外貿易有巨大的利潤,于是,由疍家人駕駛的“蠻舶”遠赴海外經商,出售中國的絲綢、瓷器等商品,收購東南亞諸國生產的香料、棉花等物資回國。海上絲綢之路就是在這個商業流程中興盛起來。
[責任編輯:杜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