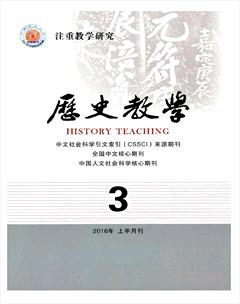試論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遺緒
馮爾康
[摘要]明清徽州名族處在君主專制社會晚期的科舉制時代,中古士族則在君主專制社會中期九品中正制時代,都是世系綿延歷時數百年,均致力于本身及社會文化教育事業,為自身凝聚與出仕需要進行族史的撰寫,都為堅守門第婚姻而強調門當戶對。在這些基本要素方面兩者相同,但在出仕上,士族出任高官,長期掌握朝政,名族官宦無常,絕不能操縱政權。鑒于名族與士族表象的類似與實質的相近,可以說名族是士族的遺緒,具有傳承士族文化的意義。
[關鍵詞]徽州名族,中古士族,名族志,俗美,宗族通史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57-6241(2016)06-0020-09
嘉慶年間編修徽州府志,擔任人物、掌故寫作的龔自珍提出并實踐寫作《氏族表》的主張。據《徽州府志氏族表序·義例》云:“載大宗,次子以下不載,夫宗法立而人道備矣;次子之子孫,官至三品則書,不以宗廢,貴貴也琪以立言明道,名滿天下則書,不以宗廢,賢賢也。自今茲嘉慶之世,推而上之,得三十世以上者,為甲族得三十世者,為乙族得二十世者,為丙族。”龔自珍以氏族傳世多寡為主,兼及有無高官、明賢作為標準,將氏族區分為甲乙丙三級。他的這種分類標準,令筆者聯想到南北朝時期士族的品級劃分及其原則,就將明清徽州名族與中古士族聯系起來,再思及兩者其他相同和相異之處,遂有前者為后者遺緒的想法,進而聯想到徽州名族的社會屬性、在中國宗族通史中的位置與歷史地位,茲將淺見紹述于次,敬祈方家指教。
一、何謂名族及將其納入中國宗族通史中研究課題的提出
龔自珍所說的徽州氏族,在明清時代徽州人的觀念中是“名族”,徽州史上先后出現不只一種名族志,有的縣有名族志,甚至休寧東門邵氏的族史亦名《龍源名族志》。另外,從宋代到當世,徽州名族史在地方志中的專題表述,不絕如縷。“名族志,志名族也”。名族志是敘述名族歷史的圖籍。那么何謂明清徽州名族?為何聯想到士族?名族在中國宗族通史中有何地位?
㈠何謂明清徽州名族
徽州“名族”及其應具備的條件,需要從編纂名族志的作者及其同時代人的認知來考察。歙縣人、江西布政使左參政鄭佐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在《新安名族志·序》寫道:“名族志之義有二焉:尚世也,尚賢也。族衍于世,世延于賢……吾新安婚姻問家世,派系征譜牒,則猶沿襲成俗,不失前古遺意。故其為族也,有殊邑聯宗、數村一姓之蕃。其為婚姻,有貧不偶富、賤不偶貴之異。其先代墳墓之存者,遠肇齊梁,近自唐宋,百年十世者勿論焉。此其尚世之不系于世祿,他郡罕及之也。”“名族而責之實也,則見其前開后承,或以明道集成而功存著述,或以效忠盡節而跡秉丹青,或悖孝友以導俗興仁,或樂恬退而修德守約,或政治晡燁于當時,或文章傳誦于后世。”他將名族特征歸納為“尚世”與“尚賢”。尚世,不只是世祿,更要世系綿延不衰,族大人眾,標志在于有千年祖墳、萬千人丁;尚賢,有開創之賢人,還要有后繼的賢人,前后輝映,即由有業績之官人、學者做到孝悌忠信、闡明學理、倫理。另一位作《序》者祁門王諷同樣強調賢人的作用,所謂“故族之名,名于人也”。并具體地說出明賢的價值:首先,賢人以其立德立功立言光耀家國,即“在一家光一家,在一國光一國,在天下光天下。世稱舊族,其流風遺韻,直可擅譽望于一鄉,而同天地于悠久者,其上者豈不以立德在希圣,立功在輔世,立言在名道,而光在天下古今者”。其次,賢人“以忠孝節義張正氣,官守言責以垂政聲,詩文紀述以列詞苑,而光在一國者”。復次,是功名爵位的傳承:“以科名爵位世續書香而光在一家。”深入說明名族飲譽鄉國,為國家天下增光彩,且能悠久傳世。萬歷朝兵部左侍郎歙縣人汪道昆(1525~1593年)在《太函集·論巨室為庶人楷模》中說:“巨室,即所謂大家,固庶民之綱紀也。”指明名族是倫理道德的楷模,起著庶人表率作用,以此不同于一般民人和家族,也就是說名族重視人倫綱紀,是其必備品格。關于名族實踐綱常倫理的意義,隆慶二年(1568年)《珰溪金氏族譜》中的《陳俗》予以高度評價:“族必有俗,族之大小惟視其俗之如何。俗美矣,即有小族亦可言大;俗不美,即有大族乃所以為小,大小之分不系乎人力之眾寡厚薄,而系乎其俗。”族之大小,不在于人數多寡與爵祿,關鍵在仁厚敦讓,孝悌忠信,與人為善,有美俗者即為大族、名族,否則非是。到清代,乾隆朝軍機大臣休寧人汪由敦(1692~1758年)在休寧古林《黃氏族譜序》中寫道:“其族又多聚處而親睦,病相急,死相葬,婚嫁相饋,遺有無,相周血,不然者以為非我族類。”原來族人之間講究親情,互助互救,富能濟貧,不這樣行事,就不被宗族、族人接受,是以人人自我約束,行為端正,風俗醇厚,是美好的社會風尚令宗族興旺發達,歷世綿延。清季,績溪邵氏將老譜祠規、前賢宗規及當下應行之事匯編成新祠規,其中有“族講”一條:“每季定期由斯文、族長督率子弟赴祠,擇讀書少年善講解者一人將祠規宣講一遍,并講解《訓俗遺規》一二條,商榷族中大事體。各宜靜聽遵行,共成美俗,實為祖宗莫大之光應置紀善籍一本,每歲終將本族之有大善者由公核實紀籍,以示風勵。”設立族講制度,定期開講祠規和乾隆朝協辦大學士陳宏謀編輯的《訓俗遺規》,年終進行善事登記,令人向善,學做好人。以此美化風俗,形成美俗。邵氏的“美俗”與汪由敦的“親睦”、金氏《陳俗》后先輝映。
綜合眾多明清時代人士的徽州名族論述,對名族的含義作出界定,似乎可以用歷世久遠、賢能治家、文化立言、禮儀美俗、門第婚姻二十字五個方面來描述。歷世久遠,家族淵源,遠者兩晉六朝,近者唐宋,歷時數百年、上千年,傳世幾十代,族群繁衍,眾達千丁萬戶,散布徽州各村鎮、府縣城關,乃至外遷全國各地,及至清明掃墓,有千丁祭祀之盛。賢能治家,家政井然有序,屢屢出人才,涌現明賢、仕宦,延續家聲。文化立言,重視文化教育,開辦書院,組織文會,研討經史,在各種文學藝術領域多有成就。禮儀美俗,是族人之間按照宗法性倫理、規范行事,以祭祖儀式、頒胙、飲胙及族講等形式教化族人,孝悌和睦,形成優良風尚,成為社區民眾效法的楷模。門第婚姻,嚴禁與賤民婚配,講究主仆名分,以保持族人血緣的純潔性,維護名族社會地位。在這五項之中,歷世久遠、人丁眾多、良賤不婚是名族的基本條件與外部特征(外在表現);賢能治家是宗族成為名族的根本保證;文化立言、禮儀美俗之講究禮法是名族的精神內核。歸納名族的這些特征,是否可以給明清時期徽州名族以這樣的定義:歷世久遠的血緣群體,在賢明仕宦紳衿主導下從事文化建設,形成宗法性仁讓敦厚的人際關系和社會風尚,成為民間楷模,并以此不同于一般的宗族。
(二)魏晉南北朝隋唐士族特征
筆者的中古歷史知識貧乏,僅就所知,認為中古士族有五項特征:
一為高級官宦世代相承的血緣群體。北魏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詔定姓族,規定漢人士族的“郡姓”層級:“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者,為‘甲姓;就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稱為“四姓”。成為士族的條件是連續三代有高中級官員;因需要三代連續任職,所以成為世代簪纓之族,又由于士族擁有恩蔭權,起家官清貴,品秩高,甚至以六品為起點,比較容易保持世代為高官。
二是門第婚姻成為士族維持高貴地位的輔助手段。士族門第高貴,婚姻講求門當戶對,而其高門第為人羨慕,向往與之聯姻以提高社會地位者甚多,到南北朝后期衰微中的士族靠賣婚維持生計,作為維持士族地位的一種手段,要賣婚又要拿架子,往往給新貴碰釘子。唐朝政府為打擊舊士族,規定婚姻財禮的數量,限制舊士族的受財。唐高宗(649~683年在位)限制超級士族間的通婚,下令禁止隴西李寶、太原王瓊、滎陽鄭溫、范陽盧子遷、清河崔宗伯等七姓十家不得互相嫁娶,但是這種禁止反倒提高了舊士族的身價,收效有限。唐文宗(826~840年在位)要把公主嫁給士族,還怕人家不樂意,因而憤恨不平地說:“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員而為閥閱,我家二百年天子顧不及崔、盧耶?”
三是高度重視文化教育并有著優異的文化學術成就。惟有重視文化教育,提高成員文化品質,才能累世出仕。生活在膏粱之族的瑯琊王僧虔(426~485年)說:“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書數百卷耳。”深知士族保持長盛不衰就在于讀書掌握文化。瑯琊王氏之度支尚書王筠認為有文化,代代有文章傳世,是王氏家風,要求子弟“仰觀堂構,思各努力”。《南史》作者李延壽總結王氏歷史,稱其先世“并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說到陳郡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人各有能,茲言乃信”。高度重視文化,王謝才能出現王導(276~339年)、謝安(320~385年)、謝玄(?~388年)、謝靈運(385~433年),謝道蘊、王羲之(303~361年)等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思想家、藝術家,成為書圣、山水詩創造者。
四是為人仰慕的優雅閑適生活方式。士族具有特定的風范、門風,表現其獨特身份。南北朝末年顏之推(531~約591年)說當時南方士人穿著香料熏過的衣服,在光臉上搽紅粉,乘坐長轅車,腳登高靴,坐在織有方格圖紋的綾羅墊上,倚在多種顏色絲線織成的靠枕上,周圍陳列古玩珍寶,從容出入,人們看他那神采飄逸的姿態簡直像神仙。衛玠(286~312年)被“看殺”的故事,適足反映士族的豐彩。《晉書》說他五歲“風神秀麗”,七八歲時在京都(洛陽)“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觀之者傾都”。他是有名玄學家,“好言玄理”,有見識,在永嘉之亂前說服母兄,奉母南遷。為人道德高尚,理解與原諒他人,“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衛蚧不僅人長得秀麗,為人風雅有識量,受人仰慕。他到建鄴(南京),“京中人士聞其姿榮,觀者如堵。玠勞跡遂甚,永嘉六年(312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王導說他“風流名士,海內所瞻”。道出他被“看殺”客觀原因。這種優雅閑適風度是士族的必備條件。士人講究穿著、儀容、氣度、語言、飲食,否則就不配做士族。
五是士族為特權等級、高尚宗族,具體情形下詳。
總之,士族擁有食邑與依附民,具有一定意義上的貴族性,它是以文為主的高官、高等級、高層群體聯姻的三位一體血緣群體。
㈢思考徽州名族與士族聯系問題
緣于龔自珍將名族內部區分為三個層級,令筆者想到名族與士族既然都是血緣群體,名族與有六個層級的士族有無承緒關系;進而想到士族由官位決定,名族之為名族也離不開仕宦因素:士族文化成就輝煌,名族緊步其后:士族生活方式為世人仰慕,名族美俗為庶人楷模。兩者既然有這些相近、相似之處,就有必要思考這兩個不同時代的宗族有無關聯,是何關聯的歷史課題了。
名族自然不是士族,與豪族、小族也不相同,那么它在中國宗族通史的宗族分類上屬于哪種類型呢?若考察宗族結構式,它處于何種位置,也就是說在中國宗族通史中它處于哪種位置?接下來就需要明了它的社會歷史地位了。
二、名族與士族的同與異
明清徽州名族與中古士族處于不同的歷史時代,社會背景多有差異,特別是與它們密切相關的選官制度迥異,一個是九品中正制,另一個是科舉制,因此它們不可能完全相同,名族也不是士族的復制品,事實上歷史上的任何一種現象、團體、人物是不可能完全復制的。名族與士族是兩種宗族,但是又有許多相近、相似的成分,是有共同點,亦有差異,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這里使用抽象觀察方法探討名族與士族表象上的同與異,以為下一目的分析奠定基礎。
(1)世系綿延的血緣群體
名族、士族都有血系數十世、歷時數百年歷史。瑯琊王氏、陳郡謝氏都是同東晉、南朝相始終的著名士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清河張氏、聞喜裴氏、滎陽鄭氏、隴西李氏、杜陵韋氏、天水趙氏,以及南方土著士族朱、張、顧、陸等氏,無不有數百年的傳承。
明清徽州名族,如同鄭佐所說的“尚世”,有的是東晉以來家族的延續。汪由敦在前引《黃氏族譜序》中還說:“吾徽著姓巨族,視他郡特盛。代序遠者二三千年,近亦數百年。族之人多者數萬,少亦千計。……今世稱甲族者,所在多有,顧往往不如吾徽之盛。”龔自珍(定庵)據其歷世標準,開列出徽州大姓洪、吳、程等十五個,民國間休寧人許承堯認為不只是十五個,他說:“吾徽最重宗法,定庵言大姓甲于全國,固非夸也。惟所標舉十五族,不知何據?若以吾許姓計之,自遷徽祖儒公至承堯,得四十四世,譜系井然可征。是十五族外,猶有遺漏矣。”《新安名族志》所收傳世久遠的名族八十八個。
(2)世代高官與官宦衿士代不乏人
士族中的甲族(膏粱、華腴、甲姓、乙姓)盡為世代仕宦高官,低等士族也擁有世代中層以上官員。確定士族的原則業已明白無誤地表明,士族就意味著仕宦,特別是高級官員家族,平民宗族與士族沾不上邊。士族的官宦歷史不必贅言。
明清時期,徽州舉業興旺,官員眾多,令人矚目。以明代中后期的歙縣為例,許承堯說:“吾歙京朝官,以晚明為極盛。……同時以進士官部曹及守令者約三十人。……此誠他縣所希,皆由進士出身也。”這些歙縣官員是武英殿大學士許國,兵部左侍郎汪道昆,戶部侍郎方宏靜;禮部右侍郎張一桂;南戶部侍郎吳仲明;工部左侍郎畢懋良;戶部尚書程國祥,進士應天府尹方良曙,大理知府程道東,等等。清代的徽州,有“連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之說。殿撰是狀元首任官職,翰林,系中進士者的榮譽官選,大學士不乏翰林出身者。此種俗諺,反映清代徽州人科舉出仕者多。
在出仕方面,士族必定有官做,且多高位名族,亦以有官員而興旺,但不是世代出官宦和高官,不過它有衿士和讀書人,有強勁的官宦預備隊。
(3)婚姻重門閥與良賤不婚
前已說明士族實行門第婚姻,相互嫁娶,世代聯姻,謝安在書圣王獻之兒子中為侄女“詠絮之才”的謝道韞選婚,最后選中王凝之,就是顯例。
名族門第婚姻,主要是強調婚姻的門當戶對,堅守良賤不婚原則,對與賤民婚配的族人處以開除出宗的懲罰。歙縣蔚川胡氏《蔚川胡氏家譜-規條》中的“重婚姻”規則:“婚姻,宗族之門楣所系至重,故婚娶者不但取其閥閱,尤當擇良善。……族女字人……茍利其貲財,以致閥閱不稱、良賤不倫者,眾議罰其改正,違則削其宗系。”徭受州彭城錢氏《家規》的《正婚姻》云:“凡嫁娶須擇門楣相對、家世清白者,斷不可草卒(率)了事,致辱門庭。違者,革出祠外。”不得入祠,革出祠外,意味著削譜除宗,處分極其嚴厲。
(4)重視族譜編纂,目標有所不同:一在出仕與聯姻,一在凝聚宗族
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說:“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由于譜系。”“簿狀”,即“姓氏簿狀”,是一種關于宗族史的譜書;“譜系”,亦為一種譜書。兩者相通,都是宗族譜系專著。簿狀,政府用以選官,所謂“有司選舉,必稽譜籍,而考其真偽”,因此,嚴格要求譜牒資料的準確性。士族成員據以被舉出仕;譜系,是士族聯姻的考察資料。譜系之作,在中國古代史上出現四種類型,即帝王諸侯世譜,通國氏族譜C百家讖,地方宗族譜洲郡讖和家族譜。士族制最盛行的兩晉南北朝時期,相應的是著力于通國氏族譜的編纂,其次是關注州郡譜。員外散騎侍郎賈弼之奉晉武帝之命主持修譜,乃搜集各族宗譜,審核考訂,編撰《百家譜》《姓氏簿狀》。梁武帝詔令北中郎咨議參軍王僧孺知撰譜事,改定《百家譜》,他乃撰成《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鈔》十五卷、《東南譜集鈔》十卷。兩晉南朝,賈氏的賈弼之、賈匪之、賈淵祖孫父子“世傳譜學”。王氏在王僧孺之外,王儉等都修纂譜書。因而賈氏、王氏兩個家族成為譜牒學世家。唐人柳芳講,六朝“官有世胄,譜有世家,賈氏、王氏譜學出焉”。就是說的這種情形。看來兩晉六朝之編修譜牒,主要是為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選官之用,次則為選婚。
徽州名族著力于自家文獻建設,編纂多種類型文獻,有一個一個家族的宗譜蹤族人物傳記的先德錄,如《潭渡黃氏先德錄》;家族聚居地的村鎮志,如《橙陽散志》《巖鎮志草》;匯集徽州府或某一縣名族史的名族志;匯集徽州府名族人士文論的文獻志,如程敏政的《新安文獻志》,程瞳的《新安文獻志補》,程廷策的《續新安文獻志》、汪洪度的《新安女史征》。在這些類型文獻中最值得留意的是宗譜與名族志。名族族族修譜,且多不斷續修。何以反復修纂?歙縣棠樾鮑氏乾隆續修宗譜,發凡起義云:“譜牒之作,蓋子孫錄其先人,務盡其實,所以尊祖收族也。”清初汪琬為休寧張氏宗譜作序,認為該譜有三善:“闕疑一也,尊祖二也,收族三也。”編修宗譜,記錄家族世代延續狀況,令族人各自明了自身及與他人的血緣關系,在祖宗的旗幟下凝聚成為一個整體,所以修譜起著收族與悖倫彝教化作用。州郡譜與士族制基本上是孿生物,唐代以后,州郡譜就很少有人制作了,而在徽州,元明清時期卻屢次出現,元代陳櫟編纂《新安大族志》,明代戴廷明、程尚寬等編撰《新安名族志》,曹嗣軒編纂《休寧名族志》。名族志書寫名族忠孝節義事跡,提倡名族美好社會風尚及其成員修養,從而提升徽州在全國州郡地位,同時因名族風俗惇厚,有利于社會安定,朝代延續。總之,以凝聚族人,激勵自身上進,提高名族素質和社會地位。
(5)一以貫之重視文化教育,但士族、名族主導思想有所不同
前面交代士族特征,已見其深知文化教育對家族的作用,不僅如此,他們同時關注全社會的教育事業。晉元帝(276~322年)尚未正式登基,錄尚書事王導上書建議恢復因戰爭而停辦的學校教育,令朝臣子弟就學。淝水之戰前后,尚書令謝石(327~388年)亦因戰亂學校遭到破壞,“上疏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當然,他們關心的是貴胄與士族子弟的學業。
明清徽州名族之極其注重教育可從科舉出仕者眾多顯現出來。由于投入文化教育事業,徽州名族成員的文化學術研究成就斐然,從三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多學科全面發展。以近現代學科分類說,徽州學人對哲學、文學、藝術、史學、方志學、考古學、文獻學、圖書館學、工藝美學及數學、天文學、醫學等領域,即人文學科、自然科學、醫學和工程科學,都有涉獵,均有成就,這就充分表明徽州是文化名郡,在全國的府郡中,躋身于南北二京、蘇州、松江、常州、揚州、杭州等文化名城之列。二是有在全國學科中占居重要地位的學派,就是經學中的皖派(徽派),成為清代漢學發展到高峰期的標志,還與吳派共同促成揚州學派的誕生。詩賦中有新安詩派。三是在一些不大的學科中,徽州學人占有一席之地,像醫學有“新安醫學”,書畫界有“新安畫派”。
在文化教育方面名族與士族的主導思想有所不同。南北朝時期,士族對儒道佛均有興趣,當然儒學是主流,不過許多士族人士是道教信仰者和支持者。清河崔浩支持魏太武帝反佛祟道,與北朝著名道士寇謙之(365~448年)關系密切。王羲之一房“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創造南天師道的廬山道士陸修靜,出身于吳姓大士族。吳郡士族顧歡(420~483年)著《夷夏論》,傾向于道教。晚年生活在隋唐之際的道士王知遠(530~635年),瑯琊士族出身,是茅山道的重要人物。有知識的道家注意天文歷法,研究煉丹術和醫藥學。因此,道教具有中古知識界團體的某種性質。可以說南北朝時期思想文化比較多元,有益于文化的發展。
名族篤信儒家理學,徽州是“東南鄒魯”之區,新觀念難于產生和傳入。江登云、紹蓮不無自豪地在《橙陽散志》寫道:“(徽州元明以來,英賢輩出,則彬彬然稱‘東南鄒魯矣。”他們意味中的東南鄒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思想觀念方面崇尚儒家理學,如同著作《易經讀本》《知魚集》的乾隆朝進士程塤所說:“吾鄉山水甲天下,理學第一,文章次之。”二是表現在人們依照理學倫理行事。徽州是朱熹故里,名族特別推崇他,他的《家禮》成為行動指南,借以營造良風美俗。
(6)內部組織結構相同
士族世系綿延,人員增多,于是宗族規模較大。如清河張氏、濮陽侯氏有近萬家成員,河東汾陰薛氏“世為強族,同姓有三千家”。幾千家、幾百家的宗族,內部血緣關系復雜,分出許多房,房下又分出支派。“彭城劉氏”,是漢代楚元王的后裔,南北朝時分為四大支,為彭城綏輿里、安上里、從亭里三支和呂縣一支。瑯琊王氏丞相王導一支,所謂馬糞巷房,子孫貴盛,屬于膏粱、華腴士族冱導的侄子、書圣王羲之一支,日烏衣房,家道不振,遠不及王導房。宗族房支的區分,表明宗族壯大和內部結構復雜,也反映宗族的分化和房分的重要。
前引汪由敦言徽州名族“人多者數萬,少亦千計”。《橙陽散志》云:“吾徽有千百年祖墳,千百丁祠字,千百戶鄉村。”可知名族擁有數千、數百子弟。績溪城西周氏于乾隆間重修祠堂,到工地干活的族人,“日指以千計,凡歲八稔而祠成”。每天有一二百名男壯勞力出工,想見周氏宗族成員之眾多。與歷史上的宗族相同,子姓多,就分出門支,以程靈洗族裔而言,分出歙縣虹梁、潛口、宣明坊、表里、馮唐、褒嘉坦、巖鎮、蝎田、方村、臨河、岑山渡、竦口,以及休寧漢口、婺源高安、祁門善和、黟縣南山、績溪中正坊等等分支。許氏出自唐朝守睢陽的名將許遠,后梁時避亂到歙縣,歷經宋元明,“族裔繁衍,間析居郡邑,及僑寓江淮”,分出九派,統宗祠祀奉許遠為顯祖,和支派九祖為不祧祖。黟縣鶴山李氏自始祖“肇趾于斯,越十數傳而子孫蕃衍”,分出四大房。徽州名族修譜,往往是“會修”“統宗譜”,會修是不在一個村落、地區的同宗族人聯合編寫宗譜,統宗譜就是匯集各個支派族譜編寫宗族全譜。《休寧名族志》編輯者曹嗣軒,著有《曹氏統宗譜》,該族分出休寧曹村、南街、草市、祁門曹村諸支派。
(7)居地與郡望
傳統社會人戶以“地著”,政府用戶籍治理,人有籍貫。具有血緣關系的人,要成為群體,需要居住在一起,是為聚族而居,因此宗族同特定地區聯系在一起,著籍于某地,所以某一宗族,就用著籍地區作為標記,瑯琊王氏、太原王氏,都是王氏,地域不一,是為兩個族群。士族一定有郡望,在姓氏之前,冠以地名,以為該士族的符號,如泰山羊氏、余姚虞氏、弘農袁氏、清河崔氏。地望一經形成,長期不變,即使遷徙,仍然冠著原先地望。僑置州郡亦然,如蘭陵蕭氏。隨著時間的推移,有的士族成員因遷徙改變郡望,成為新士族。如王方慶是瑯琊王導十一世孫,《舊唐書·王方慶傳》說他是雍州咸陽人,因他的曾祖父王褒于北周時徙居咸陽,子孫就在這里著籍,所以他的家譜——《王氏家牒》不再冠有“瑯琊”字樣。裴守貞,祖先原是河東聞喜人,后來才屬籍絳州稷山,他的《裴氏家牒》也不加聞喜老地望。地望的變化,反映舊士族的分化,其中的一部分以新士族的面貌出現,新的地望正表現這一狀況。新舊地望表明,士族同原籍關系的密切程度多有不同,有的士族遠離家鄉,游離于城市,同鄉土關系不密切。
明清徽州名族是真正地在著籍地聚族而居。《橙陽散志》在前引“千百戶鄉村”之后,又說徽州“一鄉數千百戶,大都一姓,他姓非姻婭無由附居,且必別之日‘客姓”。接著說,“城市諸大姓,亦各分段落”。明白無誤地道出徽州名族千百戶聚居在一個大村落或幾個村莊,既是在城中亦聚族而居。科舉制按照縣、省分配各級功名中式名額,名族讀書人要想中式,必須保持籍貫(或在他處寄籍),否則無由讀書仕進。出自鄉里,退則回鄉,是為“告老還鄉”“歸田”。明代萬歷間大學士、徽州歙縣城里人許國,因功,賜建石牌坊于居里,休致,賜馳驛回原籍。侍郎汪道昆晚年在天都太乙宮主盟白榆社,請蘇州名畫家周公瑕加盟,以娛晚景。名族扎根地域,離不開鄉土,它的力量也正在基層,在鄉里擁有權威,發揮建設家鄉的作用不僅管理內部事務,兼管村社建設和春祈秋報活動。前述乾隆間重建的績溪周氏祠堂,內有文昌閣、土地廟、文會所、能干祠等建筑,文會所是族內部分成員為培養讀書子弟組建的;能干祠是為紀念對宗族事務做出貢獻者建設的;文昌閣和土地廟兩所建筑是為全體族人信仰所用,它們設在祠堂內,表明宗族管理村民的土地神、文星信仰及其儀式,意味著宗族主管村民信仰事務。黟縣鶴山李氏為祭祀社神特別在道光十年(1830年)集資建立利濟會,“以備迎神鑾衛事宜,一應會規悉有成議”。為會能夠持久,先后“呈請前邑憲張及今邑憲謝批準立案,各存在案,庶幾業可世守”。名族主管村社祀事,同時借重文會措辦族內、族際重要事情。由于各村自辦的文會,“以名教相砥礪”,讀書人會依據主流意識辦事。績溪汪氏有需要向政府寫呈文,就由文會撰擬呈詞,如族內有節孝子孫,由文會撰文,向政府申報嘉獎;族中若有不得不向政府申報的事情(如打官司),尊長、鄉約與文會共同經辦:“本族倘有不得已公事,必致呈公,鄉約正副、尊長并文會,秉公呈治,不得徇私推諉。”族人之間、族人與外族人之間的糾紛,文會參與調解,免得到官廳廢財破家。方士庭的《新安竹枝詞》有句:“雀角何須強斗爭,是非曲直有鄉評。不投保長投文會,省卻官差免下城。”事實表明,名族強化組織,加強管理,在文會協助下,實現自我管理,維持與穩定社會秩序,成為一般宗族的楷模。
三、明清微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遺緒及名族在中國宗族通史中位置
有了前面兩個子目的陳述,可以進入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遺緒話題的討論了。主要是分析名族、士族異同與認定名族是士族遺緒的道理,將涉及名族、士族各自與皇權(政權)的關系,進而了解名族在中國宗族通史中的地位,以及由名族是士族遺緒,聯想到宗族文化對中國文化教育事業的影響。
(1)名族與士族在構成宗族重要成分方面基本相同
抽象地觀察,各個家族世系綿延數十世,時間長達數百年;士族與名族均崇尚文化素養,高度重視文化教育,士族以文化傳承,名族亦然:士族、名族內部,由于人丁眾多,依據血系區分出門派洛個家族熱衷于編纂族譜,士族重視編纂通國譜與州郡譜,名族注重編修宗譜,兼及撰修地區名族志:士族、名族均堅守門第婚姻原則,反對失類婚姻:士族、名族都離不開郡望鄉貫,以標明郡望與籍貫顯示注重根基。血系綿延而人丁興旺、血系分明、有聚居地是形成宗族的先決條件,族譜明析族人派系,起到保障宗族凝聚的作用,強調文化教育是宗族發展興旺的必要條件,在這些構成宗族重要成分方面,名族與士族基本相同。因此,才可能思考名族與士族的關聯,名族是士族的遺緒問題。
(2)名族與士族在與皇權關系中地位相差較大
考察士族、名族與中央集權制的皇權關系,需要高度重視九品中正制與科舉制的作用。這里不妨簡單勾勒中國皇權集權史,以及九品中正制、科舉制與皇權、士族、名族權利的關系。周朝是典型的分封制與宗法制時代,周天子只能管轄畿甸臣民,不能直接統轄諸侯領地,權力有限;秦漢實行郡縣制,皇權下到全國州縣,但是丞相制與皇帝分權,官員的選用,漢代行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發展為九品中正制,察舉制、九品中正制都是選舉制,皇帝必須尊重舉主的選擇,舉主地位高,士族高層為舉主,他們自己舉薦自己,保證士族出仕,保持士族地位。到了唐朝,實行三省制,正式取代丞相制,百官直接對皇帝負責,從而強化皇權,同時實行科舉制,選官的權力就集中到皇帝手中。科舉制成為皇權集中的重要輔助制度。有九品中正制的保障,士族地位穩定,不是皇帝能夠隨意擺布的。東晉南朝對士族尤為尊重,才有“王與馬共天下”之說,士族內部事務,皇帝不能過問,只得聽由士族作主。齊武帝寵信的中書舍人紀僧真是武吏出身,要求改為士族,武帝不好作主,讓他找士族首領濟陽江斅、陳郡謝瀹商議,結果紀僧真在江斅面前碰了釘子,這才明白:“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侯景向梁武帝要求娶瑯琊王氏、陳郡謝氏女子為妻,武帝告訴他,王、謝的門第太高,不是你能夠匹配的,你可以在江南朱、張士族以下的宗族中去找配偶,氣得侯景說我將來把江南的士族女兒都配給奴仆。紀僧真不得進入士族行列、侯景的向高層士族求婚之愿落空,充分表明皇帝不能干涉士族內部事務及庶族與士族政治地位的巨大差距。至此需要明了在君主專制社會里士族的社會等級與宗族結構中地置。簡單化的中國君主社會歷史上社會等級結構式是:皇帝-貴族與官員(特權等級)-平民(庶人)-賤民,士族成員屬于高級官員行列,處在特權等級上層。中古宗族的簡單社會構成,其結構式為;皇族(尊屬、疏周-士族(甲族之膏梁、華腴、甲姓、乙姓與低等士族之丙姓、丁姓)-平民宗族(豪族、寒門),士族是僅次于皇族的特權宗族。士族的宗族社會地位與社會等級地位相一致,是特權等級中的宗族。
明清徽州名族生活在科舉制下,能不能科舉出仕權在皇帝,作為“天子門生”的進士能不盡忠皇帝嗎?能不絕對秉命皇帝嗎?靠仕宦衿士支撐門面的名族只能處于忠誠服從的臣民地位,像士族那樣與皇帝抗衡,想都不敢想,想的是盡忠。明太祖頒布《大誥》,命學校生員誦讀講解,并從中出題測試生員,更向民間頒發,令民人到京城講讀。這項制度的貫徹,徽州名族成員努力執行,婺源視溪方林卿,“有耆德,國初為朝京父老,背誦《大誥》,面聽宣諭,欲擢之,辭以疾歸”。歙縣南市程叔翁,洪武間“被旨赴京,講讀《大誥》,賞賚有加”。方、程二人進京講讀《大誥》,是響應朝廷號令,以實際行動配合朝廷貫徹政令,所以他們本人也為皇帝看中。康熙帝頒布教化民間的圣諭十六條,官方奉命執行,名族立即響應。歙縣汪氏要求子弟遵行:“恭逢圣天子諄諄教民敦化,所頒圣諭十六條見奉各憲府主縣主實力舉行,嚴敕各鄉朔望宣講,凡兩族子孫務宜仰遵。”名族并將對族人忠君納糧的要求寫進規約。歙縣蔚川胡氏道光以前《譜規》:“先達謂人賢族斯賢。凡我后人須幼學壯行,在家為孝子悌弟,出仕則忠君愛民。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異日載之,自足為宗譜光。”強調做官者忠君,績溪邵氏《家規》進而開導眾人納糧當差以效忠朝廷:“忠上之義,擔爵食祿者固所當盡,若庶人不傳質為臣,亦當隨分報國,趨事輸賦,罔敢或后。區區螻蟻之忱,是即忠君之義。《傳》曰:嫠不恤緯而憂王室,野人獻芹猶念至尊。名列于譜者省之。”名族要求族人做忠于君上的蟻民(小民、順民),聯系它致力良風美俗的營造,充當了鄉里治理者角色。
(3)明清徽州名族是中古士族遺緒
鑒于明清徽州名族處在君主專制社會晚期的科舉制時代,中古士族則在君主專制社會中期九品中正制時代,都是世系綿延歷時數百年,都致力于本身及社會文化教育事業,為自身凝聚與出仕需要均進行族史的撰寫,都為堅守門第婚姻而強調門當戶對。在這些基本要素方面兩者相同,是以名族具有士族的濃重昧道,或者說類似膽是有一個較大差別,就是在出仕上,士族主要出任高官,長期掌握朝政,名族官宦無常,不要說控制朝政,連地方政權也難于操縱,因此不能將名族等同于士族。要之,處在不同時期、不同選官制度下的名族與士族是兩個事物,由于兩者表象的類似與實質的相近,因而筆者認為名族是士族的遺緒,一定意義上的延續。
(4)名族在中國宗族通史中位置
宗族在其內部有房支結構,在宗族之間同時有著不同類型、不同社會層級之別,簡單地說有特權階層宗族與平民宗族之分,而歷史上各個時期有一個或兩個主要宗族,縱觀宗族發展史,宗族的嬗變大體是:先秦皇族與貴族-秦漢世家-兩晉南北朝士族-隋唐新士族-宋代官員宗族-明清官員衿士宗族;宋代以降宗族民間化、民眾化,清代平民宗族趨于發展,到了近當代,宗族擺脫宗法因素,成為民眾家族群體及俱樂部式的宗親會。
明清徽州名族從實質上說是官員衿士血緣群體,它也有隸屬的世仆莊戶,出仕者也有一定程度的免役權,但絕不同于貴族,與政權的關系,概括地說:先秦周王宗室及同姓貴族宗族是政權核心力量;具有某種貴族性的兩晉南北朝隋唐士族是構成政權的主要成分;明清徽州名族與同時存在的其他地區望族是政權基層秩序的保障力量,獲得朝廷允許的某種鄉里“自治權”和族內管理權。
(5)士族歷史影響巨大,尤其在文化教育方面
中國家庭、家族極其關注文化教育,形成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這要歸功于士族的身體力行與倡導,同時也應歸功于科舉制,名族、望族賡續士族傳統,使得注重家族文化教育成為傳統社會主脈。
當代學術研究認為徽商有著“賈而好儒”的品質,然而何種社會因素使其形成此種特性呢?筆者想到兩點,一為徽州名族高度重視文化,深入人心,變成文化傳承基因,或者說名族成員血液中就有文化因子,為徽商承繼下來。二是名族美俗、好義的影響,前已說明士族講求優雅的生活方式,名族重在構建人際和合關系的良風美俗,徽商的樂善好施,盡力回報宗親、故里和新居地是美俗的傳承。
[責任編輯:杜敬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