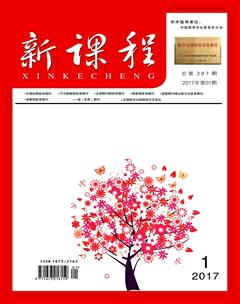跨界整合,促進教學能力的提高
李建忠
科學課上,一學生低著頭,認真地寫著語文作業,以至于我走到他旁邊,都沒發現我。我拿起他的語文書,故意問他:“這節課上什么?”他抬頭看著我,露出了一絲恐懼,吞吞吐吐地說:“上——科——學——”我反問道:“那怎么還寫語文?”他低頭不語。
我拿著他的語文書隨意翻了一下,發現第四單元是一組關于觀察的課文。“這不是跟科學上的內容緊密相連嗎?‘留意鮮花開放跟觀察植物那一課有關,‘觀察星星的閃爍跟天文有關,‘注意蜜蜂的飛行跟觀察動物有關……”我思考著。我越看越對這一組課文感興趣,尤其是習作——讓學生寫觀察日記。下課后,我仔仔細細地把語文教材的第四單元讀了兩遍,然后找到語文老師,把整合語文課與科學課的想法告訴了他。我們經過深入交談,最終商定把語文教材中第四單元的習作與科學教材中的觀察植物、觀察動物的單元整合。在語文老師的指導下,我掌握了習作教學的一般流程,于是一堂別開生面的跨界課拉開了序幕。
科學課上,我教給學生如何觀察蝸牛,按照怎樣的觀察順序去研究,用鉛筆觸碰蝸牛的觸角、撫摸蝸牛的腹部看有什么反應,還教給學生觀察蝸牛的一些其他細節,比如觀察蝸牛從什么地方排泄、蝸牛喜歡什么樣的食物的實驗設計等。因為這些觀察需要長時間進行,所以課下就布置他們在家進行,在上科學課時把自己的觀察進行分享。科學課的作業都非常好玩,所以孩子們比較喜歡,自然也愿意完成這樣的作業。第二次的科學課上,學生踴躍發言,積極分享。在分享過程中,我按照語文老師的指點——追問學生,在我的不斷追問中,學生不但把話說明白了,而且還把觀察的細節說清楚了。我說:“下面每一位學生,按照日記的格式,把剛才自己分享的觀察內容寫下來,咱們要比一比誰寫得有趣、好玩。”我的話音剛落,學生便拿起筆,沙沙地寫了起來。一節課,學生由說到寫,輕輕松松完成了一篇習作。
我問學生:“你們知道,剛才我們上的什么課嗎?”他們異口同聲地說:“科學課。”“錯!”我否定了他們的回答,“是習作課。”“不會吧,我一直感覺自己在上科學啊!”“我怎么沒感覺出是上作文課呢?”“天哪,我怎么沒感覺出作文難寫呢?我可是‘作文困難戶啊!”看著同學們一臉的茫然和詫異,我說:“下課后,語文課代表把同學們寫的觀察日記收起來,交到你們語文老師那里。對了,忘了告訴大家,你們寫的觀察日記,就是語文園地四里面的習作。”“啊?”語文老師看到學生寫的這些作文后,極為贊賞。
一次無意的發現,促使我進行了有意的跨界。自從上次跨界的成功,之后的我便屢試不爽。
學習“植物”這一單元時,我發現與美術有可結合之處,便讓學生帶上鉛筆、橡皮、彩筆以及素描紙,帶領學生走出教室,來到校園內觀察樹。我給學生講觀察大樹的順序,講觀察樹冠的形狀,如何描述等。講到如何觀察樹冠時,我除了從科學課的角度講,還從美術課的角度講,比如整體觀察、兩點連線觀察、橫豎對比觀察等。然后讓學生拿出鉛筆把所觀察到的樹冠畫下來。每個學生都饒有興趣地坐在地上畫著。還有的學生拿出彩筆,到大樹上制作樹皮拓片。臨下課,我讓學生從地上撿落葉,指導他們制作成樹葉標本。下一次美術課,我又根據美術課上制作樹葉貼畫的方法指導學生把標本制作成一幅幅美麗的樹葉貼畫。
四年級上冊科學教材中,有一課是《認識身體的結構》。人體的外部結構很容易講,通過眼睛看以及用手觸摸等方式便可以了解,可是人的內臟、肌肉、骨骼、血管等如何去觀察呢?借助模型是一種方式,但是學生不會有深刻的認識。于是,我把這一節課與體育課進行了整合。在教室內把人體的外部結構講完后,把學生拉到操場上,一人發了一根跳繩。我說:“接下來,我們進行一分鐘跳繩比賽,看一看誰跳得最多。預備,開始。”每個學生都拼命地揮舞著跳繩。“跳完之后,你感覺到了什么?”“老師,我的心跳加快了。”“用手摸一摸,能感覺到嗎?相互用耳朵聽一聽,能聽到嗎?”……通過與體育課上的跳繩比賽相結合,不但讓學生進行了體育運動,還讓學生認識到了人體的內部器官。
嘗到了跨界甜頭的我,把所教年級的所有教材借來通讀一遍,只要發現需要跨界的地方便與任課老師商議進行跨界教學。
跨界,不但縮短了各科教學的課時,而且還避免了重復性教學。我也在跨界中重構了自己的教學能力,成為一名全科教師。
編輯 李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