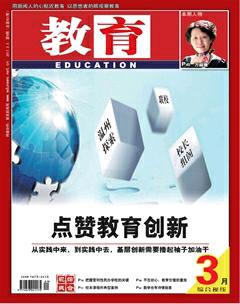客觀看待“學霸”當主播
客觀看待“學霸”當主播
盧澤華在2017年2月15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撰文指出:從宏觀視角來看,新興領域的涌現是社會發展的重要標志,由此打破社會階層的固化,成為社會進步的一大特征。以電競主播“女流”為例:她是內蒙古理科高考狀元、清華本科、北大研究生,這樣的學歷卻去當一個游戲主播,其經歷引發網友熱議。誠然,如今網絡直播還存在很多亂象,其就業背后的職業規范和保障體系也遠未建立起來。但是,面對新生事物,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放棄成見,用積極友好的態度接受它。當然,既然它是一個職業,有關部門和社會公眾就應該共同努力,促進其在職業規范、權益維護、社會保障、政策引導等方面形成完整的配套體系,這既是護航從業人員健康發展的有效途徑,也是消除社會成見的根本方法。
在最近的招聘會上,部分企業貼出的網絡主播招聘信息格外顯眼。可以預見,未來這樣的招聘還會持續增多。正如過去“女流之輩”不能讀書是偏見一樣,網絡主播是不務正業也是一種偏見。時代不同了,對于網絡主播等新興職業,我們當以平常心看待。畢竟隨著社會發展,社會價值和個人價值的體現也漸趨多元,只要有利于社會進步和個人發展,任何職業都應當得到鼓勵。從這個角度來說,“學霸”當主播,只要能體現正面價值,就是恰逢其時。
弘揚傳統文化不能脫離現實
王鐘的在2017年2月14日《中國青年報》撰文指出:《中國詩詞大會》在今年春節期間熱播后,獲得冠軍的復旦大學附屬中學學生武亦姝獲得了“古典才女”的美譽。然而,思想界隨即引發了背誦古詩詞是否有助于弘揚傳統文化的爭論。一些評論者認為:機械地背詩比的不過是記憶力,與一個人的古詩鑒賞能力無關。更有學者犀利地指出:少年人,背個詩詞算什么本事?
平心而論,《中國詩詞大會》推廣傳統詩詞文化的成效有目共睹。古詩詞傳播的最大挑戰是其本身缺乏現實活力。要讓傳統文化在更廣闊范圍生機盎然,就必須在更現實的層面產生影響。詩歌仍然是有生命力的文體,現代詩依然有較多受眾。將古詩詞元素融匯于現代詩中,或許是傳承傳統文化的好方法。像詩人鄭愁予那樣在創作中結合古詩詞意象,就是基于傳統的創新。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要寫詩成為詩人,古詩詞欣賞能力也未必與背誦能力成正比,但在日常文字表達中化用古詩詞,足以讓一個人在精神上雍容起來。
首先是文化受尊重,其次才是傳統文化受尊重。在傳統文化傳播過程中,要避免一種傾向——傳統文化成為獨立的、與現實隔絕的文化。與一些得到良好傳承的地域文化不同,中華文化在近現代經歷了劇烈的變動,舊文化幾乎在一夜之間從現實生活中退出,這種狂飆突進在世界范圍內都屬罕見。弘揚傳統文化不能脫離現實文化格局,在漸進中重拾瀕臨丟失的文化元素。
家長包辦作業是“角色錯位”
高路在2017年2月20日《錢江晚報》撰文指出:時代不一樣了,教育方式當然也得變。科學已經證明了家庭教育在教育中的分量,家長某種程度上的參與、督促,有助于孩子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我們不可能回到過去那個撒手不管全扔給學校的年代。那樣,對孩子的成長不利。現在孩子學業上的負擔也遠非以前能比,社會需要找到學校學生家長一起努力的合作方式。一些作業看似是增加了家長的負擔,但從長遠看恰恰可能會減輕家長的負擔,比如:我們小孩的學校要求家長每天在作業本上簽字,注明完成時間,這種方式就挺好。經過三年的積累,現在,孩子做作業基本不需要家長催。這也是家長的抱怨一般發生在小學低年級的原因,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正是塑造良好習慣的時候,需要一定強度的壓力。
但學校恐怕也得弄明白:哪些是的確需要家長參與的,哪些則是沒有意義的負擔。比如:讓一個一年級的學生滿大街去尋找標識廣告牌里的錯別字,這有啥意思呢?孩子字都認不全,找什么錯別字呢?被理解為折騰家長,一點都不冤。更不能用成人的評判標準來粗暴地對待學生作品,比如,家長放手讓孩子做了,做出來的可能文不對題,可能在成人看來是粗制濫造,那老師有沒有耐心去發現每件作品的閃光點呢?是否能準確地向孩子傳遞這樣的信息:自己動手做的才最可貴?
家庭作業的目的是為了教育本身,而不是制造出學生一個個都很能干、都多才多藝、少年天才的假相。有好的初衷還得掌握好度的處理,城市人的生活緊張,負擔本來就重,能在學校里完成的教學任務就不要帶回家了。各司其職,各自有各自的定位,讓家長疲于應對,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教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