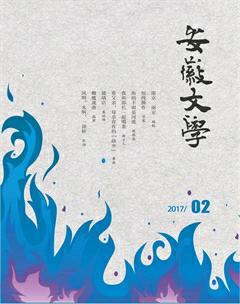形式的構(gòu)建與意義的探尋
劉霞云
在朱斌峰的前期作品中,我們明顯感受出作者醉心于對先鋒技巧的嘗試與實驗。也許作者已經(jīng)意識到純粹的技巧演練并不能傾情表達(dá)其對世界的看法,故在新作《玻璃店》中,其開始嘗試運用具有后現(xiàn)代主義傾向的現(xiàn)實主義手法,試圖為讀者展示一個介于現(xiàn)實與超現(xiàn)實之間的彼岸世界。
《玻璃店》采用典型的“福克納”式結(jié)構(gòu),試圖以第一人稱多重視角并置的敘述方式來還原一樁人命案的真相。關(guān)于“并置”,此乃古今中外創(chuàng)作中較為常見的一種寫作手法。如中國古代最早的《天凈沙·秋思》就是典型的意象并置,而在20世紀(jì)下半頁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對全球的強(qiáng)勢滲透,空間并置已然成為小說創(chuàng)作中常見的一種寫作手法。在中國,尤其進(jìn)入新時期以來,從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嘗試使用敘述者并置以來,中國諸多作家采用串聯(lián)式、并聯(lián)式、串聯(lián)并聯(lián)式等空間并置形式,實行敘述者并置、人物并置、故事并置、情節(jié)并置、意象并置等內(nèi)容,多角度踐行著空間并置的文體觀,進(jìn)而使中國當(dāng)代文壇產(chǎn)生了一批文體佳構(gòu),最典型如李洱的《花腔》、賈平凹的《病相報告》、莫言的《檀香刑》、羅偉章的《不必驚訝》等。當(dāng)然,眾作家選用并置手法不僅緣于此種敘述方式的經(jīng)濟(jì)與靈活,更多青睞于作品形式的構(gòu)建與作者寫作意圖的巧妙融合。以此來評判《玻璃店》,其在并置的形式構(gòu)建中是否透過表象,融合形式,妥帖地表達(dá)出起初的寫作意圖?我們不妨回到文本中去尋找答案。
“玻璃店”乃故事發(fā)生的中心地,故事圍繞發(fā)生在玻璃店的一樁人命案而展開敘述。按傳統(tǒng)的線性敘述方式,一女子死在玻璃店,死因不明,與之相關(guān)的玻璃店老板和員工莫名潛逃,警察介入偵查,故事隨著案情的進(jìn)展而推進(jìn)。若作如此處理,作品則變成一個老套的偵查故事,文學(xué)的品質(zhì)也隨之大打折扣。很顯然,在這部作品中,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揭示女子的死因真相,真正舉意是從故事中突圍,在形式的構(gòu)建中表達(dá)其對生活、人性的感悟和洞察。作品采用并聯(lián)式空間并置結(jié)構(gòu),按照現(xiàn)實生活邏輯,分別安排玻璃店馬老板、玻璃店員工春子、玻璃店對面洗頭房紅姐、街坊領(lǐng)居阿婆、玻璃店隔壁修摩托師傅以及公安等六個敘述者,以第一人稱內(nèi)視角,以獨白或?qū)φ劦姆绞较蜃x者展示各自隱秘的內(nèi)心世界,而這些或絮絮叨叨、或神神叨叨、或油滑無忌的傾訴正是小說的精神內(nèi)核所在。如馬老板,雖然身體殘缺,但他的精神世界寧靜而充實,外界的紛擾喧囂也擾亂不了他的內(nèi)心。如此心境中,“鏡子都是柔軟的,即使出現(xiàn)裂縫也會慢慢彌合,它們會給每個人一個完整的夜晚”。正因靈魂充實,堅硬的鏡子讓他倍感溫柔,而自春子像躁動的小獸一樣出現(xiàn)在他的生活中,他隱隱處于一種莫名的慌亂之中,他的安靜的靈魂受到了現(xiàn)實的沖擊,只能在寓意著古老傳統(tǒng)文明與歷史的“銅鏡”中獲得些許安慰與寧靜,但庸俗艷麗的女客戶的出現(xiàn)更讓他驚慌,盡管他沒有殺人,一種本能的恐懼使他選擇了逃離。很顯然,女客戶的死與馬老板無關(guān),而春子在飽受苦難生活的折磨之后,內(nèi)心深處依然善良,但物欲橫流的世界還是在一點點撕裂他年少柔軟的心,世俗的社會還是在一步步教會他冷漠與漫不關(guān)心。與馬老板喜歡“銅鏡”相對應(yīng)的則是,他喜歡意喻著暴力與現(xiàn)代文明的“玻璃”,面對無聊失意的女客戶的糾纏,他只能琢磨著如何施以暴力制服,但善良的他只是揮動了一下手中的玻璃碎片而已,其實在他揮動“兇器”之前,女人已死。可他不知真相,只能畏“罪”潛逃。而作為曾經(jīng)的風(fēng)塵女子紅姐,她對死者的人生經(jīng)歷了如指掌,對死者自殺的原因也了然于心。作為和死者有過相同人生經(jīng)歷的她深深體會到死者曾經(jīng)的迷茫與當(dāng)下的悵惘。但與死者不同的是,她選擇了以平淡的方式活著,而死者選擇了以極端的方式解脫。這三位敘述者對于故事的發(fā)生、發(fā)展乃至真相的揭示具有線索意義和敘事功能。
至此,案情似乎已真相大白,故事的核心情節(jié)似乎也已交代完畢,所謂的人命案件也只是一種虛妄的存在,不過通過這虛妄的鏡像,我們讀出了底層人生活的辛酸與不易,體味出他們無處逃遁的困窘與掙扎。但從作者的結(jié)構(gòu)設(shè)置來看,其更深的意圖似乎寄寓在后三位敘述者身上。接下來,作者讓年邁的阿婆看見馬老板逃進(jìn)“銅鏡”,讓修摩托師傅與公安進(jìn)行了一場充滿喜劇感的對話,讓公安對偵查行為本身進(jìn)行一番解構(gòu),這種安排意圖何在?嘲諷公安的無能、無聊與荒誕?“銅鏡”意象的再一次突顯寓意著“人性本善”的缺失與找尋?這不禁令人質(zhì)疑:這些就是小說的全部精神內(nèi)核嗎?我們常說,文學(xué)無高低之分,文體也無優(yōu)劣之別,但若文體的形式構(gòu)建與作品的表達(dá)意圖得以巧妙融合,那我們不得不說此“文體”乃妥帖的文體。以此觀照《玻璃店》,這部作品除了延續(xù)前期常用的“銀城”地名以及“玻璃”意象,在整體表達(dá)上并沒有彰顯出他意欲打造的文學(xué)版圖的地域色彩。作品已摒棄了迷宮式敘述,話語表達(dá)也不再晦澀難懂,從形式構(gòu)建到內(nèi)容表達(dá),都不再是一部與“先鋒”技巧有任何關(guān)聯(lián)的文本。作者大膽地選擇了一個庸常的故事素材,意欲通過非傳統(tǒng)的文體設(shè)置,在現(xiàn)實與歷史中尋找生活迷宮的出口,但從實際藝術(shù)效果來看,六個敘述者的人生言說稍顯單薄與含混,形式的構(gòu)建與作者的意義探尋存在一定的斷裂,庸常的故事依然難以支撐富有深度的理性反思。
當(dāng)然,對于一個具有明確寫作目標(biāo)和強(qiáng)烈文體探索意識的作家而言,存在不足正是其前進(jìn)的空間所在,《玻璃店》是朱斌峰不多作品中的一部,應(yīng)該也是其寫作的起點之一,我們堅信在今后的寫作中,他會以獨特的方式踐行自己的文學(xué)觀、文體觀,逐步打造出屬于自己的文學(xué)版圖,妥帖地表達(dá)出對這個世界的理解。
責(zé)任編輯 李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