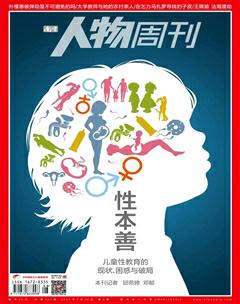《推銷員》 :一部沒有推銷員的伊朗電影
王寶民
首先讓我感興趣的是戲中戲的結構。
一對伊朗演員夫婦,在片中演了一出家喻戶曉的美國戲劇,僅此而已。沒有推銷員,也沒有推銷員之死,更沒有人們期待的平行敘事。
那為什么要把這兩個異質元素搭在一起呢?
“當今的媒體都試圖呈現我們彼此之間的不同和隔膜。但是我相信,我們之間的相同之處遠遠多于差異。”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在回答西方記者提問時這樣說,“表面看來,《推銷員之死》是一部關于推銷員的戲劇,但是它已經成為神話的一部分,不僅在美國,同時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
伊朗也不例外。據導演本人介紹,在“伊斯蘭革命”(1979年,巴列維領導的親西方的君主立憲政體被推翻,霍梅尼成立了政教合一的反西方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政體)之前,包括阿瑟·米勒的這部作品在內,一些著名的歐美戲劇經常在德黑蘭上演。革命后,盡管“西方腐朽文化”遭到官方反對和抵制,但其對于伊朗精英階層的影響遠比想象的深刻而久遠。
這正是本片主人公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之一:霓虹燈、爵士樂、西方電影與書籍等等,在如今的德黑蘭隨處可見;盡管妓院被公開取締,但那些暗娼依然隱身在居民區;男性與女性之間表面上仍“授受不親”,但實際上,一個被看作中世紀神權統治的當代伊朗,已然被一些敏銳的西方媒體形容為“伊斯蘭性革命”的前夜(美國《外交政策》雜志2013年5月31日的一篇題為《色情共和國》的文章聳人聽聞地作此斷言)。
然而,若以此推斷當今伊朗在私人領域已然跨過了“貞操至上”的保守主義鴻溝,恐怕過于樂觀和草率了。全球化讓人有一種錯覺:以為那些存在于傳統社會私人領域的種種偏見、陋習已被歷次革命所蕩滌。但事實上,它們從未消失,甚至在精英人群中。它們只是被巧妙地掩蔽了,暫時安全。一旦重要的沖突發生,這些“冬眠”的價值觀就會瞬間被激活,并且橫行無阻,聲勢浩大。
這包括性道德。每個社會都會有自己的貞操體系,有的簡單,有的復雜。復雜的貞操體系所關注的已經遠非身體,而是整個社會關系的構建,牽一發而動全身。別以為一個生活方式上完全西化的伊朗精英知識分子就會被這個體系豁免。恰恰相反,他可能陷得更深,隱藏得更深,以至于自己都不知道。當有意外發生,這個社會的抗震系統隨時可能崩潰,或至少造成裂痕。
這大概就是《推銷員》的意義所在。
阿斯哈·法哈蒂的電影經常聚焦于家庭私密領域,尤其是夫妻關系,確切地說,是他們之間的“裂痕”(導演在本片中多次訴諸影像修辭)。這些裂痕往往并非來自當事人本身,而是外在環境:社會觀念、文化差異、國家政治等等。這些像鏡子一樣反射到私人領域的強光,胃口很大,不僅要求當事人順服,而且要求自動順服。它們深入骨髓、靈魂甚至夢境,即便再高的教養也難以抵御日積月累的侵襲。
影片中,夫妻二人起初感情非常好,價值觀似乎也比較一致,是典型的德黑蘭中產階級知識男女,“政治正確”地活著或彼此愛著,即便發生了那個意外事件。影片結尾,這對夫婦仍在一起,生活或演戲,愈演愈真實、愈徹骨。
然而我們清晰地看到那個裂痕,在他們之間,如此醒目。
《欲望號街車》(1951)
導演:伊利亞·卡贊
主演:費雯麗、馬龍·白蘭度
若干年之后,我仍然記得打在女主人公面龐的強烈光線。那是一道巨大的傷口,被田納西·威廉斯寫在劇本里、被費雯麗呈現、被馬龍·白蘭度揭發……那是一個美好時代,人們對于一部“不道德的、墮落的、粗俗的和有罪的”電影趨之若鶩。
《孩子王》(1987)
導演:陳凱歌
主演:謝園 楊學文 陳紹華
牧童、霧、孩子王和圓形物體。神秘的動機。草帽下永遠看不清的臉。低低地走過,消失在霧中。牛鈴聲久久不去。他來自何方?為何讓我心中一動?我還能再見到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