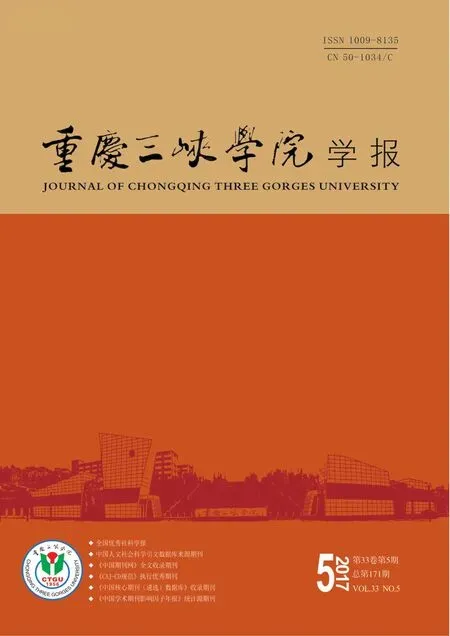郭敬明書籍暢銷背景下的受眾、書企、作家
楊 曙
?
郭敬明書籍暢銷背景下的受眾、書企、作家
楊 曙
(常州工學院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常州 213022)
一些理論家認為郭敬明為代表的暢銷書籍在文藝消費過程中存在一定的缺憾。事實上,消費民主文化、造粉工程、受眾內心缺失促成了受眾的粉絲文化;行業競爭、網絡娛樂競爭促成了書企營銷工程的打造;消費市場中的作家功能、作家自身發展、文化產業導向促成了作者明星身份。在受眾粉絲文化、書企營銷工程、作者明星身份的三重影響下,郭敬明的暢銷書必然要順應資本權力來實現其暢銷。
資本權力;暢銷書;粉絲文化;營銷工程;明星身份
郭敬明被諸多理論家關注,一些理論家認為,以郭敬明為代表的暢銷書籍在文藝消費過程中存在一定的缺憾。當前的一些文藝消費中存在著非理性行為,以郭敬明為代表的暢銷書語言簡單,作品意義與社會現實的纏繞度較低。如蔣承勇在《文學評論》2014年第3期撰文認為,太多的炒作、太多消費文化的影響,左右著文學傳播,敗壞了文學品味,當今一些產業化的文學在不斷傳遞負能量,一些作家創作出彌漫著欲望和血腥的產業化“作品”奉獻給讀者,讓作者與讀者彼此都置身于非理性的喧囂和本能的狂歡之中[1]。文章以郭敬明的相關暢銷書作為研究對象,從粉絲文化、營銷工程、明星身份等角度入手來為資本權力視域下的郭敬明暢銷書密碼正名,從而為消費文化對當代文藝傳播的影響現象進行深度解讀。
一、受眾:粉絲文化
當今文學消費的受眾主力是粉絲,不光歌星、體育明星等文化偶像擁有廣大的市場,不少學者、作家也憑借文化產業的動力建立起自己的市場。單從銷量看,郭敬明的文學作品一直位居中國暢銷書的前列,郭敬明在2001、2002年連續兩年蟬聯“新概念作文大賽”冠軍,后來出版的長篇小說獲得7次內地圖書銷售的年度總冠軍[2]。1999—2015年期間的暢銷書排行中,郭敬明的著作幾乎年年上榜,位居前15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2010年包括《折紙時代》《虛銅時代》《刺金時代》的《小時代》系列三部曲長篇小說,僅僅2008年的第一部《折紙時代》,前三天就創造了“2008年度的全國第一銷量”的神話。依托暢銷書的腳本,2011—2015年,《小時代》三部曲被分拆,改編成《小時代1》《小時代2》《小時代3》《小時代4》電影四部曲,獲得18億的票房。不少文學調查顯示,郭敬明一直是眾多青少年粉絲喜歡的作家[3]-[8],其文本滲透力十分顯赫,從城市到農村,到處遍布粉絲。
在資本的刺激下,當下的粉絲促使郭敬明成為作家并進入市場邏輯的泥潭。粉絲必須不斷去制造一些與偶像相關的事物,以此拉近與偶像郭敬明之間的距離。雖然粉絲和偶像郭敬明之間的距離在不斷縮小,但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粉絲與郭敬明之間的距離不是一般的物體距離,而是階層差異所帶來的區隔。在實際生活中,郭敬明和粉絲屬于不同的階層,但在消費主義刺激下,兩者則會在大眾文化的背景下攜手長袖共舞。兩者鴻溝明顯,但是粉絲日常卻不會覺察到;不少粉絲沉湎于消費文化所帶來的快感,成為偶像經濟的買單人。
郭敬明的粉絲起源并非偶然,具有時代的合理性。
一方面,粉絲代表了一種消費民主的實現。在當前社會,物質生活極為豐富,某些消費領域不再被某些特權階層獨占,也逐漸向粉絲開放,粉絲的生活顯得豐富自由。消費主義給粉絲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表達空間,使粉絲獲得了較強的消費自由,這是消費民主的體現。粉絲的消費行為具有積極的意義,并不被資本意識操縱。粉絲的權力是粉絲個人自由意志的體現,粉絲作為個體,他們的消費權力是至高無上的。個體有權實現自身的需求與愿望,這種需求與愿望不該被外部的權威壓抑或剝奪。從資本自由市場角度來看,只有通過自由資本市場的競爭才能幫助粉絲獲取最大的利益。在資本市場的競爭中,生產者必須服從消費者,資本市場充當著一種外在權威,而不是一種社會合作方式。
另一方面,今日之娛樂不是傳統的“造星”,而是“造粉”。“粉絲”不僅簡單地去追隨偶像,還擁有很大的能量,并能在“造星”中發揮極強的作用。大眾媒體時代,名人偶像的形成或失去必須由受眾做出決定。雖然粉絲對明星很迷狂與執著,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處于后追星時代,粉絲的出現已經打破了傳統的造星格局。粉絲們不是“沙發上的土豆”,而是帶有較多思考和批判意識的群體,具有強大的互動性。在百度貼吧,粉絲可以給自己一個網絡據點,并且自立門戶,為喜愛的郭敬明歡呼雀躍或對不喜歡的明星嗤之以鼻。在貼吧部落,每個成員可以選擇不同的部落,在這些部落里粉絲不斷分享資訊,并評論與郭敬明有關的人和事。媒體的相關從業人員也要進入粉絲群體和粉絲進行互動,在粉絲的隊伍極其壯大時,大眾媒體的話語權也移交到粉絲那里。粉絲十分熱情地參與到傳播者行列,進行明星形象的塑造。
第三,在粉絲的認同國度,在當代城市冰冷建筑的背后,熙熙攘攘表象之下是人們內心的漂泊與孤寂。對于粉絲而言,“沒有選擇,就得沉默”,所以他們會去尋找一些其他的方式獲得精神的共鳴,用以填補內心情感的極度缺失,對郭敬明的崇拜成為他們不錯的選擇。粉絲在對郭敬明的認同過程中,為了證實自己審美取向,就去尋找興趣一致者,形成一定的粉絲團體,與彼此感興趣者一起分享對郭敬明的體驗,產生身份認同感。他們不是大眾中沉默的個人,而是圍繞郭敬明組成的群體,這是一種粉絲的亞文化邏輯。從這個角度可看出他們十分關注流行文化,具有文化創新的熱情,潛移默化推動文化產業的進步。英美相關的粉絲研究理論認為,粉絲受眾和普通的文化受眾比起來,他們會付出較多的精力、金錢與情感,以此創造更多的認同價值。“他們是不計成本的‘過度受眾’(excessive consumers),也是‘館藏式消費’(curatorial consumption)的積極實踐者(收羅一切與偶像有關的物品并收藏),因此他們是‘完美的受眾’(consummate consumers)。”[9]
二、書企:營銷工程
出版企業完全是市場化的,其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通過喚起受眾的閱讀欲望來實現消費市場的資本合理配置,完成積累并擴大剩余價值。在出版企業進行資本積累與擴張的過程中,資本運行邏輯的倫理性是不可避免的話題。
營銷工程的出現與整個出版市場業的規則緊密相關,正如作家兼書商路金波提到的:“錢鐘書說的,你吃了炒雞蛋,就別管是哪個母雞下的。但我覺得,在目前內容過剩的時候,受眾沒有辦法區別出來哪個最好,這個時候母雞是非常重要的。”[10]錢鐘書生活時代的出版業和現在的相比,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書作為商品供大于求已經成為眾所公認的現實。為了保持出版社的利潤,書商必定會全力打造明星作者和暢銷書。
2000年以來,傳統圖書出版業更受到了網絡娛樂的沖擊,中國國民的網絡閱讀率從2000年的3.7%上升為72.8%,15年增長了24倍。網絡閱讀具有多媒體互動性、開放性、廉價性等特點,受到較多受眾的青睞,不少傳統紙媒的忠實受眾也不斷離開紙媒的閱讀陣營,轉至網絡閱讀。
在這“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暢銷書必然成為文學市場發展的救命稻草。傳統出版是以產品為核心,而現今的出版必須要以受眾為中心,以營銷為根本,將“出書”轉為“售書”。作為暢銷書,離不開強大的營銷隊伍。如華藝出版社每年會選取有可能成為暢銷書的3~4本圖書作為營銷重點,進行相關的宣傳,如媒體記者的發布會、書評會或研討會等。在這方面,一些重點暢銷書的銷售量達到15萬冊以上,這些重點暢銷書會做3~4次的宣傳。如果預期銷量為2~3萬冊的,則只會進行1次宣傳。90%的圖書則因發行有限,沒有任何宣傳[11]141-142。在這樣的情況下,明星作家就會成為出版社的武器,出版社如果要出版圖書,首先考慮的是作者的名氣,如果是名氣較大的作者,如郭敬明,其圖書會迅速成為出版社重點關注和推廣的對象。針對這種情況,文化產業發達的美國也在使用這種策略,美國作為明星制度的起源國,也對作家進行了一系列的包裝。出版商選擇暢銷書,不僅要重視書籍的內容,還要追求作者的個人魅力。為了保持最大的利潤,出版商通過各種媒介議程促使作者成為媒體明星,開發出最大的閱讀市場。英國學者莫倫認為:“在將作者提升為‘名人’的過程中,圖書宣傳變得日益重要,這其實是文學生產被不斷整合到娛樂產業的一種癥狀。它讓作者和書籍都成了名人現象的文化普遍性的一部分,而名人正是壟斷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12]消費時代的文化產業則更多利用名人效應進行商品構建,郭敬明成為富豪和偶像也就成為特定的符號,其寫作風格、個人隱私、個人經歷往往被大眾媒體夸大或扭曲,轉變為特別的銷售符號。
郭敬明的圖書完全不依賴傳統圖書的評價體系與篩選機制,他們主要依靠市場與受眾。郭敬明雖然加入作協,表面進入到體制中,與其他作家一樣參與到體制文學中,但是由于他與一些主流作家有差異,所以從文學的責任度而言,他必定被邊緣化。雖然郭敬明才華橫溢,名聲較大,但是一些正統作家常常不屑于其作品與身份。值得注意的是,郭敬明為了能使作品更符合當下暢銷文學作品的資本規則,作品也經常包含懷舊情調、姐妹(兄弟)情深、三角戀情、勞燕分飛,并穿插噱頭。
三、作家:明星身份
消費主義時代,一切均可成為商品,明星制度也不例外。明星是整個文學生產環節的核心元素,明星作家與普通作家相比具有更大的市場話語權力。明星作家的消費,是在作家功能、作家個人發展、文化產業市場導向的緊密結合下所產生的正常資本權力形態。在這種市場邏輯下,明星消費文化形態成為傳媒發展中必須遵守的重要法則。明星能產生較強的吸引力,促進文化產品的銷售并提升廣告的效益。郭敬明是大眾傳媒時代的寵兒,在大眾傳媒的強大造星機制下,作家郭敬明為現代人所追捧。對于媒體而言,他們根據郭敬明的實際情況去制作出相關的明星新聞,以此提高閱讀率、收視率與點擊率。
從作家功能看,作家明星化是正常文學現象,能鞏固出版業活力并促進其發展。賀紹俊認為,在當代大眾文化的影響下,整個文學生產具備較強的明星化趨勢,“明星是文化消費的焦點,也是文化經濟增值的支點”。江冰認為,“由于青少年受眾在青春期的‘偶像崇拜’心理,作家的偶像化正好是通往目標受眾的有效途徑”[13]。不少書商為了保持利潤的持續性,他們會從已經成名的作家當中尋找合適的對象進行包裝,在這方面,郭敬明無疑是書商們熱捧的對象。從文學輿論方面考察,郭敬明是當代年輕作家中最富有爭議性的作家。消費文化本身帶有很強的后工業時代色彩,與消費文化直接聯系的文化產業手段有策劃、推銷、包裝、炒作等。英國學者赫斯蒙德夫(David Hesmondhalgh)認為,文化產業是高風險產業,又具備較低被復制的可能,作為文化產業,使用明星規避市場風險,是十分優良的手段[14]11-12,17-21。當代文學創作市場競爭過于激烈,如果書商不進行媒介議程設置打造明星以保持作家的活力,則無法給予作家一定的活力。
從作家個人發展看,一些年輕作家如果想在消費時代快速走向中心,就需要被明星化,這也是樹立作家的社會地位的重要方法。今天的作家在寫作時,無論自身是否意識到,他必定無法擺脫資本權力問題的纏繞。書籍暢銷是所有作家的夢想,在消費文化之下,文學不是作家孤立創作的文本,必須與出版整體大環境、社會審美期待、受眾的消費心理完全結合,才能產生較大的社會影響[15]。面對受眾群分化、受眾的主流閱讀主要是娛樂消遣的現狀,作家會考慮市場,適應整體受眾的需求。1990年代以后的受眾以消遣閱讀為主,基本愛好趨向娛樂化、平面化,多種娛樂消費成為他們精神消費的主要方式。受眾喜歡帶有流行與娛樂的文學作品。如果作家有意識迎合受眾,則會獲得銷量的成功,否則就會失去市場青睞。如果完全走過于嚴肅文學道路,只會令自身的創作空間越來越狹窄。作為文學作品,雖然完全符合消費的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郭敬明本身具備明星包裝的條件(英俊的外表、不凡的表達能力、與眾不同的個性、超出常人的商業頭腦等),他就具備了成為明星作家的條件,他也找到了適合自身的、處于經典文學之外的成名方式。對于作家而言,他在乎的是資本市場能否實現自身作品的暢銷,能否成就他自身的經濟地位。郭敬明雖然進入正統作家行列,甚至進入公務員序列①,但他本人也非常清楚,他只是表面被正統體制收編,實際上完全不屬于體制,在混沌復雜的資本權力中,在迎合受眾的同時保持自身的個性與鋒芒,依靠性格和才華去博得財富。
從文化產業的市場導向看,在當前的消費時代下,郭敬明的明星角色是無法自主自立的,當前的文化產業屬于買方市場,并不是賣方市場。“娛樂業實現工業化經營之后所需要的快速成名模式,極大地增加了娛樂勞動者對媒體的依賴性。即使娛樂勞動者成為明星之后,也同樣無法減輕對媒體的依賴度。原因在于,流水線上的娛樂勞動者生產模式導致娛樂勞動者,甚至包括明星,存在嚴重的供應過剩且產品高度同質的現象,這就好像當今中國若干一般性商品行業生產嚴重過剩且產品雷同一樣。”[16]對于明星,如果沒有持續性的關注,其后接的替補是比較多的。無論是郭敬明,還是別的80作家,亦或歌星、影星,他們如果不遵循市場規律,或者違背流水線的明星生產模式,其結果往往是消失在那些樂意服從文化產業明星生產規律的人群中。
在資本權力背景下,郭敬明書籍的暢銷是由多個元素推動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郭敬明審時度勢,迎合了市場受眾的需求。郭敬明書籍的暢銷現象給當下的文學市場一些啟示:一方面,在資本權力背景下,文學評論家需要對新的受眾群體的知識構架與價值觀進行評價,不能以傳統的文學批評標準評判新生事物。郭敬明的暢銷書畢竟代表了當下80后與90后的心聲,他的成功與其適應資本權力市場緊密相關,具備一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注意防止郭敬明等作家過于諂媚資本市場而造成的負面影響。文學的創作離不開淵博的知識與豐富的想象力,在郭敬明等暢銷書作家之外,還有一些創作態度嚴肅的作家,他們的作品或可具有較長的藝術生命力。
[1] 蔣承勇.感性與理性 娛樂與良知——文學“能量”說[J].文學評論,2014(3):15-18.
[2] 仇宇浩.專訪郭敬明:我紅了十年我還在上升[EB/OL].(2013-10-04)[2017-06-15].http://www.hdzc.net/html/news/handan/handannews/2013_10/04/21841106.html.
[3] 白燁.一份調査問卷引發的思考[J].南方文壇,2005(6):75-78.
[4] 王先霈.新世紀以來文學創作若干情況的調査報告[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6.
[5] 楊玲,劉曉鑫,陳書毅.解構神話:受眾視角中的網絡文學項關于網絡文學觀念與閱讀的實證研究[J].濟寧學院學報,2008(5):11-15.
[6] 水丹丹,吳珊環,宋思森,等.廣外閱讀現狀調査:一代有一代的文學[EB/OL].(2009-04-07)[2017-06-15].http://campus.gdufa.edu.cn/html/gwzone/focus/iniview/20090407/7552720.html.
[7] 王金勝.當前青少年學生文學閱讀調查研究——以山東省青島市為例[J].上海商學院學報,2010(6):75-80.
[8] 徐佳.郭敬明成都宣傳《小時代4》系列票房18億遠超預期[EB/OL].(2015-07-20)[2017-06-15].http://scnews.newssc.org/system/20150720/000583493.html
[9] 楊玲.超女粉絲與當代大眾文化消費[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09.
[10] 劉恒濤.路金波:把作家做成品牌[N].財經時報,2007-07-02.
[11] 向勇.北大文化產業前沿報告[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4.
[12] Joe Moran. The Reign of Hype, in P. David Marshall ed., The Celebrity Culture Reader[M]. New York : Routledge, 2006.
[13] 江冰.論80后文學的“偶像化”寫作[J].文藝評論,2005(2):13-17.
[14] David Hesmondhalgh. The Culture Industries[M]. London: Sage , 2002.
[15] 徐秉鵬.論當代批判性思維的早期形式:宣傳分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6,30(10):22-31.
[16] 秋風.娛樂業工業化之過[N].南都周刊,2006-05-19.
(責任編輯:張新玲)
①2009年,郭敬明受邀出任長江出版集團北京圖書中心副總編輯,負責主抓青春文學項目開發,享受副社長級待遇,成為國內青年作家26歲就任副處級干部的第一人。
The Readers, the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and the Writer in the Context of Guo Jingming’s Best Sellers
YANG Shu
Theoristsholds that there are some shortages of thebest sellers, such as Guo Jingming’s, showed in the process of artistic consuming. As a matter of fact, consuming democratic culture, fans-making project, and the lack of mental spirits are all th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receivers’ fans culture. Fierce fields competition and on-line entertainment competition are the reason for book marketing of the publishing corporations. Meanwhile, the writer’s functio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e industry in the consuming market further confirm the idol identity of a writer. Influenced by receivers’ fans culture, book marketing, and idolized identity, these best sellers have to adapt to the capital power.
capital power; best seller; fans culture; marketing project; idolized identity
G235
A
1009-8135(2017)05-0033-05
2017-06-20
楊 曙(1984—),男,江蘇海門人,常州工學院副教授,文藝學博士,主要研究文藝傳播學。
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虛擬存在的美學研究”(14YJA751028),2014年度常州工學院校級科研基金項目“消費文化與當代文藝話語傳播”(YN143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