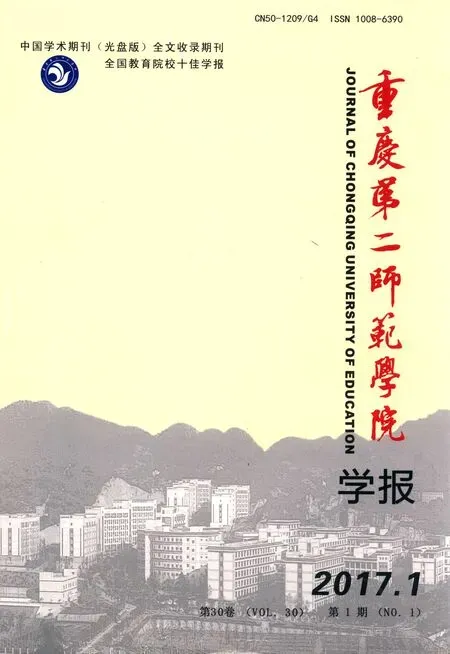論盧見曾與袁枚的交誼與交惡
袁 鱗
(山東師范大學(xué) 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濟(jì)南 250014)
論盧見曾與袁枚的交誼與交惡
袁 鱗
(山東師范大學(xué) 山東省齊魯文化研究院,濟(jì)南 250014)
作為乾隆時期東南詩壇的主持者,盧見曾與袁枚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盧、袁兩人的交往經(jīng)歷了一個由相互仰慕到矛盾激化的過程,其原因在于兩人價值觀念、師法策略和對詩歌功用的看法存在較大不同。盧見曾與袁枚的分歧可以看作詩歌創(chuàng)作領(lǐng)域中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的一次交鋒。
盧見曾;袁枚;價值觀念;學(xué)詩方法
清代乾隆時期的詩壇極為活躍,名家輩出,作為其中重要代表的盧見曾、袁枚均曾主持東南文壇,對當(dāng)時的詩歌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前者效法漁洋,提攜后進(jìn),組織文人修禊,以雅化俗,整肅時風(fēng);后者則成為“廣大教主”,在考據(jù)大盛之時,獨倡性靈,自立一派。盧、袁同處江南大環(huán)境中,早年相互仰慕,后卻因種種矛盾而分道揚(yáng)鑣。長期以來,關(guān)于盧、袁交往情況的研究尚不多見。本文通過對盧見曾與袁枚的交往及其矛盾的梳理,對二人的關(guān)系變化以及清乾隆時期詩壇的豐富性加以考察。
一、以詩相知,神交已久
盧見曾作為清代重要的文化名人,以《經(jīng)義考》《雅雨堂叢書》《周易述》等書籍的刊刻而廣為人知,但其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同樣有著不俗的造詣。盧見曾三十二歲中進(jìn)士,其與馬維翰合作的《柏梁體聯(lián)句壽座主臨川先生》一詩在京師引起較大轟動[1]541。乾隆元年,盧見曾任兩淮鹽運(yùn)使,隨即被誣與高鳳翰結(jié)黨,并于四年后遣戍邊塞,乾隆九年蒙恩賜還。盧見曾將其出塞期間的詩作編為《出塞集》,于乾隆十一年刻板成書,廣為流布。據(jù)《隨園詩話》記載,袁枚不僅很快讀到《出塞集》,而且對其大加贊賞:
盧雅雨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譎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肯者再:喜師弟之印可也。[2]68
那么,盧見曾所作《生祭蔣蘿村》到底是一首怎樣的詩呢?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目的主要是為寬慰同戍之友蔣蘿村。蔣因年老體弱,恐怕此生不能遣返,故而盧見曾作此詩以解其愁。該詩為四言短句,想象生動,用語詼諧,可以看出盧見曾以苦為樂的曠達(dá)之情。由于全詩較長,現(xiàn)截取部分,錄之如下:
我聞閻羅,即包孝肅。其家廬州,仆曾為牧。牧不負(fù)神,神應(yīng)電矚。為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冥司,分隸城隍。我輩頭銜,頗與相當(dāng)。定容抗禮,謙尊而光。豈如井底,妄肆蛙張。我聞此地,李陵所竄。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河梁,妙絕詞翰。地下相逢,定非冰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冢表表,血食為神。乃心漢闕,同鄉(xiāng)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幻想,謂死有覺。有覺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3]118
這首詩以出人意料的構(gòu)思和人性化的表達(dá),打破了祭文這一題材在風(fēng)格選擇上的限制。在讀者與典故的互動中增添了喜劇效果,令人忍俊不禁,一時傳為名篇。以學(xué)入詩而又能將其化為藝術(shù)性的審美享受,這與袁枚倡導(dǎo)的“性靈說”有著天然的契合。袁枚的“性靈說”不僅主張詩歌要強(qiáng)調(diào)個性的表達(dá),還要具備一定的才情與智慧,善于變陳為新,出奇制勝。盧見曾的這首詩想象新奇,兼?zhèn)洳抛R,不落凡套,想必此時,“首肯者再”的袁枚就已引年長自己二十六歲的盧見曾為同調(diào)了。
袁枚對于仕宦并不熱衷,故而早早辭官買園,安享其樂,營造“山環(huán)水抱,樓閣參差,處處有圖畫之妙”的隨園;游歷山水,“盡其才以為文辭詩歌,足跡造東南山水佳處”;喜愛美食,留下膾炙人口的《隨園食單》。盧見曾雖然宦海沉浮三十年,位居兩淮鹽運(yùn)使,但官僚氣薄而名士氣重,這就構(gòu)成了二人早年交好的基礎(chǔ)。盧見曾同樣善于享受生活,如其對酒的喜愛達(dá)到了癡迷的程度,即便流放塞外,依舊嗜酒如命。由于塞外得酒不易,盧見曾不惜“窮廬無酒,遠(yuǎn)購乃得”,滿足酒癮。[1]665盧見曾亦頗愛菊,單從《官署遷移到處必自藝菊……以新詩口占奉答》[3]21一詩的題目中,我們就可以感受到盧見曾“不可一日無此君”的魏晉風(fēng)度。綜上,不能不說袁、盧二人在生活態(tài)度和品味上具有一致之處。
如果說《生祭蔣蘿村》一詩,使得袁枚對盧見曾詼諧不羈的個性有了初步了解和認(rèn)可,那么盧見曾赴任兩淮鹽運(yùn)使后,對袁枚的關(guān)切則使得二者的關(guān)系愈加緊密。袁枚對于盧見曾的仰慕之情集中體現(xiàn)在其《呈雅雨公詩冊》中:
抱孫先生再領(lǐng)兩淮鹽運(yùn)之任,枚江左末吏,靡由識荊。門人王梅坡來自揚(yáng)州,道先生問枚甚悉,并頌其壁間題句。枚竊喜自負(fù),恭賦五言四章,渡江求教,知己之感,情見乎詞。[4]243
此時的盧見曾再任兩淮鹽運(yùn)使,負(fù)責(zé)江蘇、安徽、湖北、江西等省鹽務(wù)。鹽務(wù)涉及國家命脈,可謂位高權(quán)重。作為詩壇前輩、政壇高官的盧見曾屈尊下士,“問枚甚悉”,這在講求官階等級的封建社會里,尤為可貴。況且這樣一位詩壇前輩的關(guān)心,對文采自許的“江左末吏”袁枚無疑是一種鼓勵。袁枚在其贈詩中既表達(dá)了對盧見曾“愿公為劉晏,理財先養(yǎng)民”的政治期許,也有對其“公再登騷壇,高秋立雕鶚”的文壇地位的肯定,更有“豈不畏路長,相知感君子”的知己之感。此后二者還有書信往來,如袁枚作于乾隆二十二年的《奉和揚(yáng)州盧雅雨觀察紅橋修禊之作》第三首,將盧見曾與歐陽修、蘇軾、何遜等人并提,肯定其扶輪風(fēng)雅之舉:“歐蘇當(dāng)日擅風(fēng)流,重整騷壇五音秋……莫怪梅花東閣盛,年來何遜領(lǐng)揚(yáng)州”。另外,現(xiàn)存袁枚作于乾隆二十三年的《揚(yáng)州轉(zhuǎn)運(yùn)盧雅雨先生招游紅橋集三賢祠賦詩》、乾隆二十五年的《寄盧雅雨觀察》一文,也見證了盧、袁二人的交誼。可以說,盧、袁二人在這幾年之間交往頻繁,關(guān)系融洽。然而不久,二人的這種友誼因在薦士問題上的紛爭而出現(xiàn)裂痕。
二、薦士風(fēng)波,矛盾公開
清代科舉考試較為嚴(yán)苛,一大批知識分子入仕無望,轉(zhuǎn)而入幕為僚。作為東南大吏的盧見曾,一方面有著較為開明的頭腦,禮賢下士,主動結(jié)交學(xué)者文人,提供優(yōu)厚的讀書和生活條件;另一方面,盧見曾本人具有較高的經(jīng)學(xué)、文學(xué)造詣,因而對他們的精神世界更加了解和包容,諸如惠棟、沈大成、王昶、吳敬梓、鄭板橋、金農(nóng)、金兆燕等文人先后入幕為僚。盧見曾既不乏愛才好士之心,又具有優(yōu)厚的物質(zhì)基礎(chǔ),因而親朋故舊也多為引薦。而關(guān)于袁枚薦士的文獻(xiàn),見于兩封書信。一封是《寄盧雅雨觀察》,其云:
先生借省會之余閑,訪野人于物外,一林梅萼,半榻茶煙,想別后猶殷然在念也……陳生古愚,因受知于先生,而有其室家。因有室家,而轉(zhuǎn)增食口。良醫(yī)治人,原不能十全為上也。然恩始恩終,大君子必?zé)o厭色……茲來晉謁,祈進(jìn)之前席,而洗其寒酸,幸甚。[5]37
另一封為《與盧轉(zhuǎn)運(yùn)書》,其云:
月之十七日陳生歸又三日,公手書至,道生操觚率爾不克受公恩,并戒枚毋再薦士……陳生士之未成者也,其所以位置之者當(dāng)自有道矣……明公居轉(zhuǎn)運(yùn)之名,要在轉(zhuǎn)其所當(dāng)轉(zhuǎn)而不病商;運(yùn)其所當(dāng)運(yùn),而不病天下。不必頭會箕歛知有商而已也,亦不必置喜怒于其間,以會計之余權(quán)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枚嘗過王侯之門不見有士,過制府中丞之門不見有士,偶過公門士喁喁然以萬數(shù)。豈王侯制府中丞之愛士皆不如公耶?抑士之暱公、敬公、師公、仰望公果勝于王侯、制府、中丞耶?靜言思之未嘗不嘆士之窮,而財之能聚人為可悲也……然則使公或晉擢他去,誠恐詩之十倍陳生者,亦未必一至門下。而何有于生?生遇公,公遇生,誠兩不可再,而卒齟齬以窮媒勞恩絕何耶……如生者徑之至狹者也,惟公能收之而惜其不寬也。生休矣,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bǔ)公過。枚謹(jǐn)覆。[6]1508
據(jù)《袁枚年譜新編》可知,陳古漁結(jié)婚時間在乾隆二十三年冬[4]289,《寄盧雅雨觀察》的寫作時間當(dāng)在乾隆二十三年陳古漁結(jié)婚之后。而《與盧運(yùn)使書》中所提到的“陳生”是否為陳古漁,由于盧見曾的回信現(xiàn)已不存,還缺乏直接的證據(jù)。但我們不妨從袁枚寫給盧見曾的兩封書信入手,探討兩人關(guān)系的轉(zhuǎn)變。
如前所述,盧見曾效法王漁洋,多次舉辦雅集,招攬文人學(xué)者,成為東南文壇的領(lǐng)袖人物。在盧見曾聲望如日中天之時,袁枚則指出盧見曾獲得如此聲譽(yù)并不是因為自身的過人之處,不過是手握權(quán)財而已,一旦盧見曾失去現(xiàn)有官位和財勢,是難以有所作為的。袁枚指出盧見曾能匯聚群賢的基礎(chǔ)在于“財之能聚人”,一方面,匯聚在盧見曾周圍的文人乃是為財而去的勢利之徒;另一方面,盧見曾的一己之德還不足以令真士“一至門下”。袁枚進(jìn)而批評盧見曾以個人的喜怒決定幕僚榮辱:“不必置喜怒于其間,以會計之余,權(quán)取天下士而榮辱之也。”總之,在袁枚看來,盧見曾既無辨別真士之能,又非真心愛士之人。袁枚的這封信毫不留情,措辭嚴(yán)厲,絕無當(dāng)年“竊喜自負(fù),恭賦五言四章,渡江求教。知己之感,情見乎詞”的恭敬與謙卑。書信的最后還不甘示弱,表露自己“恐生之外尚有其人,枚將終薦之以補(bǔ)公過”的嚴(yán)正態(tài)度。
袁枚《與盧轉(zhuǎn)運(yùn)書》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主要出于對盧見曾以財聚人的行為以及由此導(dǎo)致的文壇諂媚之風(fēng)表示不滿。關(guān)于盧見曾愛好風(fēng)雅是否帶來負(fù)面影響,這里我們暫不討論。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袁枚僅僅因薦士“陳生”被拒而措辭嚴(yán)厲,針鋒相對,特別是考慮到袁、盧二人身份地位的差異,這種態(tài)度轉(zhuǎn)變以及直言的勇氣更令人匪夷所思。況且陳生自身存在著“操觚率爾”的問題,盧見曾拒不接納陳生也合乎情理。此外,袁枚曾向恩師兼密友的尹繼善推薦自己的好友陳古漁,但尹繼善因陳古漁其貌不揚(yáng),性情古怪,因而并不接納,“(尹文端)蓋見其骨鼻污膺之狀,貌昌披了鳥之冠巾,扈載清寒,宰相似難造命”[7]183,袁枚和尹繼善并未因此而公開辯難,做出激烈反應(yīng)。由此可見,陳生被黜與袁枚對盧見曾的指責(zé)論辯,并不構(gòu)成必然的關(guān)系。此外,聯(lián)系到二者的身份差異,僅僅因為友人入幕被拒而不惜與三品大員盧見曾決裂,這也與袁枚避實就虛的一貫作風(fēng)不符。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qū)е隆把庞瓯勺硬牛首硬乓嗪拗盵8]853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呢?
三、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的交鋒
陳生被黜事件使得盧、袁二人的矛盾公開。其背后所反映出來的分歧,絕非薦人被拒那么簡單。況且二人一為民,一為官,談不上政治利益上的瓜葛。通過對兩人為人處事、詩壇地位和詩學(xué)傾向等方面的比較分析,我們大致推斷二人反目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價值觀念的對立
盧見曾與袁枚雖同為科舉考試的優(yōu)勝者,但二人有著不同的家世出身和為官經(jīng)歷,形成了不同的價值觀念。盧見曾一生秉持的是崇儒重經(jīng),為政以德的處世態(tài)度,與其奉儒守官的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其曾祖盧宗哲為官剛正不阿,權(quán)相嚴(yán)嵩欲籠絡(luò)之,遭到其嚴(yán)詞拒絕。而其父盧道悅敏于職守,為官清廉,頗有政聲。盧見曾在為官的三十余年間,歷任縣令、知州、轉(zhuǎn)運(yùn)使,在其任上興辦學(xué)舍、興修水利、整頓鹽務(wù)等,堪稱循吏。而盧見曾對于思想文化的巨大投入尤其值得矚目。據(jù)記載,盧見曾任縣令時不僅捐俸資助書院而且親臨講授,與當(dāng)?shù)匚娜藢W(xué)士打成一片:“邑初無書院,先生捐俸設(shè)書院于茲……征邑士之秀而文者,日與講迪敷弦歌。”[9]418張柱的《邑侯庚亭颶賢治洪善政紀(jì)略》一文給予盧見曾以高度評價:“時川南文學(xué)實至先生開之。”[9]414事實證明,盧見曾對學(xué)子的教育事業(yè)極為關(guān)注且成效顯著。
乾隆十八年,盧見曾到任“媚行者成市”的揚(yáng)州。為扭轉(zhuǎn)頹廢的世風(fēng),盧見曾先后舉辦千人參加的文人雅集活動,而其所主持的詩文雅會并非萬眾狂歡,紙醉金迷,花天酒地。從其“凡紅橋之會,凡業(yè)鹽者皆不得與”[10]213的嚴(yán)格規(guī)定,可以看出其嚴(yán)格的選拔標(biāo)準(zhǔn)和鮮明的文化立場。盧見曾希冀改變由揚(yáng)州鹽商所引領(lǐng)的尚利享樂的不良風(fēng)氣,以重塑士人的人格精神。沈德潛的這首《和盧雅雨運(yùn)使紅橋修褉詩》已經(jīng)表露出對其轉(zhuǎn)移風(fēng)氣的肯定:“壺觴不用紅裙侍,賡唱齊將白雪酬。”盧見曾借此引領(lǐng)了雅文化的浪潮,確實對當(dāng)時的世風(fēng)產(chǎn)生了影響,留下了無形的文化資產(chǎn)。這一點從后人的評價中可以得到印證:“揚(yáng)州自雅雨以后數(shù)十年來,金銀氣多,風(fēng)雅道廢。”[11]150盧見曾之于揚(yáng)州的意義正在于此。
袁枚出身微賤,“只緣少也賤,歷嘗考試艱”,雖然考中進(jìn)士后,也曾“頗思有所樹立”,外任知縣也一度勤于政事,還將做縣官的經(jīng)驗寫成《州縣心書》,以資他人借鑒。然而貧寒的家世出身,使得袁枚“追求功名,更主要的目的是為了擺脫貧窮卑賤,獲得更多的人生享受”[12]57。縣令瑣碎繁忙的工作使得袁枚過早生發(fā)出對于官場的厭惡,而江浙富庶的經(jīng)濟(jì)條件,優(yōu)厚的文化生態(tài),又助長了其離開官場的欲望。袁枚于乾隆十四年辭官,居家隨園,擺脫了官場的束縛轉(zhuǎn)而看重個體價值的極大彰顯。不可否認(rèn),袁枚仕途偃蹇,缺乏建功立業(yè)的機(jī)會,但主要原因是袁枚年少家貧,又生長于富庶的江浙地區(qū),成名較早而又格外注重自我的物質(zhì)需求與精神體驗。這樣的傾向在袁枚營造隨園之時就早有顯露:“使吾官此,則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則日日至焉。兩者不可得兼,舍官而取園者也。”[6]1406袁枚較早脫離官場,憑借其過人的交際能力,與江南官員、鹽商保持著良好的關(guān)系,但也沾染了不少奢華習(xí)氣。據(jù)袁枚之弟袁樹記載:“兄于上元日(乾隆二十六年)招宮保諸公子宴隨園,長廊高榭懸燈四百余盞,遠(yuǎn)近士女喧鬧,人影衣香徹夜不散。”[4]305袁枚這種追逐享樂的習(xí)氣在以富庶著稱的江浙頗為流行,但與盧見曾整治時風(fēng),以雅化俗的初衷相比,顯得格格不入,故而不同的價值觀念可能是導(dǎo)致二人沖突的重要原因。
(二)詩學(xué)主張的差異
作為東南極富號召力的文化巨頭,盧、袁二人有著不同的詩學(xué)主張。袁枚在乾隆樸學(xué)盛行之際,鼓吹“性靈”,引領(lǐng)了別樣的時代潮流,特別是以打破固有的思維方式,消解傳統(tǒng)和經(jīng)典的絕對價值,顯示出典型的求我、求新的特點,受到社會的廣泛歡迎。袁枚教導(dǎo)后學(xué),有著自己明確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從古風(fēng)人各性情,不須一例拜先生”[6]692,“以出新意、去陳言為第一著”[2]185。但袁枚有時強(qiáng)分真?zhèn)危呛诩窗祝谴思幢耍缭趯τ趹?yīng)酬詩的看法上,盧、袁二人就體現(xiàn)出不同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據(jù)《隨園詩話》記載:“予在轉(zhuǎn)運(yùn)盧雅雨席上,見有上詩者,盧不喜。余為解曰:‘此應(yīng)酬詩,故不能佳。’盧曰:‘君誤矣。古大家韓、杜、歐、蘇集中強(qiáng)半應(yīng)酬詩也,誰謂應(yīng)酬詩不能工。’”袁枚在最后也表示“余深然其說”,但其“自成一隊”的詩學(xué)追求使得袁枚在面對傳統(tǒng)的質(zhì)疑、論難所帶來的強(qiáng)大壓力面前,有時難免會走向?qū)α⒚妫识m勝人以口,但不能服眾于心。
與之相對,學(xué)有根柢,講究師承是盧見曾詩學(xué)評價體系的核心,并以此作為判斷詩歌優(yōu)劣的重要標(biāo)準(zhǔn)。盧見曾在其編選的《國朝山左詩鈔》小傳中多次提到:
(何世璂)余以辛丑登第,留京教習(xí)。每與先生談詩輒進(jìn)一解,以其受業(yè)于漁洋最久,衣缽有自故也。[1]648
(魏丕承)藿村生有夙慧,穎悟出群,六歲受《孝經(jīng)》即能成誦,十九歲與田香城先生同受知于學(xué)使者宮孟仁拔入太學(xué)。受業(yè)田山姜、孫峨山,兩公詩文皆有根柢,故能啟迪后進(jìn)多所成就。[1]650
(牛運(yùn)震)獨稱詩與余不同,然持論具有根柢。[1]792
那么“根柢”究竟為何物?優(yōu)秀詩歌作品并非憑空而來,離不開對前代優(yōu)秀詩歌的學(xué)習(xí)借鑒,清代詩歌的發(fā)展更是如此。關(guān)于“根柢”的實質(zhì),盧見曾同鄉(xiāng)先賢王士禛曾云:“本之風(fēng)、雅以導(dǎo)其源,溯之楚騷、漢魏樂府以達(dá)其流,博之九經(jīng)、三史、諸子以窮其變,此根柢也。”[13]749在盧見曾看來,學(xué)有根柢是作詩、論詩的前提條件:一方面,學(xué)有根柢重在“根柢”,這就避免墮入晚明楚習(xí),廢書不觀,隨波逐流;另一方面重在“學(xué)”,意在融會百家,防止形成強(qiáng)分唐、宋這樣狹隘的文學(xué)觀念。盧見曾作為士子教育的參與者,其目的在于指導(dǎo)后學(xué),而并非強(qiáng)調(diào)表達(dá)個性,標(biāo)新立異。他在評點《杜子美詩集》時大量抄錄前人的注文,具有極強(qiáng)的溯源意識。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條:“此與《北征》為集中鉅篇,郁結(jié)寫胸臆,蒼蒼莽莽,一氣流轉(zhuǎn)。其大段有千里一曲直勢,而筆筆頓挫,一曲中又有無數(shù)波折也。”[14]20又如其評《大云寺贊公房四首》條:“聲調(diào)穩(wěn)愜,雅近選體。”[15]9再如其評《示從孫濟(jì)》條:“多似古樂府,溫柔敦厚,比興深切。”[14]14評《彭衙行》條:“通篇追敘……神思漢魏。”[15]4可以看出,盧見曾本著“取法乎上”的原則,樹立可供參考的學(xué)習(xí)對象,有著切實可行的學(xué)詩軌跡,確實與袁枚以抒寫性靈、求我求新的路徑有所不同。
(三)詩歌功用上的分歧
從歷史上看,關(guān)于詩歌功用問題的討論,其分歧大抵不出“言志”和“緣情”兩派,但具體來看又受到不同時代精神的影響。清朝出于鞏固統(tǒng)治的目的,高度重視思想意識的控制。而基于對晚明以異端自居,時風(fēng)日下的反思,清代的知識分子也自覺地向儒家傳統(tǒng)精神回歸。與此同時,隨著江南商品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商業(yè)資本有意識地介入到文人生活中來,經(jīng)濟(jì)的獨立使得思想領(lǐng)域也孕育出了追求自我、尊重個體價值的風(fēng)氣。作為這一時代產(chǎn)物的袁枚,將儒家經(jīng)典文本重新詮釋,以此來解放人們的思想。如對“詩言志”這一傳統(tǒng)母題,他解釋為:“詩人有終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詩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興到、流連光景、即事成詩之志。‘志’字不可看殺也。”[16]6袁枚既消解了對于“志”的道德束縛,又從根本上使得攻擊者喪失持論之本。除了對于經(jīng)典的重新詮釋,袁枚還發(fā)前人之未發(fā),如對前人往往回避的風(fēng)情詩有所提倡。《隨園詩話》記載:“黃陶菴先生性嚴(yán)重,館牧齋家,不肯和柳夫人詩。然其詩,極有風(fēng)情。《竹枝歌》云:‘東湖西湖蓮菂開,一日搖船采一回。蓮葉田田無限好,只因曾見美人來。’‘柳條不系玉蹄腡,拗作長鞭去路斜。春色也隨郎馬去,妝樓飛盡別時花。’[2]268萊陽姜垓云:‘十年前遇傾城色,猶是云英未嫁身。今日相逢重問姓,尊前愁殺白頭人。’……按萊陽兩姜先生,以孤忠直節(jié),名震海內(nèi),而詩之風(fēng)情如此。聞憶娘與先生本舊相識,一別十年尊前問姓,故詩中不覺情深一往去。”[2]208袁枚認(rèn)為詩中描寫男女風(fēng)情是自然需要,與人的道德高低并無必然關(guān)系,這就打破了傳統(tǒng)的以詩論人、以人論詩的審美理想,顯示出新的時代要求。
如果說袁枚更多體現(xiàn)了對業(yè)已形成傳統(tǒng)的解構(gòu),表示了對世俗情懷的關(guān)注,那么盧見曾則具有濃厚的復(fù)古氣質(zhì)。首先,盧見曾所在的山東地區(qū)有著厚重的復(fù)古文學(xué)傳統(tǒng)。以邊貢、李攀龍、謝榛為代表的桑梓先賢,對于地方文化的傳承發(fā)揮著重要而持續(xù)的作用。即便在晚明公安、竟陵盛行之時,公鼐、于慎行等人仍然高揚(yáng)齊風(fēng),捍衛(wèi)地域文化傳統(tǒng),復(fù)古風(fēng)氣不可謂不濃。其次,復(fù)古派的詩歌主張一開始就具有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針對性:“前七子掀起以復(fù)古為革新的文學(xué)熱潮,是他們在劉瑾專權(quán)、武宗荒淫等特定背景下將王朝中興希望的轉(zhuǎn)移,寄托著他們以文學(xué)托諷補(bǔ)世的苦心孤詣。”[17]183盧見曾年幼時隨父赴任偃師,后又先后擔(dān)任知縣、知州,還曾遣戍邊塞,對于百姓生活以及現(xiàn)實的弊端有著深切的體察。盧見曾繼承了前后七子實用主義的詩學(xué)主張,依舊秉持著儒家主張言必有據(jù),言必有用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旨,并一再表示詩歌創(chuàng)作必須有感而發(fā),有為而作:“詞旨了然,而醖釀道麗。無蕪音累句,其可與采風(fēng)者之選矣。”[18]62在這一原則下,盧見曾反對“徒飾形貌,無關(guān)性情”[18]47的作品,這一點在其編選的《國朝山左詩鈔》中大量反映個人遭際和民生疾苦的詩作中有著突出的體現(xiàn)。因此,盧見曾與袁枚二人對于詩歌功用有著各自明確的看法,同時作為東南文壇的主持人,不可調(diào)和的詩學(xué)矛盾無疑會對二人的關(guān)系產(chǎn)生一定影響。
四、結(jié)語
盧見曾于乾隆二十七年告休回鄉(xiāng),后因兩淮鹽引案事發(fā)而押解至揚(yáng)州監(jiān)獄,乾隆三十三年九月病卒獄中,時年七十九歲。在盧見曾死后的第六天,袁枚寫下了《十月四日揚(yáng)州吳魯齋明府招同王夢樓侍講蔣春農(nóng)舍人金棕亭進(jìn)士游平山即席有作》一詩,其云:“手握牢盆能養(yǎng)士,算清禺便刊書。海內(nèi)詩人半貧者,一時麕至推風(fēng)雅。爭學(xué)彭宣拜后堂,甘為夫差作前馬……潘岳閑居竟不終,褚淵高壽真非福。一夕清霜萬瓦飄,巢傾卵覆不終朝。窟營轉(zhuǎn)覺馮諼拙,金散方知疏廣高。今朝酒客還盈座,曾受恩人有幾個。晁錯方聞東市行,羊曇偏向西州過。”[6]499這首詩可以看作袁枚對于盧見曾一生的最終評價,不僅肯定其在愛才好士方面的功績,而且對亡友的被誣離世表示了應(yīng)有的尊重和哀悼。作為那個時代最為杰出的詩論家,袁枚與盧見曾可謂與詩相始終,既有過惺惺相惜的期許,也有針鋒相對的論辯。總之,盧見曾與袁枚的交往作為清代詩人交往的一個縮影,展現(xiàn)了那個時代多元并存的詩學(xué)主張,為我們再次審視清代詩學(xué)的復(fù)雜性提供了重要參考。
[承蒙山東大學(xué)杜澤遜先生借閱盧見曾批《杜子美詩集》(《芷蘭齋藏稿鈔校本叢刊》),特此致謝!]
[1]盧見曾.國朝山左詩鈔[M]//山東文獻(xiàn)集成第一輯:第41冊.濟(jì)南:山東大學(xué)出版社,2006.
[2]袁枚.隨園詩話[M].顧學(xué)頡,校點.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12.
[3]盧見曾.出塞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4]鄭幸.袁枚年譜新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5]袁枚.小倉山房尺牘[M].范寅錚,校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7.
[6]袁枚.小倉山房文集[M].周本淳,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7]陳毅.詩概[M]//四庫未收書叢刊影印乾隆二十五年眠云草堂刻本:第10輯第2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8]袁枚,伍拉納.隨園詩話·附批本隨園詩話批語[M].顧學(xué)頡,校點.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2.
[9]洪雅縣續(xù)志[M]//故宮珍本叢刊:第212冊.四川府縣志:第8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10]李斗.揚(yáng)州畫舫錄[M].北京:中華書局,1997.
[11]郭麟.靈芬館詩話[M]//杜松柏,主編.清詩話訪佚初編:第2冊.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
[12]石玲.袁枚詩論[M].濟(jì)南:齊魯書社,2003.
[13]郭紹虞.清詩話續(xù)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4]盧見曾批《杜子美詩集》[M]//芷蘭齋藏稿鈔校本叢刊:卷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15]盧見曾批《杜子美詩集》[M]//芷蘭齋藏稿鈔校本叢刊:卷三.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6.
[16]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7]陳書錄.明代詩文創(chuàng)作與理論批評的演變[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5.
[18]盧見曾.雅雨堂文集[M]//清代詩文集匯編:第26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責(zé)任編輯 于 湘]
2016-09-08
袁鱗(1992— ),男,河南駐馬店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區(qū)域文化與中國文學(xué)。
I206.2
A
1008-6390(2017)01-005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