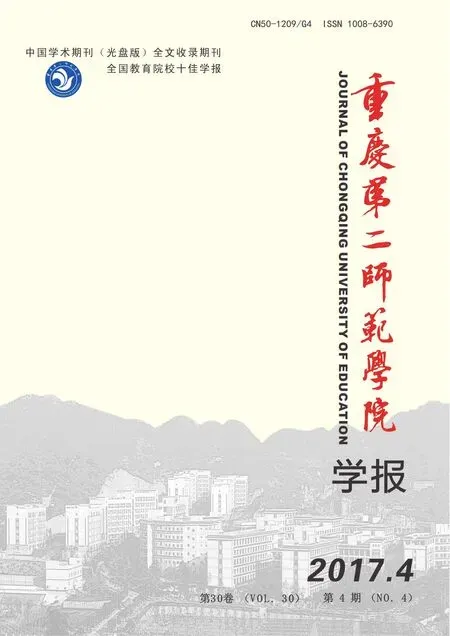政治與經濟二重奏下的中國都市研究
——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評介
石 月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 610065)
?
政治與經濟二重奏下的中國都市研究
——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評介
石 月
(四川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成都 610065)
日本著名中國史專家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史》,是海外歷史學者研究中國城市的經典讀本。該書從經濟史的角度出發,認為不能單一地從行政功能來認識中國都市的發展,而應加入對經濟因素的考慮,強調工商業發展對城市的影響。唐宋時期,國力的強盛帶來了商業活動的頻繁,從而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城市的發展,都市中的市場體系和社會結構由此發生變化,工商業都市的形成和市鎮的崛起,印證了斯波義信的觀點。在探索商業因素對中國城市發展的影響力背后,更需對中國社會以及城市的發展模式加以關注。
中國都市;斯波義信;經濟史;城市自治
斯波義信作為日本及國外學者中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先驅,其《中國都市史》[1]一書重點從中國式都市的“中國特色”方面來討論,“一改以往的都市史研究多從行政的側面探討都城到縣城功能的研究路徑”[2],聚焦于經濟活動和民眾文化,歸納中國都市的發展歷史以及傳統體系,并詳細分析了漢口、寧波、上海和佛山等幾大都市或市鎮的具體發展情況。斯波義信在這本書中強調對都市市場體系和社會組織的關注,最終展示給讀者一部區別于“行政都市史”的“經濟和社會都市史”。這與傳統的“中式”城市史研究有著較大的區別,因此受到學界極大關注,已經成為研究中國城市史的必讀經典。
一、斯波義信筆下的中國都市
在《中國都市史》這樣一個宏大的題目之下,這本書的內容其實并沒有那么包羅萬象,而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待中國城市發展的一次嘗試。斯波義信在前言中自述該書有兩個要點:一是闡述中國都市的形成及其發展變化的狀況;二是論證在中國“都市的存在無論從歷史角度還是從社會角度來看都是一種普遍現象”。
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前兩章對縣城與鄉鎮、都市的空間、都市的體系和社會結構的狀況進行了有針對性的闡述。第三章是對漢口、寧波、上海、臺灣、佛山進行詳細解讀。結語則對全書進行補充和總結。
第一章名為“歷史上的都市”。首先,斯波義信從夏商時期“邑”的形成開始,講到秦朝郡縣制的產生。邑,是邑制都市,或都市國家,是中國古典官僚制的溫床。由邑向縣的轉變,是中國古代城市變為“點”領導“面”的開始。這個轉變在漢代末期結束,并在西晉時期形成真正的郡縣制度。此時,“鄉”不再是一個聚落的名稱,而是縣下轄的行政區劃的名稱。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大規模的移民和自然村落的普及,村落、村莊等詞語開始出現,“鄉”開始變為新的農村地域名稱。城市中的居民居住在“坊”。農村的“鄉村”和都市中的“坊郭”開始區別開來,城與鄉的二元對立出現。其次,斯波義信認為唐中期開始“市”的轉變。唐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大變革時期。隨著交通的便捷,村市、草市、山市等逐步出現,社會向商業化、都市化轉型。唐末五代時期,草市中規模較大的成長為“鎮”,鎮和市結合到一起的市鎮在各地形成。宋代時,都市中的行會組織形成。商業繁盛,酒樓、茶肆、飯店等,開始彼此交錯集中在一起。此外,斯波義信對中國城市的空間形態進行了思考。中國城市的選址一般多在低地,城墻形狀以規則的正方形、矩形最為常見,不規則的橢圓形、半橢圓形、圓形、半圓形,或六邊形、五邊形等也都存在。城市內部的規劃設計也多根據《周禮》禮儀制度和道教風水來進行。
第二章名為“都市的體系”。斯波義信根據中國的都市行政體系,自然、經濟都市體系,結合地理特征,將中國劃分為八個大地域。在這一章中,斯波義信討論了近代中國的都市化程度。結合施堅雅對20世紀中期四川農村的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結論是——中樞地區人口多,稠密度高,都市化率也高。斯波義信根據對都市的不同定義,認為中國的都市化率大致為5.3%、5.5%、6%、6.5%,經修正,基本可以確定為6%。來自長江上游地區也就是四川地區的數據測定結果,基本可以代表中國整體的平均數值。斯波義信還考察了中國都市中的社會構成。首先,斯波義信認為在松散混亂的中國都市中,中國特色因素可從城市規劃中總結出來:一是官紳區和工商區兩個中心并存的結構;二是工商中心區的位置取決于和交通要道之間的關系。其次,繁華的都市吸引了大量的外來者,外來人口所結成的同鄉行會和同業行會成為普遍現象,城市之間人和物質的地理移動成為一種常態。城市逐漸變為多樣化及多樣性社會,許多行會從地緣性盈利組織逐步過渡,開始參與全市性的市政活動和公共福利事業,這一趨勢從“善堂”“善會”的普及可以看出。
第三章名為“都市的解剖圖”。本章主要針對四個具體城市的情況進行了說明。“只看長安或北京無法了解中國的都市史”,相比北京、長安、洛陽、南京、開封、蘇州、杭州等歷史名城,斯波義信特意選擇漢口、寧波、臺灣和佛山作為具體案例的切入點。斯波義信認為,上述那些著名的城市,可能具有中國城市的典型性,但是像漢口、寧波、佛山這樣的城市或市鎮更有普遍意義,能更好地理解中國都市發展的一般情形和整體特征。首先,斯波義信敘述了漢口三鎮合一的進程。在高速發展的19世紀后期,工商業成為漢口的主要產業。在斯波義信看來,被稱為“外來者都市”的漢口培養了“市民自治”和“市政”,且成績突出。其次是寧波。寧波和上海都是因為汽船航運轉折時期,因擁有外港碼頭而發展起來的城市。在傳統社會時期,寧波的官僚、士大夫、工商階層各自擁有一定的地盤和空間,共生共榮。在對寧波的描寫中,斯波義信繼續強調同業行會的重要作用,“三江幫”是活躍于江浙滬地區的商人群體,其核心就是寧波商人群體,或稱“寧紹幫”。“寧紹幫”在近代戰勝各地商人,逐步控制新興都市上海。這些都是從寧波的視角對江南三角洲地區都市體系重組的描寫。第三是臺灣。臺灣的開發伴隨漢族移民進行。臺灣的漢化,由南向北逐步推進,在近代,最大的城市是臺南。“三郊”是由北郊、南郊和港郊聯合組成的商人團體,也是臺南最大的商人群體,以致政府將民事和商事的司法權交付這個團體。最后是關于佛山的成長歷程。唐中期起,城外的市得到發展,并在五代時期促使一批市鎮的崛起。在清代,佛山人口急速增多,依靠金屬加工業、造紙業、陶瓷業等,城市建設迅速發展,其規模已經區別于普通的鎮,清政府為此設置了專門的派出機構進行管轄。
本書的“結語”部分則對市鎮的崛起和行會組織的發展進行了補充說明。
二、政治與經濟的都市二重奏
斯波義信試圖說明的問題,即中國的都市或城市之形成和發展,是在政治和經濟兩個因素的雙重影響之下的普遍現象。在宋之前,受行政因素影響、發揮政治職能的城市占據中國都市的大部分,“行政中心城市體系在強大的政治因素作用下得以逐步確立,并不斷發展完善”[3]。宋代以后,由于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南方大片地區得到開發,交通條件不斷改善,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等因素的影響,大批市鎮崛起,行使經濟職能的都市得以在此基礎上形成并逐漸增多,其顯著標志就是南方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國家經濟重心的轉移。斯波義信對都市之中官紳區和工商區的關注,就暗含對政治和經濟因素的影響力的強調。
斯波義信主張打破傳統歷史學者所認同的中國所存在的城鄉二元對立的觀點,認為不能膚淺地從行政功能來認識中國都市的產生和發展,還應加上經濟功能,強調工商業對城市發展的影響,并用數據、模型進行分析,試圖重新審視中國的都市。同時,斯波義信在該書中隱晦地表達了其認為在“府-州-縣”結構之外,因商業化的發展而形成市鎮的合理性這一觀點。尤其是明清以后,沿海沿江地區以經濟功能為主的都市和市鎮的興起,最終推動中國城市體系的演化發展。斯波義信對于中國市鎮的形成過程和運行機制的考察,無疑是具有前瞻性和豐富內涵的。
“由誰來控制地方政府的問題一直是城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三種觀點引起了爭論——精英觀點、多元論觀點和州管理主義觀點。”[4]有學者認為,城市控制在一些精英手中,形成了城市自治和地方政治,市民能自主地、積極地參與城市治理。斯波義信在“前言”和“結語”部分與韋伯等中國城市研究的前輩進行了對話。韋伯向來認為中國城市之中并不存在市民自治這一環節,因此中國的“城市”并不存在真正的城市。但是斯波義信通過對傳統社會晚期的同鄉團體、同業團體的描述,說明中國城市并不是完全由政府意志所主導,同樣存在市民自治,且這樣的自治是通過同業公會、行會的方式實現的。這一論點與羅威廉的論點相同。著名經濟史學家羅威廉在《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中 “承認行會具有重要社會政治功能”,并且著重“考察它在社會地方生活中的另一些正式與非正式的作用”[5]。與斯波義信一樣,他認同在中國除官府之外,存在這樣一個市民組織對城市進行管理和維護,充當了西方社會中的市民自治這一環節。
三、新思維下的中國都市史研究
經濟史著重于研究經濟領域的發展、變遷的過程和原因。經濟史既是人類社會過去所有發生過的經濟活動的匯總,也是經濟史學者對過去的描述、研究和探索。經濟史常常為現實世界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經驗、途徑和方法。斯波義信是一位研究經濟史的學者,他的代表作《宋代商業史研究》《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是研究中國宋代經濟的必讀書目。在這兩本書中,斯波義信從生態、農業、商業、城市、社會等方面,試圖還原真實的宋代經濟史。而《中國都市史》則超越某一朝代、某一地區的范圍,關注點從上古時期中國城市的發源直至清代的快速發展期,從某一地區轉向無規則誕生的五大都市或市鎮。其新穎之處,極為引人關注——斯波義信看待中國城市的角度吸引著史學研究者和普通讀者——不同于傳統的研究城市歷史的學者們的視角,也不同于考古學家們對城市平面布局、分期、淵源的強調,而是運用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在第一章中對中國都市的時間和空間進行討論,第二章對社會學的結構進行思考,之后再進行案例研究,體現的是一種理論結合實地調查的方法。
更為重要的是,斯波義信因其經濟史學者的身份而別具一格的思維方式。斯波義信認為,歷史靠數據說話,對數據的重視是其作為一個經濟史學者的基本特征。第二章中對中國都市化率的探索是本書最難懂的部分(或許是因為斯波義信自主省略了一些計算過程而直接呈現了計算結果)。有著經濟學相關教育背景的學者,對于建立數字模型來分析和解決問題較為擅長。斯波義信結合施堅雅的調查報告以及“中心地”學術概念[6],把中國劃分為八大部分,然后用七至八個層級來界定行政層面和經濟層面,城市與城市之間的上下關系并劃分等級,思考它們的匹配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有猜想、有論證、有結論。斯波義信通過圖表進行分析,提出假設,最后推翻假設,得出結論。不得不說,如此量化的研究方法體現了一門學科的科學性,這也是大多數文科出身的歷史學者所欠缺的。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史》以及《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7]提供了一條很好的思路。“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各學科的研究方法大量滲入經濟史研究,以致經濟史研究逐漸從主要依靠史料考證方法的學科,演化為多學科方法結合的學科;從以描述歷史上經濟現象及其變化過程為主的‘敘述史學’,發展為以探索歷史表象下隱藏的深刻內容為目的的‘問題史學’”。[8]
值得思考的還有斯波義信提出的城鄉二元對立問題。本來,城與鄉并沒有相反的含義,鄉也是都市群中的一類。自唐代起,城鄉的對立情況變得明確。從宋代開始,市鎮在鄉村中出現。但直到清代,城鄉二元對立結構保持不變,并沒有產生“城-鎮-鄉”三元結構。盡管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鎮這一行政單位才得以確立,但其源頭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紀。那么,為什么中國明清時期的統治者如此固執地遵守著這樣一種城鄉制度?斯波義信認為,也許是“儒化”以及強化儒家思想所帶來的模式的僵化。自儒學產生以來,其對于傳統社會方方面面的影響,不言自明。從觀念到方式,從政策制定到具體實施,民眾和國家都深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可以說,中國的文明與秩序,深深扎根于儒家思想之中。儒家思想推動了傳統社會的進步,但“儒化”所造成的語言和文化的固化,也在某種程度上固化了人的頭腦和社會的發展。
此外,前述斯波義信有關都市市民自治的問題,同樣值得思考。中國古代行會由來已久,唐宋時期已經形成行會雛形,明清時期得到發展,是傳統的城鎮工商同業組織。商人們按照一定的行規成立行會組織(或稱為幫)來對本行業進行管理并力圖促進行業發展。晚清時期,中國城鎮經濟發展速度加快,工商業從業人數增多,行會數量也相應增加。除了傳統的行會組織本身,會館、公所等具有行會性質的同業組織也十分發達。會館在長江上游地區尤為多見。清朝立國初期,飽受戰亂禍害的長江上游地區終于得以安定下來,在政府的政令下,大批來自陜西、湖南、湖北以及江西的移民進入四川、重慶。這些移民共同出資在異地設立同鄉會館,以祭奠鄉神、舉行同鄉聚會等。根據學者對四川會館的研究調查,有4所會館以上的85個縣總計有會館727所。[9]由同鄉團體發展而成的同業公會、行會、會館等組織,在傳統社會中的地位和影響力是難以估量的。以漢口為例,羅威廉認為漢口就是一座被經濟因素深刻影響的城市。漢口商業發達,貿易繁盛,其社會和經濟結構促成了中國現代化的進行,商人群體對社會發展的影響力是巨大的,斯波義信重點關注其商業貿易及其機制[10]。而事實上,筆者認為,斯波義信過于強調同業經濟組織對城市發展的影響,但其實際影響力是未知的。漢口和成都本地行會在其各自都市中的影響力誰更大,這種影響力究竟到了什么樣的程度,其真相難以尋求——可能跟城市具體外來人口比重相關,可能與城市工商業經濟發展水平相關,也可能受到其他不明因素的影響。這一問題和斯波義信在《中國都市史》中所研究的其他問題一樣,在一定程度上也許并不適用于中國所有地區,僅是某一地方的個案,其廣泛性、通用性、普遍性都未得到印證,因此難以尋求一個通則。從研究范式上來說,將西方學術觀點中的“自治”這一觀念強加于傳統中國之上,是一種“西方中心觀”的表現。中國不具備西方城市的發展特征,西方社會的發展經驗也不適合中國,將中國套在西方的理論之下,是一種“精致的西方中心主義”。這種范式為當代中國史學者所詬病,受到多數學者的批判。因其將西方概念原封不動照搬至中國,而忽視了中國本身的實際狀況及中國在現代性構建中所產生的實際問題和具體過程,無論是“公共空間”還是“市民自治”,都將浮于表面而難以深入傳統中國的核心。同時,對傳統中國而言,學界對市民自治存在與否的爭論究竟是否具有價值,也是值得思考的。在筆者看來,讀者在閱讀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史》時不必過于糾結這個問題。
四、余論
斯波義信是日本戰后第一個中國史博士,是整個日本學士院中唯一一名中國史學者,是無可爭議的史學大師。誠然,其《中國都市史》也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斯波義信在該書第一、二章中對中國都市發展的整體性描述并不完整,沒有形成理論體系。其次,其對中國都市史的概括幾乎都是從經濟方面入手,顯得較為片面;而中國大地的廣袤和中國城市發展史的悠久,實在并非可從單一經濟原因闡述清楚——缺乏對政治、文化的融會貫通,無法解讀中國的內核,進而通覽中國的都市史。最后,斯波義信在對于影響城市發展的因素和市鎮崛起的原因的分析上,可能有些流于表面,還可以挖掘得更深。《中國都市史》比普通教材更專業,但相比嚴謹的學術著作又缺乏深度,僅有“片面的深刻”,應算是城市史、經濟史的科普讀物。該書的另一個軟肋是翻譯,譯者所用的語法結構類似翻譯機器遣詞造句的方式,有不少令人費解之處。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書名的翻譯卻相當精準,“都市”和“城市”的區別值得討論。結合斯波義信本人的意圖,都市和城市的區別,或是斯波義信意在強調“都”的重要性,即商業給城市帶來的意義。在翻譯書名時,對這一細節的重視,也是該書的價值之一。總的來說,瑕不掩瑜,斯波義信的《中國都市史》抓住了中國城市發展歷史中一個關鍵的要素,即工商業經濟對城市的影響,以此出發探討中國城市的特點,為中國學者研究城市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范式。
[1]斯波義信.中國都市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2]陳華文.經濟視角下的中國都市史[N].經濟參考報,2013-12-30.
[3]鮑成志.區域經濟變遷與中國古代城市體系的演化[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36-42.
[4]馬克·戈特迪納,萊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3.
[5]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沖突和社區(1796—1895)[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6]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7]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2:216..
[8]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介[J].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4):146-159.
[9]王笛.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M].北京:中華書局,2001.
[10]羅威廉.漢口:一個中國城市的商業與社會(1796—1889)[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責任編輯 文 川]
2017-04-05
石月(1992— ),女,重慶市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城市史。
K
A
1008-6390(2017)04-003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