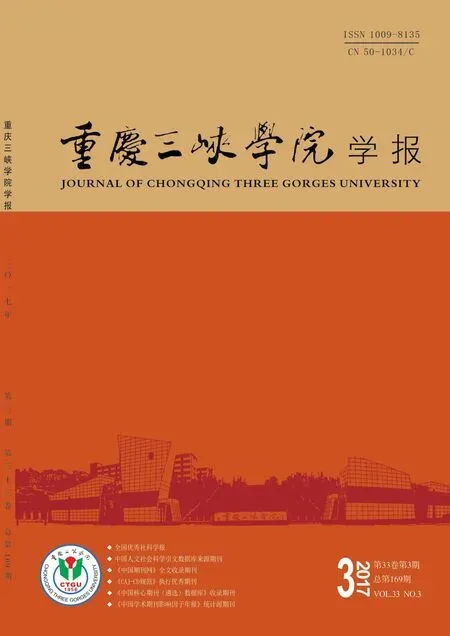論漢語修辭學體系的建立
——《文心雕龍》的修辭學研究
陳會兵 孫 婷 劉文亞
(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重慶 404020)
論漢語修辭學體系的建立
——《文心雕龍》的修辭學研究
陳會兵 孫 婷 劉文亞
(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重慶 404020)
《文心雕龍》不僅是我國第一部體大思精、震古鑠今的文藝理論和文章創作論著作,也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漢語修辭的理論著作,其修辭理論、辭格研究和修辭實踐達到了那個時代的高峰,初步建立起漢語修辭學的理論體系。《文心雕龍》開了漢語修辭學系統研究的先河。
《文心雕龍》;修辭理論;辭格研究;修辭實踐;修辭學體系的建立
《文心雕龍》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章創作論中內容最豐富、體系最完備的一部杰作,震古鑠今,它對我國傳統文學研究的貢獻可謂首屈一指,歷來備受推崇,對此書的整理、研究成為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一門顯學——“龍學”。同時它又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全面論述漢語修辭學的理論著作,標志著漢語修辭學體系的建立。作為一個具有濃厚儒家思想的理論家,劉勰的文學思想和修辭研究都深深地打上了儒家學說的烙印,但又能突破某些儒學正統觀念,他的文學思想、修辭學觀念和具體的修辭學研究都繼承、總結并發展了儒家經典的文學觀和修辭觀[1]。
在中國修辭學史上,《文心雕龍》主要繼承了孔子“文采”“尚巧”的修辭學說,兼采儒家經典和諸子著作“質”“文”辯證的修辭觀念,總結前代經典著作的修辭理論、實踐和方法,對傳統的遣詞、煉句、裁章、謀篇等主要修辭內容,特別是文學語言的修辭,均有精湛論述。其中《神思》《體性》《風骨》《情采》《熔裁》《聲律》《章句》諸篇從一般修辭理論、修辭的作用和效果、字詞的選擇、章句的組織、聲律的配合、語言的風格等方面(即后世所謂“消極的修辭”)全面具體論述了漢語修辭理論;《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等篇則總結了先秦以來儒家經典、諸子著作以及詩歌文賦的具體修辭手法和實踐(即后世所謂“積極的修辭”)并給予理論的提升;著作本身的語言也對我國六朝以前的修辭方法兼收并蓄,可以說是劉勰修辭觀念的具體體現和修辭理論的具體運用,反映了六朝時期文學藝術的自覺和“唯美”的時代精神[2]。
通過這些理論探討和修辭實踐,《文心雕龍》初步建立起了漢語修辭學的理論格局,跟其文學理論和文章創作論一樣,完成了中國傳統語言學中空前的系統的修辭學理論構架,指導著后世詩歌文賦和各種體裁文章的語言修辭,并給予漢語修辭學的進一步發展以啟迪。本文試從修辭理論、辭格研究、修辭實踐三個方面探討《文心雕龍》的修辭學研究,懇請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一、修辭理論
我國先秦時期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就十分重視語言的運用,他們在許多著作和文章中對漢語修辭進行了經典性的論述,如《尚書》:“辭尚體要,弗惟好異”;《易經》:“辨物正言,斷詞則備”;《詩經·淇奧》:“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論語·顏淵》:“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禮記·表記》說“情欲信,辭欲巧”;《老子》:“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等,成為漢語修辭學的發端[3]。這些著作和文章本身對漢語修辭也身體力行,成為后世文章的修辭典范(見《文心雕龍》的《原道》《征圣》《宗經》等篇)。劉勰《文心雕龍》批判地繼承了先秦經典和諸子著作的修辭觀念,結合后世人們對修辭的認識和自己的研究,建立了漢語修辭的一般理論體系。《神思》《體性》《風骨》《情采》《熔裁》《聲律》《章句》等篇集中探討漢語修辭問題,對漢語修辭的作用、修辭的方法等修辭理論的重要問題進行了集大成式的研究,還有許多其他見解散見于別的篇章,這些論述是對前代及當時語言修辭的總結和發展,這也是前無古人的,在修辭學上的地位無與倫比。
在文采與質實的關系上,劉勰繼承并發展了儒家“盡善盡美”(《論語·八佾》)、“文質彬彬”(《論語·雍也》)的文質論。《文心雕龍·情采》進一步主張“文附質”“質待文”,明確指出了文章內容決定修辭形式,修辭形式要為文章內容服務,要求情采相稱,他說:“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后緯成,理定而后辭暢,此立文之本原也。”提倡“為情而造文”,反對“為文而造情”。認為“聯辭結采”的目的是“將欲明理”,文章要以“述志為本”。如果“繁采寡情”,則“味之必厭”。處理文章文質關系要“文不滅質,博不溺心”,這樣才能做到“雕琢其章,彬彬君子”。《文心雕龍》本身就是一部“剖情析采”(《序志》)的偉大理論著作。具體說來,語言修辭應從形態、聲音、性情三個方面入手,他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性發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廣泛精研前代著作,分辨源流正邪,“亦可以馭文采矣”。劉勰要求文章既要內容豐富真誠,又要文辭美妙優雅,這是執筆作文的金科玉律,所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征圣》)。
語言修辭一個重要方面是錘煉字、詞、句、段和剪裁篇章。《練字》論述選字、擇字問題,即選擇最恰當的字眼來表情達意,使文章更加精美。要做到“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這里涉及兩個問題,一個是用詞問題(即字義),要求不用偏僻字,少用偏旁相同的字,要權衡一個字重復出現,這主要是從文章的內容考慮,同時也考慮了文章的形式;一個是書法問題(即字形),要使文章書寫出來以后有視覺上的美感,不能單調重復。除此以外,劉勰還告誡運用語言不可沿訛求奇,如對“別風淮雨”的論述。
《章句》:“夫人之立言,因字(詞)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劉勰明確指出字(詞)是篇、章、句的“本”,是語言和文學的基礎和根本,句、章、篇則是字(詞)生出的“末”,“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語言的正確使用必須做到字、句、篇、章不妄、無玷、無疵。只有這樣,才能達到文章修辭的根本要求:“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劉勰在本篇還進一步通過分析“兮”字探討了虛字“無益文義”(即沒有詞匯意義,“益”應理解為“增加”,而不是“有益、無益”)的本質,通過分析虛字在文章中“發端”“札句”“送末”等位置探討了虛字的“彌縫文體”“外字難謬”的語法作用和修辭作用,在漢語史上影響深遠。同時這也是我國最早的一篇文法、修辭結合論[4]。
《熔裁》對剪裁篇章有精到的論述:“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熔裁,櫽括情理,矯揉文采也。”寫作文章,布局謀篇的關鍵在于熔意裁辭,矯正文章情理上的偏差,修剪文辭上的毛病。“規范本體謂之熔,剪裁浮詞謂之裁。”熔裁文章情理和文辭首先要確定三個標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于終,則撮辭以舉要”。其次要討論字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疏;字不得減,乃知其密。”“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熔裁,何以行之乎。”熔意裁辭要達到“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意顯”的境界。劉勰對錘煉詞句、剪裁篇章的精到論述對今天我們運用語言仍然具有啟發意義。
充分運用漢語聲律來增強文章的語音美是漢語修辭的另一個重要內容。運用語音來增強語言和文章的美感是魏晉六朝的時代風氣。《聲律》篇從聲律的產生、聲律與音樂的關系、聲律在語言中的運用、聲律對文章的重要修辭作用等問題給予了充分的論述,是對六朝時期我國音韻學研究的理論總結,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限于論題和篇幅,茲不詳述,參見拙文《〈文心雕龍〉的語言學研究》)。同時也將聲律理論運用到文章創作中。語音對文章的修辭作用不容忽視,《神思》:“循聲律以定墨。”《聲律》:“音以律文,其可忽哉。”“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關鍵,神明機杼,吐納律呂,唇吻而已。”這是說人的語言是構成文章的關鍵,是表達思想的機關;吐辭發音要符合音律,要調節唇吻等發音器官。《聲律》論述利用語音進行修辭就要做到聲韻調配合,劉勰稱:“凡聲有飛沉,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離句而必睽;沉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飏不還,并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聲調的飛沉(高低升降)與雙聲疊韻必須“轆轤交往,逆鱗相比”,“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這樣才能達到“聲轉于吻,玲玲如振玉;辭靡于耳,累累如貫珠”的語音效果。語音在語言運用上還要注意兩點:“異聲相從謂之和,同聲相應謂之韻。”“和”與“韻”有顯著的不同:一是求異,一是求和;兩者又有相通之處:異中求和,同中求韻,以此構成完整和諧的統一體,構成優美的聲律。對當時兩大不同的文體“文”與“筆”在語音修辭上的運用也進行了比較,認為“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寫作無韻之“筆”容易工巧,但要使音調和諧(異聲相從)最困難;寫作有韻之“文”難以精工,然而壓韻(同聲相應)卻很容易。劉勰還從反面指出,文章違反“聲律”要求,必然導致“文家之吃”,就會“吃文為患”。六朝聲律理論的研究及運用于詩文創作,為六朝駢文的盛行和唐代“一代之文學”——律詩的鼎盛打下了基礎,這是語音修辭對詩文發展重大影響的一個結果,劉勰《文心雕龍》的推動功不可沒。
《風骨》《體性》等篇集中論述了文章的藝術風格,但是語言風格是形成文章藝術風格的一個重要因素,作家的語言風格又主要體現在修辭上,因而它們也是修辭論著。《風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故練于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苑: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章之鳴鳳也。”“若骨采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騖新作,雖或巧意,危敗亦多。”“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光華。”這些論述闡明了藝術風格、語言風格對于文章和作家的極端重要性。《體性》篇則具體總結了文章的藝術風格:“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如前所述,語言的風格是形成文章藝術風格的主要因素,作家的語言風格又主要體現在修辭上,因而,這些藝術風格同時也是作家通過修辭而得到的語言風格。
二、辭格研究
修辭格的使用是語言修辭的主要內容之一,陳望道在他的《修辭學發凡》里將這種有意識使用的特殊修辭方式稱為“積極的修辭”。一般認為,對修辭格的全面研究始于宋代陳騤的《文則》,但是,就事實而言,《文心雕龍》首開辭格全面研究的先河。《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等辭格專論總結了先秦至齊梁時期儒家經典、諸子著作以及詩歌文賦具體的積極的修辭手法和實踐并給予理論的提升。只是前修未密,后出轉精,這是學術發展的規律。劉勰的時代,人們對修辭格的認識可能還相當粗疏,許多人們經常使用的修辭手法(即“積極的修辭”)在當時并沒有總結為特殊的修辭方式(即辭格),后世才確定為“積極的修辭”,這是當時人們認識水平的限制。另外,《文心雕龍》“體大而慮周”,它側重論述原理、原則性問題,要求其理論具有“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跨越前哲的系統性,對細枝末節不做過多追究。因而,劉勰有意識地在《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等篇里詳細討論了當時“駢文”常用的一些修辭格,而其他一些修辭格則散見于其他篇章之中。但這些討論并不是零散的,而是深入、系統、全面的。
《麗辭》篇論述對偶修辭格。麗者,儷也,兩個結構比較一致,詞義、音律上下相對的一組(兩個或兩個以上)句子就是麗辭。劉勰將對偶句式分為四種:言對、事對、正對、反對,前兩種是從內容上劃分,后兩種對形式也有考慮,雖不及陳騤《文則》和現在人們給對偶句式的分類精細,但他首開根據內容和形式給對偶句分類并進行深入研究的先河;總結對偶的方式則有“句句相銜”“字字相儷”“宛轉相承”“隔行懸合”等等,這些對偶句式“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麗辭》篇還討論了這四種對偶句的修辭運用和效果,認為“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通過舉例說明用得不好的對偶句為“句之駢枝”,一意重出,即后人所謂“合掌”;要求屬對優劣相配,“務在允當”。六朝駢文盛行,《文心雕龍》受時風影響,也多用偶句,但他并不排斥單行奇句,認為“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相反,“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聵耳目”,這也是劉勰對六朝綺靡文風、片面追求對偶形式的匡正。
《比興》借助《詩經》的“六義”講解比興,“比興”之義,歷來人們認識分歧,有人認為是“詩體”,有人認為是“詩法”。但是細按文意,我們認為在劉勰的觀念中,比與興在語言的運用上沒有什么實質的區別,都是指比喻。“‘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義。”所謂“比”就是“寫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興”要“起情”“擬義”,指的就是有譬喻作用的起語。比較而言,“比顯而興隱”。“比興”的作用是“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比喻的方式則是“或喻于聲,或方于貌,或擬于心,或譬于事”;比喻的運用要做到“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比喻用得不恰當則“刻鵠類騖,則無所取焉”。
《夸飾》一篇論述夸張的修辭手法。普通語言的運用,常常會出現“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而運用夸張的修辭手法,則可以做到“形器易寫,壯詞可以喻其真”。盡管運用了夸張的修辭手法,卻可以描摹事物的真實情狀,“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劉勰還簡要地論述了夸飾的發展,認為“自天地以降,夸飾恒存”,“大圣所錄,以垂憲章”,“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修辭運用夸飾,則“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夸飾運用得當,能抓住要領,讀者的共鳴就會蜂擁而起;夸飾運用得不好,即“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運用夸飾的修辭手法基本原則是要做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事類》:“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據事以類例,援古以證今者也。”事類就是引用古事古語來論證支持作者自己的觀點。這一修辭手法歷來受到人們普遍的重視,所謂“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乃圣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用人若己,古來無懵”。“引成辭”“舉人事”的主要作用是“明理”“征義”,其主要方法和修辭特點則有“重言”“綴采”“起興”“節縮”。經籍深富,文采浩瀚,人人都可以從中吸取營養,為我所用。然而,要恰當地引用事類,就必須要有淵博的學識,多識古人、古事、古語,即所謂“宗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捃理須核,眾美輻輳,表里發揮”,才能做到“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用典不能“引事乖謬”,否則就會“雖千載而為瑕”。《事類》是中國語言學史上第一篇全面研究“事類”辭格的專論,全篇幾乎無一字不是談引用辭格。
除上述辭格專論外,《練字》《諧隱》中論述了“隱語”“謎語”等辭格,認為好的隱語應該“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貴在“理周要務”。《物色》篇討論了“摹狀”“復迭”等辭格:“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沉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瀌瀌’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喓喓’學草蟲之韻。……并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所舉例子,都是身兼“摹狀”“復迭”兩種辭格。
劉勰還特別注意文字書寫書法的美感作用,《練字》篇認為字形對于修辭的作用與語音對于修辭的作用同樣重要,即所謂“諷誦則績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這是從聽覺上和視覺上追求語言的美感。為了追求文章的字形和書寫美,劉勰提出“綴字屬篇,必須練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復”,要求文章不用詭異的字,相同偏旁部首的字應盡量避免連用,如果實在不可避免,一句之中可用三個聯邊的字(即“半字同文者”),要權衡重出的字(即“同字相犯”),但是“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這是與劉勰形式服從內容的正確認識一致的,還要注意調整單復(即“字形肥瘠”,筆畫多少),不能“瘠字累句”,也不能“肥字積文”,字形的肥瘠要相間,做到“參伍單復,磊落如珠”。只有這樣才能在文章書寫上給人以視覺享受。我們知道東漢發明了紙張,魏晉之際,書法大家、書法理論相繼出現,當時的書籍主要靠手抄,為追求美感,人們必須注意書法和漢字的結構。劉勰要求作家在寫作的時候,除了要考慮文章本身內容和形式的美感以外,還要注意文字書寫書法的美觀,也就是要求文章寫作要聲音美、視覺美、感覺美(內容美),在可能的條件下,無一不美。這是一般研究語言文學的理論家不大注意的,不管這種要求是否合理,但它體現了六朝“唯美”的時代風氣和劉勰的修辭思想。隨著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應用,書籍文章在文字書寫上千篇一律,后世人們也就不再考慮文字書寫書法的美感作用了。
三、修辭實踐
劉勰是文章學和文學理論大師,也是語言學和修辭學大師,其《文心雕龍》可謂一部語言和修辭寶典。《宗經》篇闡述了劉勰修辭的總標準,他說:“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他將儒家經典視為“群言之祖”和文章之祖,是漢語修辭的楷模,認為“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若征圣宗經以立言,“則文其庶矣”。而對那些不合經典的“緯書”,盡管從內容上斥為“乖道謬典”,但在形式上卻贊譽其“詞富膏腴”,認為“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辨緯》),體現了劉勰的儒家正統觀念及對這種正統觀念的某種超越。
劉勰的修辭要求體現在《附會》中:“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后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恒數也。”劉勰在此盡管說的是“才童學文”,但是,任何人寫文章道理都是一樣,都要“附詞會義”即煉字選詞、聯句成章來表情達意。他認為寫作文章除了必須有“情志”“事義”(思想內容)外,還要講究“辭采”“宮商”(藝術形式、語言美感),要從文章內容和形式等幾個方面來品評文章有無毛病,存優去劣,做到恰到好處,這是構思作文的一般規律。明確指出了漢語修辭的主要內容,包括文章內容和形式的諸多方面(與今天人們一般認為修辭只講究語言形式有區別,但筆者認為如此則更科學)。《文心雕龍》的語言運用體現了劉勰的修辭主張。
《文心雕龍》還總結了不同文體、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修辭實踐。在其 20篇文體論中分別論述了每一種文體的語言運用、修辭準則和技巧(篇幅所限,茲不贅述),《定勢》簡要概述了一些文體的修辭標準:“是以括囊雜體,功在詮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范于核要;箴銘碑誄,則體制于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與巧艷: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表明修辭手法的運用不是千篇一律的,應該隨勢而變,適應文體和內容的需要。《才略》品評上古至劉勰當時作者的文學創作,對各時代的作家作品的語言和修辭也做了簡要總結,如:“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辭義溫雅……商周之世……文亦足師……春秋大夫,則修辭騁會……”等等,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修辭面貌;又“魏文之采,洋洋清綺……子建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子桓慮詳而力緩……”等等,表現了不同作家的修辭風格,在歷時和共時兩個層面上全面概括考察漢語修辭的總體情況。這些不同時代、不同作家在修辭上各有特色,造成了他們不同的藝術風格。《時序》篇可以說是一篇簡略文學史,文學、語言、修辭三位一體,文學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語言和修辭的發展,或者說語言和修辭的發展是文學形式發展的標志之一,在這個意義上說,《時序》篇又可以說是一篇修辭風格簡史,正所謂“蔚映十代,辭采九變……質文沿時,崇替在選”。
《指瑕》從反面論述修辭失當的教訓,概括地說,修辭瑕疵主要有六類:一、文義失當之瑕;二、比擬不類之瑕;三、字義依稀之瑕;四、語音犯忌之瑕;五、掠人美詞之瑕;六、注解謬誤之瑕。認為“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具體舉出曹植、左思、潘岳的措詞不當,崔瑗、向秀的文章比擬不類,這些人文采風流,但在修辭的時候也還存在著一些嚴重毛病,說明運用修辭必須認真嚴謹,否則將“斯言一玷,千載弗化”;運用修辭的瑕疵除上述毛病以外,還有用詞“依希其旨”,“逐奇失正”,造成詞義不明確;“比語求蚩,反語取瑕”,即用諧音字和字詞的反切來挑毛病,這是六朝文士賣弄聲律的不良后果;劉勰還特別指出修辭(包括文章)貴在獨創,反對抄襲剽竊,他說:“制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掠人美辭,以為己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輕薄無德),時同者為尤矣。”這給“文抄公”們敲響了警鐘。
《知音》確立了判斷修辭效果的標準:“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詞,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與《指瑕》篇一起從正反兩個方面論述了修辭的原則和要求。
盡管《文心雕龍》是一部理論著作,不能很好地體現劉勰的修辭實踐,但它的語言仍極有美感,富有形象性。首先就整部著作的結構來看,《文心雕龍》像一座宮殿,外表規模宏大、金碧輝煌,內部奇珍異寶、流光溢彩。全書自序一篇,總論五篇,文體論二十篇,創作論十九篇,批評論五篇,共同構成一個完整有機而且自足的理論體系;分開來看,五十篇論著又可分別獨立,每篇集中論述一個問題。這樣環環相扣,珠聯璧合,共同支撐起《文心雕龍》的理論大廈,反映出他對整部著作布局謀篇的匠心。
文章句式整齊,幾乎全用對偶句,但又根據表達的需要,不完全拘泥于嚴整的對偶句,讀起來朗朗上口,抑揚頓挫,富有節奏感、音樂美。字詞錘煉,詞義句義高度濃縮,巧妙化用前人事跡和言論,內容豐富而又韻味悠長,語言典雅含蓄,又富有說服力;有意識地選用色彩鮮明、形象突出的詞語,詞句的聲律和諧,廣泛運用雙聲、疊韻、疊字的詞語,合理利用漢語四聲,使文章如行云流水。長句短句、肯定句否定句、主動句被動句、常式句變式句、奇句偶句、單句復句等等各種句式交錯使用,服從表達的要求,不拘一格,靈活多變,構成搖曳多姿的視覺、聽覺和感覺形象。常見的修辭手法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等在全書幾乎俯拾皆是,婉曲、排比、對比、設問、反問、摹狀、復迭等后世常用的修辭手法也幾乎都能找到,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總之,《文心雕龍》的語言修辭實踐已經涉及到后世修辭的方方面面,是劉勰語言學和修辭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和實際運用,也是漢語語言學和修辭學的典范著作。
四、結 語
魏晉六朝是我國文學藝術的自覺時代,文學、繪畫、書法等藝術門類在這個時期有了長足的發展,各自脫離其他門類開始獨立成為一個學科。漢語修辭學體系的建立可謂生逢其時。三曹、七子、陸機、摯虞、李充、鐘嶸、蕭統等文學家開始了對文學理論和文章創作理論自覺的探討,成就引人注目,盡管他們的研究“各照隅隙,鮮觀衢路……并未能振葉而尋根,觀瀾而索源”,但他們都在各自的方面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理論研究無一例外都必須建立在科學的語言研究和修辭研究的基礎之上,他們對文學、語言、修辭的研究為《文心雕龍》的全面研究作了鋪墊、準備了條件。
《文心雕龍》在漢語修辭學研究上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其修辭學理論、辭格研究、修辭實踐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已經全面建立起了漢語修辭學的理論體系,直到今天,漢語修辭和修辭學研究,仍然沒有超出這個理論框架。可能由于其震古鑠今、光輝燦爛的文學理論和文章創作理論的成就遮掩了其語言學和修辭學的價值,一直以來人們對《文心雕龍》的語言學和修辭學成就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上述有關漢語修辭的問題在文學理論家的心目中又都往往視為藝術表現手法,大多從文藝美學的角度而不從語言角度進行分析研究,這是令人遺憾的。
文學理論、語言研究、修辭研究三位一體、密不可分,《文心雕龍》在建立起它的文學理論和文章創作論體系的同時,也建立起了它的語言學和修辭學的理論體系。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文心雕龍》的每一個篇章都論述了語言和修辭問題,這是應該引起語言研究者注意的。
研究《文心雕龍》的修辭學,有助于我們了解中古時期漢語和漢語修辭的現狀和成就,了解漢語和漢語修辭的歷史和發展。如果沒有對《文心雕龍》的語言學和修辭學全面深入的研究,這將是“龍學”研究的嚴重缺陷,這樣建立起來的漢語語言學史和漢語修辭學史,也是很不全面的。
[1]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2] 鄭子瑜.中國修辭學史稿[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3] 陳會兵.儒家經典和諸子著作的語言學思想[J].黃岡師范學院學報,2003(4):61-65.
[4] 陳會兵.虛詞在先秦詩歌里的修辭作用[J].涪陵師范學院學報,2003(4):39-41.
[5] 李裕政.文筆之辨研究述略[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2):43-46.
[6] 論《文心雕龍》的生命化批評[J].三峽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S1):77-78.
(責任編輯:鄭宗榮)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heto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The Rhetoric Theory Study of Wen Xin Diao Long
CHEN Huibing SUN Ting LIU Wenya
(College of Art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Wen Xin Diao Long is not only the first classical book of literary criticism and essay writing in China, but also the initial book on Chinese rhetoric theory. Its rhetoric theory, researches of figures of speech, and practices of Chinese rhetoric are all the symbols of that era. It was this book that first constructed the rhetoric system of Chinese language as well as set a pattern for figures of speech researches.
Wen Xin Diao Long; rhetoric theory; figures of speech research; practice of rhetoric; construction of rhetoric system
H15
A
1009-8135(2017)03-0060-07
2017-02-28
陳會兵(1967—),男,重慶奉節人,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漢語史和古典文獻。
孫 婷(1993—),女,重慶云陽人,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在讀碩士生。
劉文亞(1986—),女,河南鄧州人,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在讀碩士生。
重慶市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重點項目“地方應用型本科院校漢語類課程‘3+1’教學模式的構建與實踐”(142024);重慶三峽學院高等教育教學改革研究項目“應用技術大學轉型條件下漢語類課程教學內容、模式的改革與實踐”(GJ150709)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