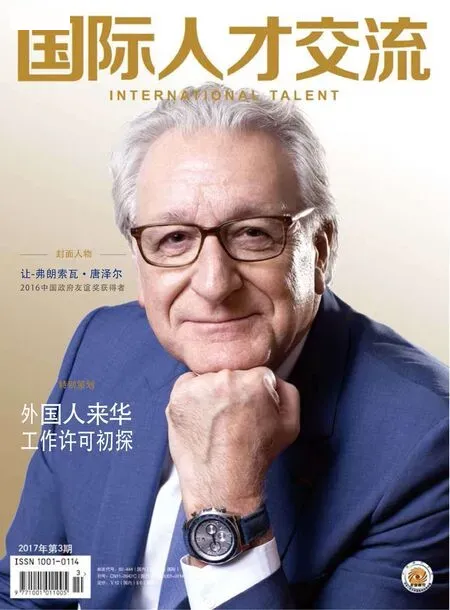印度生態毒理學家“宅”在昆山
文/楊美萍
印度生態毒理學家“宅”在昆山
文/楊美萍

在蘇州昆山的菜市場,人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膚色黝黑的印度人來買菜。你可別以為他是個廚師,其實他是一位科學家,一個有著30多年工作經驗的生態毒理學家。他光顧菜場,買的不僅是自己的食物,還有實驗所需的材料。他就是江蘇龍燈化學有限公司的生態毒理實驗室負責人湯姆森·馬泰(Thomson Mathai)博士。
湯姆森的第三個GLP 實驗室
2011年底,56歲的湯姆森受龍燈公司邀請,首次來到中國來到蘇州昆山,組建了該企業第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符合良好實驗室規范(GLP)原則的生態毒理實驗室,也是目前中國唯一獲得德國GLP認證、專門進行作物保護研究的實驗室。
GLP原則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認可的一套國際協議的法規,致力于研究的可靠性和完整性、結論報告的可驗證及數據的可追溯性。目前,很多國家對于進入本地市場的化學品都要求必須擁有GLP實驗室出具的安全性評估數據。因此,得到GLP認證,本身也是實驗室研究能力和權威性的一個證明。

湯姆森(左)在實驗室工作
作出到中國來的決定,對湯姆森來說非常簡單。龍燈公司決定設立這樣一個實驗室的時候,因為國內相關方面的人才匱乏,于是請了一位印度顧問幫忙找一位可以主事的科學家。對方推薦了經驗豐富的湯姆森。早在碩士研究生階段,他就參加了關于印度一家水泥廠對周邊生態環境污染的研究工作,此后一直從事生態毒理和環境保護方面的研究,并于1991年創立了《印度環境和毒理學雜志》。1996年,湯姆森建立了印度國內首家GLP生態毒理實驗室,2000年又創建了第二家。“我的朋友問我,愿不愿意到中國來搞一個GLP實驗室,就和我們15年前做的一樣,我說,好的。于是,我就來了。”湯姆森愉快地回憶說。
自從加入龍燈公司后,湯姆森親力親為,對實驗設施的采購和布置都提出了專業的指導,他還親自購買了水藻、浮萍、水蚤、溫水魚、冷水魚、蚯蚓和蜜蜂等用于實驗的生物。
和很多生化實驗室不同的是,湯姆森的工作場所很少看到試管、燒杯、酒精燈等實驗器材,他和同事們每天的工作就是觀察各種生物在不同濃度的農藥環境下的活躍程度,這需要靠研究人員的觀察來衡量,而不是用儀器測定的,這就意味著經驗至關重要。對湯姆森來說,工作方面的事可謂駕輕就熟,一切都進展得很順利。他進行了百余項測試,為公司的農藥產品進入歐美等國際市場做出了巨大貢獻。湯姆森表示,在現代農業中,農用化學品的使用不可避免,但政府必須制定安全標準,嚴格管理,企業的任務則是遵守這些規定,將自己的產品控制在安全范圍內。
龍燈實驗室管理人員李莉表示,隨著政府和民眾對環境保護和環境安全越來越重視,創立生態毒理學實驗室已經成為公司戰略性發展布局中的重要一環,湯姆森的貢獻意義重大。“通過生態毒理實驗,我們可以了解到我們的產品對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并針對相應的問題對產品的配方和使用方法等進行修改,確保產品安全性。”
人才流失困擾毒理學家
在自己的實驗室建立以前,龍燈公司通常的做法是把樣品寄給其他國家的GLP實驗室,請他們出具生態毒理學分析報告。這個過程非常漫長,因為這些實驗室接到的訂單很多,需要排隊,有時候一項測試就要等上半年。
有了自己的實驗室后,這個過程往往只需要一兩個月就能完成。對于一些緊急任務,還可以加班加點來完成,自主性很強。而且一旦發現問題,跟研發和生產部門的溝通也比以前迅速,能夠更快地對配方作出相應的調整,然后對新產品進行測試。如果外包給外國的實驗室,又得重新排隊,繼續漫長的等待。
成本也是龍燈決定自主建實驗室的一個重要原因。據李莉介紹,國外的實驗室價格高昂,“例如,在某一種魚身上進行的毒理研究就要上萬元,但魚的成本只要幾十元,即使加上實驗設備的損耗和人力成本,自己做也要便宜很多。”
對于自己的這個實驗室,湯姆森也感到自豪。“這是我在過去近20年里建立的第三個實驗室,也是最好的一個,因為我博士畢業后30多年在學術、工業和實驗室領域所積累的經驗都傾注在這里了,既包括實驗室的運行,也包括人才的培養。”湯姆森充滿信心地說,“這個實驗室的研究能力和領域,以及人才的儲備都在逐步發展中,未來肯定會取得不俗的成果。”
湯姆森手下有兩個印度籍和4個中國研究人員,他們都具備相關專業的碩士以上學歷,“這些孩子都和我的女兒年紀相仿,所以我和他們溝通起來絲毫沒有障礙。”由于他不懂中文,久而久之,中國研究人員的英語口語和寫作能力都有了顯著的提高,“這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人才素養的提升。”
但是,湯姆森也有他的煩惱,那就是人才流失。事實上,他在前兩年曾經培養過3個研究人員,但他們最后都離開了昆山,有些人是因為家庭原因,也有的人是因為別的公司給出了更優厚的待遇。“我能夠理解他們的選擇,也為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而感到高興,但這個問題還是讓我沮喪,因為培養人才本身就是一件耗時耗力的事情。”湯姆森惋惜地說,一個實驗人才起碼要學習3到5年才能成熟到可以獨當一面的程度,“但是這些年輕人只學了一兩年就走了,真的很可惜。”
有家不回只因一份責任
“這不只是一份工作,不只是賺錢的問題,也是一份責任。”正是出于責任心,湯姆森在昆山工作和生活期間很少離開昆山去游覽中國的大好河山,唯一一次長途旅行是去游黃山,當時是公司組織的一次集體活動。盡管公司每年都提供他回印度的機票錢,他也不回印度與家人團聚,因為他必須時刻關注實驗室的情況,還要照顧家里養的花花草草。每年,他的女兒都會來昆山看望他,跟他住上十天半個月,但大部分時間也是宅在家里,因為父親離不開工作。
花草可以說是湯姆森為數不多的愛好之一。在公司為他提供的公寓客廳里,擺滿了他養的各種植物。由于養得太多,一些花草還被他搬到了樓道里和鄰居家門口,好在鄰居非常和善,樂意為他提供便利。
湯姆森很喜歡在昆山的生活。有空的時候,他喜歡一個人在昆山市里四處逛逛。剛來的幾個月,實驗室的同事一有空就會帶他出去熟悉環境,當他熟悉了道路和公共交通后,他就開始獨自行動。大部分時候都很順利,但有一天晚上他迷路了。不過這也難不倒他,他攔下一輛出租車,把同事李莉的名片給司機看,讓對方把他送到上面印著的公司地址,然后再從公司自己回家。這座城市的安全也讓他很滿意,晚上女性獨自一人走在街上也沒問題,這在印度是很少見的。湯姆森說,語言障礙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問題,昆山是個和諧的地方,他經常看到老人帶著小孩在公園散步,雖然他們不會說英語,但也會友好地對他笑笑,或者說聲“哈嘍”跟他打招呼。
他喜歡所有的中國美食,和同事們吃飯的時候,幾乎什么都吃。外出聚餐也不會刻意選擇印度餐廳。“既然來到了中國,就要好好地享受地道的中國美食。”但他也很喜歡自己做菜,這是他經常去菜市場的原因之一。“買菜的時候,討價還價基本是靠手勢完成的,有時候,我會直接打開錢包,讓小販們自己拿錢,自己找錢。”有時候,湯姆森還會把自己做的菜帶去公司,給同事們品嘗。他最常做的菜是各種口味的魚,這大概跟他的專業有關,他能分辨出各種魚的肉質與口味的細微差別,儼然一個美食家。(蘇州市外專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