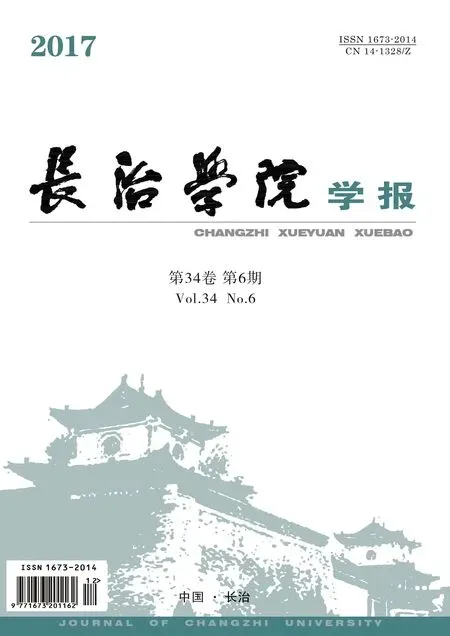論當代女性油畫家花卉創作主題的內涵
趙 敏
(長治學院 美術系,山西 長治 046011)
無論是在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當中,花卉都是美好生命的象征物,故而花卉在很早的時代就作為描繪對象進入了畫家的視野。在中國的當代畫壇上就出現了一大批以花卉為創作題材的女畫家。人們常說,女人如花,作為如花女人的女畫家在創作花卉主題的油畫作品時,如何將自身對于生命、對于世界、對于時空的感悟傾注到了作品當中?花卉的形象上面又體現了什么樣的生命情懷?這樣的探索有具有什么樣的意義?這是非常值得注意和探討的問題。
一、融匯中西創作技法,表現中國傳統
西洋繪畫的風格與創作技法傳入我國之后,就同我國傳統繪畫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手法實現了有機的對接與融合。比如在西洋繪畫史上占據重要地位的“印象派”,因其高度重視依靠色彩和光線的明暗來展現創作瞬間的印象,故而無意于勾描所畫對象的細節輪廓。[1]這同我國傳統繪畫的“潑墨”、“寫意”等創作手法有著內在的相通之處——兩者都是高度重視表達主觀意念而必然忽略對于細節輪廓的刻繪。因此,“印象派”同我國傳統的水墨畫法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相通之處,具備相互融合的基礎。
當代女畫家歐洋創作的《秋池》就將上述這兩種繪畫體系的創作手法有機地融合起來,展現了一幅色彩絢爛而富于流動感的秋日滿塘殘荷畫面。在作品中,奔放到似乎隨意涂敷的紅、綠、藍、紫等諸多色彩彌漫在整幅畫面中,令人一看便知畫家是運用了“印象派”的畫法來創作的。然而蒼蒼的荷葉卻是采用傳統的“潑墨”法來塑造,而且還使用了“印象派”畫法的色彩敷染法,用暗紅的色彩填充了潑墨畫法所造就的“飛白”部分。那細弱的葉梗則是用“積墨”法來精心繪制,更是恰如其分地表現了一種殘敗之感。至于即將開敗的花朵,則被安排到了亮光的背景處。而且活用“積墨”的手法來敷設粉白的顏料,塑造了在瑟瑟秋風中因柔弱而即將搖落的荷花形象。縱觀畫面,畫家實際上是借鑒了中國傳統繪畫“以白代形”的手法,把用粉白色敷設的瑟瑟秋風中柔弱的荷花放到了印象畫法所強調的亮光背景中,借助同色調及明亮肌理的疊加造成了虛化的表現效果,得以從生命精神的深層次上描繪了荷花因時間規律而殘敗的虛弱無力乃至無奈之感。而用潑墨、積墨等畫法塑造的荷葉、荷梗浸染在紅、綠、藍、紫等諸多色彩彌漫所營造的池塘水波及環境背景中,則造成了一種內在的動感,也就是水波和時光對殘荷的共同侵迫感。如此則畫家在有機融匯中西畫法的基礎上就把靜態畫面畫“活”了,畫出了一種“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綠波間”的氣韻感和意境感,而且傳神地表現了“還與韶光共憔悴”的意態感。
當代女性畫家通過有機互滲、融會貫通地運用中西繪畫技法[2],能夠“以靜見動”地營造富有意蘊的花卉物象,并傳達出類似中國古典詩詞一般的意境感,從而表現出中國傳統繪畫“詩畫相通”的意境與神韻。
二、人花互喻,彰顯生命意識
中國的文化,向來就有用美好的花卉意象來比喻女性青春年華及美好姿容的傳統。比如唐代詩人杜牧的《贈別》詩:“娉娉裊裊十三余 豆蔻梢頭二月初”。這就是用含苞欲放的豆蔻花蕾來比喻自己所欣賞的十三歲青春少女。既然美女如花,那么花又何嘗不如美女?因此我國文化又有“以人喻花”的習慣。比如北宋詩人蘇軾在《海棠》詩中寫道:“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燒高燭照紅妝”。這里的海棠花儼然就是當作一位美女來描繪的。所以通過以花喻人、以人喻花、人花互喻來展現一種對于美好生命形態的尊重乃至熱愛之情懷,就成為中國傳統文化在用文字或線條等外在形式語言描繪花兒時的基本指導思想。女畫家蔡錦的《美人蕉》,就是用現代油畫的藝術語言在別開生面地詮釋這種傳統藝術思想。
在《美人蕉》中,畫家采用同色疊加的手法,用粘稠的暗紅油彩顏料堆積出了一種具有凝固般質感的肌理——同色疊加部分變得更暗的色調細膩地襯托出了殘敗的美人蕉綻放過后花瓣上及花瓣邊緣的褶皺,但這褶皺似乎又蘊含著一種扭擰的內在張力。而在條條褶皺之外,稍微明朗一點的大片暗紅底色用來表現美人蕉花瓣上較為舒展的部分,它們如同宣泄一般鋪滿了整個畫面,給人帶來一種視角上的沖擊感和壓迫感。然而在這暗紅的皺褶及底色當中還出現了對稱的彩鳳圖案及散落的各種花朵圖案,這就提示觀眾:畫面上所畫的美人蕉實際上就是女子的嫁衣。那粘稠、扭擰而又飽含內在張力的花之褶皺實際上就是嫁衣的褶皺,它暗示著盡管美人蕉和美人都無法逃脫時光的擺布,盡管她們都曾用生命的精神來努力抗爭無情的時間規律,但仍難免于花謝紅顏老的宿命。因此,殘敗的美人蕉象征了美人終將殘敗的嫁衣,更象征了她終將遲暮的青春。所以這幅《美人蕉》是用現代油畫充滿張力的突兀藝術語言表達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少女傷春”的生命主題,而且更突顯了一種基于時光無情的生命焦慮感。
三、運用色彩“語言”,表現個體情緒
對于中國和西方的古典繪畫來說,色彩似乎都是輔助性的——宋代以來水墨畫成為中國繪畫的主流,而西方自18世紀興起的新古典主義繪畫則將色彩視為素描構圖的附屬物,不認為其具有獨立的表現力。而進入19世紀以后,隨著光學技術的發展以及日本浮世繪等東方繪畫的傳入,使得西方畫家認識到:繪畫表現世界的方式并不局限于以素描為基礎來創作富有雕塑感的客觀寫實油畫;相反用光影和色彩來表現個體的意愿、情緒、心境,進而為畫布上的世界涂敷一層主觀的色澤,則不失為更加自由且更具吸引力的表現手法。所以從德拉克洛瓦開始,西方畫家開始越來越注重將色彩及光影用作繪畫的主要表現手段,由此催生了印象派、新印象派、后印象派等聯接古典和現代美術的新興繪畫流派。
近代以來,隨著西洋油畫及西方現代美術被引入我國,色彩也逐漸被提升為中國畫壇的一種主要表現手段[3]。當代一些中國女性畫家就極善于嫻熟地運用色彩來創作花卉主題作品,在描摹花卉美態的同時傳達出個性化的審美見解及東方式的審美理想。比如閆平的《朋友來了》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之作。這幅畫雖名為《朋友來了》,但畫面中并無“朋友”,而只有一束瓶花。所以乍看來,這幅《朋友來了》就像是一幅靜物寫生。但實際上這并非簡單的油畫習作,而是一幅融匯了西方印象派“色彩分割”技法以及中國傳統繪畫“積墨”技法,具有豐富審美內涵的經典花卉主題作品。
同閆平的其它畫作類似,這幅《朋友來了》在構圖上也采用了突出主題花卉對象的手法。即采用平面化的構圖來展示必要的映襯背景,同時又采用立體的構圖方式來塑造花卉本身,這就有效地凸顯了主題對象,無形中增強了作品的審美張力。值得注意的是,色彩的對比并置在構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即:平面化的背景基本采用藍色調,而作為主題對象的瓶花則主要敷設了紅、橙、黃等暖色,通過冷暖對比達到了將觀眾目光聚焦于瓶花之上的目的。而且,在瓶花內部也自然而然地存在著構圖方面的色彩對比。常言道紅花還需綠葉襯,所以瓶花這個對象內部又自然地存在著紅、橙、黃等暖色花朵與綠色枝葉間的冷暖色調對比。這本是自然之理,并不稀奇。但真正體現畫家敏銳觀察力的還在于同屬冷色調的各枝葉之間以及同屬暖色調的花朵之間的色彩對比。之所以能體現這種細致的色調對比,還要歸功于花瓶。花瓶中明亮的白色屬于光源色,表明環境中的光線主要是從前方照射到瓶花上的。因此,畫家用草綠色來表現前景中的枝葉,用黑綠色來表現最靠近畫面背景的那一層枝葉,而處于這兩層之間的枝葉則用暗綠色來表現。其中草綠色屬于光源色,而暗綠及黑綠則屬于反光色。這樣一來,由于枝葉和花朵間的互相遮蔽所造成的光線在不同層次景深中復雜的反光現象則被表現得清清楚楚了。這也表明畫家嫻熟地貫徹運用了德拉克洛瓦提出的“互補色”與“反光色”理論,依靠色彩互補對比巧妙地造就了畫面不同層次的明暗調子,強化了主題對象的立體感。
作為陪襯的綠色枝葉展現了作者高超的補色技巧,而作為畫面主體的花團則更是不遑多讓。同枝葉相似,那錦簇的花團也運用了細致的補色技法來表現——從位于畫面前景中心的暖紅色花朵到后方及側后方的橙色花朵、橙黃色花朵,再到最后方靠近背景處的紫色花朵,畫家用同樣細致的補色生動地展現了自然光影在不同層次景深中的投射與反射現象。然而畫家在繪制花團時還運用了比補色法更為工細的手法——印象派繪畫的“色彩分割法”。印象畫派習慣于將色彩細化分解成很小的色塊——色點,然后用小筆觸不厭其煩地細致敷設不同的純色點,構成色彩的“線”和“面”。在欣賞畫作時,觀眾的視覺生理特點就會在無形中將色彩的“點”、“線”、“面”有機地混合成相對統一的色調,同時體會到色彩從“點”、“線”到“面”的發展所蘊含的內在動感,從而賦予畫面奇異的韻律感。這種手法在莫奈的《阿爾讓特伊大橋》等印象派名作中得到了傳神的運用,而在《大碗島的星期天下午》等新印象派畫作中發展到了極致。而閆平在這幅《朋友來了》當中也借鑒了“色彩分割法”,不過她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色點,而是色彩的“線”和“面”。比如位于畫面前景中心的那朵暖紅色的花,它的眾多花瓣就分別是由鮮紅、赭紅、橙色、淺褐、紫紅、黑紅等多種色彩構成,分別表現了花朵在光照下的迎光面、各種反光面及陰影帶。但是雖然同樣使用小筆觸,閆平所畫的花朵中卻沒有過多地表現出印象派常用的細小純色塊,而是用色線勾勒了邊界不太清晰的色彩“面”,眾多的花瓣就是由這些色彩“面”構成的。如果細加觀察還會發現,之所以能夠造就這些色彩“面”,還在于畫家借鑒并活用了中國傳統繪畫的“積墨”技法來“積色”,才造成了隱約的色線以及邊界不太清晰的眾多色彩“面”。化用“積墨”法造就的這些色線及相對模糊的色彩“面”,使得“色彩分割”所造就的調子和層次過渡更為自然,韻律感也變得更加協調。這樣一來,各種色彩得以在自然過渡中相互呼應,使得整幅畫面在暖色中呈現出一種生機勃勃的內在精神。這種內在精神,正象征著畫家的心境,即“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欣喜之感。因此,這幅《朋友來了》綜合運用了西方繪畫的補色、色彩分割以及我國傳統繪畫的“積墨”技法,用花卉主題形象象征性地表現了作者的心境,雖未畫朋友,卻表現了迎接朋友的喜悅之情。非常恰切地表現出了我國傳統美學“含蓄傳神”的審美旨趣。
綜上所述,當代女性油畫家所創作的花卉主題作品,都注重采用西洋繪畫的具體技法、同時有機融合我國傳統繪畫的相應手法來營造或富有動感、或富有張力的物象,在這動感和張力背后卻能夠引發讀者通過豐富的想象和聯想來感悟花卉物象背后所蘊含的意境之美以及生命意識。她們在“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思維指導下,以獨特的視角,借助特色化的花卉物象傳達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和底蘊。這無疑也指明了當代中國花卉主題油畫創作“民族化”、“本土化”的探索方向。
[1]徐剛.中西油畫花卉的審美觀[J].遼寧.沈陽:美苑,2004,(4):78-79.
[2]楊佳.油畫花卉中的東方情結[D].北京:大眾文藝,2010,(22):52-54.
[3]劉美雙.淺析閆平繪畫藝術的女性特質[J].福建夷山:武夷學院學報,2016,(4):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