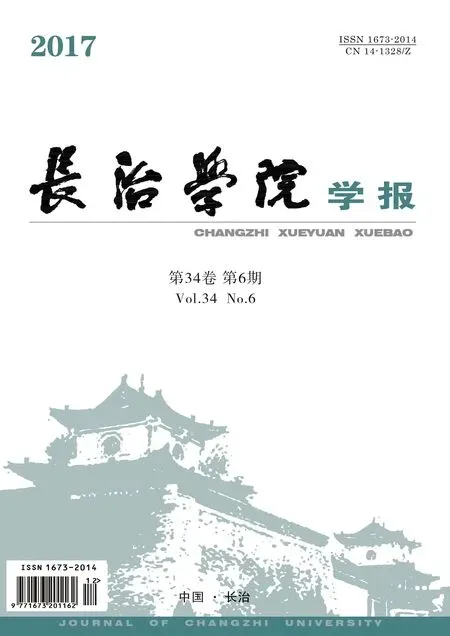生態女性主義視閾下《萬物的簽名》
王 惠
(呂梁學院 中文系,山西 呂梁 033300)
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這一名詞是由法國女學者弗朗索瓦·德·奧波妮(Francoi se d'Eaubonne)于20世紀70年代在其著作《女性或死亡》中首次提出的[1]15。弗朗瓦·德·奧波妮在該書中把生態思想和女權思想結合在一起,揭示了自然和女性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天然的聯系。此后,生態女性主義作為一種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哲學思潮在西方逐漸傳播蔓延,并隨著環境保護運動的壯大和綠色革命的興起而日益發展。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從自然、環境、性別等多重視角進行文學批評,把文學批評放在性別歧視和生態危機的語境下,與性別、自然、文學、文化等因素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反對物種歧視和性別歧視,質疑和解構西方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對立觀念,批判人類中心主義和父權制中心文化,其目的是通過文學研究對文學創作、進而對整個人類文化進行重新審視和批判,改變自然和女性的“他者”和“邊緣化”地位。喚醒人們的生態整體意識和男女平等意識,建立一個男女平等、兩性和諧、物種平等、人類社會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協調發展的社會。
《萬物的簽名》作者伊麗莎白·吉爾伯特為我們冷靜地講述了一位女植物學家一生的愛與經歷,作品主人公阿爾瑪有著科學智慧的頭腦,理性而冷靜的心態。天賦異稟的她,借由對植物的探索與認識,逐步認識到推動生命發展的基本機制。本文用生態女性主義理論分析阿爾瑪與女性和自然的關系,她從理性到經歷過戀愛、婚姻失敗后,個體得到情感的回歸。最終得到大自然的饋贈,提出了“進化論”的學說。
一、理性的女人
作品主人公阿爾瑪是一個理性的女人,她從長相到性格完全像個男人,“她長得一頭棕色的頭發,身材高大,像個男人”,她有一顆“百科全書式的大腦袋”。在阿爾瑪的世界里,科學與理性統治著一切,這得益于出身名門母親的教導,她的母親從孩子降生就祈求女兒“長大后健康、明理、懂事,永遠不和濃妝艷抹的婦女結成團體,或被低俗的故事逗得發笑,或和漫不經心的男人坐在賭桌旁,或讀法國小說,或行為舉止像野蠻的印第安人,或以任何方式成為最大的家門恥辱……”[2]1她親自教女兒讀書認字,學習各種語言,母親告訴女兒生活要有尊嚴。什么東西都不如尊嚴重要,身為女人,你的道德意識永遠要比男人高尚。她相信對感官保持無動于衷,是一種與身俱來的尊嚴,她相信尊嚴就是對感官的淡漠。生為女人,在阿爾瑪的身上絲毫沒有女人的細膩、溫柔與敏感。在母親刻板的教育之下,她的理智和情感嚴重失衡。
而她的妹妹卻與阿爾瑪形成了鮮明對照,妹妹是個美人,在妹妹面前阿爾瑪第一次感到自卑,“她纖細柔弱,而阿爾瑪則是大塊頭。她的頭發像是用金白色絲緞紡出來的,阿爾瑪的頭發則是鐵銹的色澤與紋理——而且更糟的是朝著四面八方生長,除了朝下。普魯絲登的鼻子是小花,阿爾瑪的鼻子則是一顆生長的番薯。從頭到腳,一個最凄慘的敘述。”[2]60阿爾瑪甚至自己也懷疑,“怎么可能有比普魯登絲的臉更美,更令人不安的東西?如果像她母親經常講的那樣,美的確會干擾精確。那普魯絲登呢,很可能是世界上最不精確,最干擾人心的東西”[2]69。阿爾瑪最擅長的是談論自己的觀點,大膽自信,她熱愛語言訓練、邏輯、考試、公式、定理。而類似女孩子應該掌握的功課舞蹈、音樂,她卻望而止步。姐妹倆人彼此都很禮貌,但是一點都不親密。就像兩條互不相交的平行線,各自在自身的缺陷和困擾中前進。
隨著年齡的增長,她愛上了經常出入白畝莊園的出版社名人霍克斯,但霍克斯只是把自己當作事業上的合作伙伴,一起探討交流植物學的朋友。她不懂得怎么取悅男人,除了寫一篇又一篇晦澀難懂的植物學論文之外。就連最疼愛她的父親也對女兒的婚姻深感惋惜。用男性的眼光來看,女人要永遠漂亮,即使是被父親親切地稱之為“小梅”的阿爾瑪,作為父親的他也無能為力。作為“他者”的女性被要求漂亮,溫柔,體貼。這些在阿爾瑪身上沒有一點能夠體現出來。
二、情感的回歸
作為一位有正常情感需求的女性,阿爾瑪的內心深處一直埋藏著情感的火種,她渴望愛,渴望人們的理解,渴望與人和諧相處,向往平靜美好的家庭生活。她是群星中一顆最為耀眼、奪目的彗星,雖然光芒閃耀,但卻異常孤獨。而她最艱巨的任務,卻是讓她親近的人理解她、愛她。生態女性主義就是要解構以男性為中心的體系,以理性為中心的社會觀念,倡導男性與女性的平等。激勵女性去勇敢地開創自我,走出理性與感性割裂的怪圈,走出男性與女性不平等的現實,實現女性與自我,與男性之間的和諧。
早在阿爾瑪童年,她一個人感到孤獨、害怕的時候,她總是會去找女仆漢娜克尋求情感和心靈的慰藉。因為“阿爾瑪的母親是個多才多藝的女人,可安慰的才能不在其中”。生活中一次次的經歷與痛苦,讓她在與漢娜克的傾訴中找到了生活的力量與勇氣。阿爾瑪五十多歲時,和一位版畫家結婚,她以為找到了自己的真愛,沒想到閃電般結婚后,阿爾瑪發現丈夫想要的是“白色的婚姻”,(也就是無性婚姻)。對于阿爾瑪來說,這無異于晴天霹靂。
婚姻失敗,緊接著父親去世,她一如既往去找漢娜克傾訴,漢娜克卻告訴了她一個驚人的秘密。原來妹妹普魯登絲愛的人也是霍克斯。為了成全姐姐,她放棄了自己的愛情,和她不愛的家庭教師結了婚。隨后霍克斯在求愛遭拒后,娶了阿爾瑪精神有些失常的朋友芮塔。然而霍克斯和她妹妹各自的婚姻都是不幸福的,他們三個的命運因為阿爾瑪或直接或間接地發生了偏離。洞悉事情的全部真相之后,阿爾瑪找到妹妹,把父親的全部財產都留給她,兩個逐漸老去的女人久久地站在那里,默默地擁抱在一起。這是幾十年來姐妹兩人唯一一次飽含情感的擁抱。作品中女性之間的溫情稱之為“姐妹情誼”。當父母雙亡,年僅10歲的普魯登斯被警員和一群男人圍住時,阿爾瑪的母親和女仆漢娜克保護了這個女孩,她們兩個緊緊抓住小女孩,作者寫道,“這不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決定,也不是籠罩著溫暖母愛的慈善之舉。不,這是一種直覺的行為,來自女性對世界運作方式的一種深刻無言的認知”[2]58。這是女人深植于心的保護意識,是女性對自己同類的憐憫。
安頓好妹妹之后,她獨自前往塔希提尋找亡夫的蹤跡。在環境惡劣的小島上,阿爾瑪跟隨丈夫生前的同性好友“明早”,見到了生前他為自己“培育”的苔蘚王國,面對滿眼皆是綠色的苔蘚世界,她喜極而泣。在綠色的世界中,阿爾瑪完成了和“明早”肉體的交合。在孤島上找到了自己情感的寄托與愛的歸宿,實現了身、心、靈的和諧統一,阿爾瑪的理智與情感終于達到完美的契合,最終在母親的故鄉荷蘭安詳地度過晚年。
三、自然的饋贈
阿爾瑪的父親是費城首富,他擁有一座資源極為豐富的植物莊園,這里有各類動物化石標本,參天的樹木、大片的綠地,野生小動物兔子、狐貍和鹿,種類繁多的昆蟲,和溫室里培植的眾多果木。阿爾瑪的父母鼓勵她在林地上任意游蕩,了解自然界。她搜集甲蟲,蜘蛛和飛蛾。她觀察大蛇的活動,收養毛毛蟲。她了解花朵內層的結構,觀察花朵綻放的時間,收集植物標本,她對發生在大自然中的每一件事都驚奇不已。童年時期與自然的親密接觸,加上天賦秉異,十幾歲的她就開始發表關于植物學的論文。正如生態女性主義評論家所說“所有生命都密切相關,是巨大生命之網的一部分,都應該被我們考慮在內”。[3]生態女性主義者認為,婦女和大自然有深沉的關系,密切的聯系。“婦女與大自然共語……她能聆聽來自地球深處的聲音……微風在她的耳邊吹拂,樹向她低語呢喃”。[4]175正如“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阿爾瑪的研究對象是苔蘚。大自然不僅僅是任阿爾瑪肆意探索的地方,也是安慰她的精神家園。在她遇到挫敗的時候,在她傷心痛苦的時候,每次與苔蘚的親密接觸中,找到了人生的力量與使命。作品中多次寫到她對苔蘚的潛心研究,與苔蘚的密切接觸。“她有苔蘚可做,有苔蘚可研究……”,“阿爾瑪把手指埋入短短的綠色軟毛中,感覺到一種突如其來的歡樂的期待,”[2]140她從對苔蘚的研究中發現了人生的樂趣與大自然的奧秘。
在環境惡劣、荒涼的原始小島塔希提上,她幾乎失去一切賴以生存的基本物資,憑著她的堅強勇敢,最后與塔希提的島民一樣粗糲并快樂地生活在這里,她遇到的一草一木都是上帝饋贈給她的簽名。她應邀參加了島民舉辦的“哈努拉普”比賽,打敗了強悍的女對手,最終獲得勝利,阿爾瑪體會到生命的原始力量,“她從海里大步走出來,好似誕生于大海”。[2]387在大自然的懷抱中,她又一次堅強地站了起來,這也是阿爾瑪一直要尋找的生命的答案,最終她發現了大自然最基本的奧秘。
以苔蘚為研究對象,成為與達爾文先后得出“進化論”的唯一一位女性學者。“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她知道這個世界顯然劃分為生命英勇而戰的人,和投降死去的人。這一事實是大自然的基本機制,是一切事物,一切變異背后的驅動力,也是對整個世界的詮釋。這一事實不僅適用于人類的生命,也適用于地球上的每一個生命實體,從最大的、最高級的動物到最卑微、最低等的生物。這是大自然對她的饋贈。進化論的提出基于這樣的學術背景,在浩瀚無邊的自然界,人類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類物種。作者借阿爾瑪之口提到,“我相信,當伽利略宣告我們不住在宇宙中心時。肯定對人類的自我評價造成了可怕的打擊。就像當達爾文宣告,我們不是由上帝在某個神奇時刻創作而成時,對世人不啻當頭一棒。我相信這使人類覺得自己微不足道……”[2]442。迎合了生態女性主義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解構。提倡改變自然的“他者”與“邊緣化”的地位。
《萬物的簽名》體現了作者的生態女性意識,展現了女性的聰明才智,表明女性不再處于“他者”的地位,女性曾經為社會、為人類做出的巨大貢獻。正如作者在小說尾序中寫到:“請放心,親愛的朋友,許多出色偉大的藝術,都是通過女性的了解和細膩思維,無論是反映在文字中的認知推斷,或是表現在體力勞動中的藝術,我能給您舉出大量的例子”。(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女性之城》一四零五年)[2]446。
生態女性主義批評從環境和性別的雙重視角對作品進行解讀,表明“自然”和“女性”終于從被人們遺忘的角落重新走向前臺。正如生態批評家帕特里克·墨菲認為“生態學和女性主義在保留差異的前提下聯合起來,使之朝拆解男性、人類中心主義的方向努力……”[5]20。從“缺席”變為“在場”,表明文學研究的觸角不僅伸向人類社會的另一半,更重要的是開始伸向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界。作品批判了人類中心、男性中心的思想觀念,主張女性與女性之間,女性與男性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處。正如《紐約時報》對《萬物的簽名》的評價,“作者伊麗莎白·吉爾伯特是向大自然的智慧致敬,吉爾伯特以她特有的耐性,揭示這個世界最美好的真相”。
[1]Gates Barbara T.“A Root of Eco feminism”[A].in Gaard,Gret a&Murphy Pat rick D.(eds)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 [C] .Urbana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
[2]伊麗莎白·吉爾伯特.萬物的簽名[M].何佩樺,譯.中信出版社,2015.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論文學與藝術,李俏梅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9.
[4]納什.大自然的權利[M].青島出版社1999.
[5]格雷塔·戈德.生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理論、闡釋和教學法[M].蔣林,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