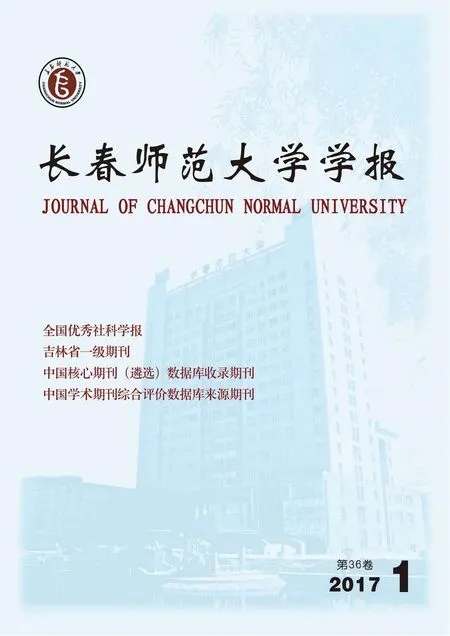日英在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問題上的對立
——從棉業競爭角度的觀察
王小歐
(長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61)
日英在1935年中國幣制改革問題上的對立
——從棉業競爭角度的觀察
王小歐
(長春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吉林 長春 130061)
1935年,中國政府面對國內危機加重、國際借款無果的困難局面,毅然決定進行幣制改革。對此,日英兩國從各自利益出發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本文試從日英棉業競爭的角度對日英在此事件中的對立態度進行分析,從而更深入地理解那個時期的日英關系。
中國;幣制改革;日英對立;棉業競爭
20世紀30年代初,經濟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帝國主義國家在獎勵出口以重獲商品市場的同時,高筑關稅壁壘,形成了不同的經濟集團。為了增加金融資本,帝國主義國家一方面鞏固他們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試圖掌握殖民地、半殖民地諸國或落后獨立國家的貨幣權,貨幣戰隨之展開。與貿易戰、關稅戰、匯兌傾銷戰一樣,貨幣戰以掠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大眾經濟為終極目標[1]40。擁有廣闊領土的半殖民地國家——中國,自然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們進行貨幣戰的最佳戰場之一。圍繞1935年中國的幣制改革,日、英、美等國均表現出積極的參與意識,其中日英態度截然不同。
一、1935年中國的幣制改革與日英對立
自兩漢以來,銀子一直是中國的主要流通貨幣,因以兩為單位,故稱為銀兩。1910年清政府頒布《幣制則例》,政府鑄造銀元為合法貨幣,中國遂開始實行銀本位制。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宣告成立。3月,南京臨時政府公布了《幣制綱要》,規定以銀元為貨幣單位。1933年3月8日,國民政府頒布《銀本位幣鑄造條例》,規定銀本位幣定名為元,重量為26.6971克,成色為銀88%、銅12%,即合純銀23.493448克。1933年3月10日,國民政府財政部發布《廢兩改元令》,廢用銀兩,改用銀元,規定所有公私款項收付、契約票據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銀幣,不得再用銀兩;持有銀兩者可由中央造幣廠代鑄銀幣,或在中央、中國、交通3銀行兌換銀幣。盡管政府已經明文規定廢兩改元,但中國的貨幣依然十分混亂,各地的銀幣成色各異且不能通價兌換。其中,銀元有“袁頭”“孫頭”,銀兩有銀角子、銀毫子等,流通的紙幣有銀元券、私票(偏僻城鄉)等。同年,美國出臺一系列關于白銀的政策,客觀上加劇了中國幣制的混亂程度。中國開始出現貨幣信用危機,全國各地的銀行、票號紛紛倒閉,中國市場上流通的白銀大大減少,工商業企業身處風雨飄搖之中。
1935年11月3日,面對國內危機加重、國際借款無果的困難局面,中國政府毅然決定進行幣制改革。主要內容為:自1935年11月4日起,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三行所發之鈔票,定為法幣,并集中發行,其他各銀行所發鈔票仍準流通,但應逐漸收回,而代以中央銀行鈔票,以后各行不得續發新鈔票,所有已印未發之新鈔,應交存中央銀行;所有以銀幣單位訂立之債務,應準照面額,于到期日以法幣清償之;所有銀幣之持有人,應即將其繳存政府,照面額換領法幣;為使國幣對外匯價按照現行價格穩定起見,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應即對外匯進行無限制之購售[2]176。這意味著改革后,中國將實行白銀國有,禁止白銀流通,法幣成為中國流通的貨幣。法幣本身沒有法定的含金量,它的價值由對外匯率來體現。法幣匯價1元等于1先令2.5便士,并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根據幣制改革的內容,法幣直接與英鎊掛鉤,后又迫于美國壓力與美元掛鉤。這樣,英美加強了對中國金融的把持。
對于1935年中國在幣制改革中將法幣直接與英鎊和美元掛鉤的舉措,日英兩國表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態度。英國以其實際行動進行了有力的配合,在中國宣布幣制改革的當天就命令所有在華的英國銀行、英國人和集團結束現銀支付,接受南京政府的相關法令。英國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等無條件將所存白銀交與南京政府以兌換法幣。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則在11月8日就中國幣制改革發表談話時表示“斷然反對”。他認為:“此次改革,事先既缺乏各種準備,及改革實行之人材,且未得各國之諒解,則遲早必發生破綻,當無疑義”,“日本不能默視鄰邦民眾之被騙入滅亡之淵也,因此,日本政府對此次改革除明列反對理由,明白宣明態度于中外之外,確認中止改革案乃救中國之唯一途徑”[3]304-305。11月9日,日本陸軍部公報進一步指出:“日本,作為遠東的一種穩定勢力,不能忽視大不列顛企圖把一個半殖民地的中國置于英國資本統制下的任何嘗試”[2]160。日軍中央部也就中國幣制改革發表聲明,宣稱幣制改革是“忽視具有安定東亞勢力之日本,擾亂東洋和平之新政策,日本帝國將斷乎排擊之”[3]308。日本極盡所能地阻攔和破壞中國的幣制改革,在華日本銀行拒絕將其存銀引渡給中國三大銀行,并發表了停止從平津向南方送銀的強硬意見。
二、從棉業競爭角度觀察日英對立
棉紡織工業對于日、英兩國來說都曾是支柱性產業之一。英國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最早完成了工業革命,其棉紡織工業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傲居世界首位,占有世界棉業市場大部分的份額。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改變了這一格局,英國在棉業市場上的優勢地位受到了來自日本的挑戰。日本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直至20世紀初才完成第一次產業革命,棉業起步晚,但發展迅速。20年間日本從英國棉制品的消費國逐漸變成其強有力的競爭者,在印度、中國等棉業市場上所取得的“優異成績”令英國瞠目。
“英國的棉織品專靠出口來維持”,對英國棉業來說,中國是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出口市場。“如果以1913年的價值為基年來看1929年英國輸華貨物的價值,則英對中國市場貿易量減少的程度極為驚人,減少的數目達30%以上”,而減少的原因,“多半由于英國輸華棉織品的衰落”。1913年,英國對中國及香港的棉織物出口價值是日本的4倍,1930年僅占日本的1/6;1913年,中國輸入的“本色市布”來自英國者不下85%,1930年,73%的“本色市布”來自日本[4]355;日本在華經營的工業中,“無論從工廠數還是從投資額的角度來看,棉業都是各行業中最多的(43家紡織工廠,資本249,890,000日圓)”[5]6。1913年,日本對華棉制品出口占其對華出口總額的33.9%,1926年上升至45%,1929年略有下降,但也占到了日本對華出口總額的37.4%,“棉貨的重要是顯而易見的”[4]453。1904—1913年,在中國的棉布進口中,英國布占進口總額的50—70%,日本僅占3—18%[6]177;至1931年,在中國華南、華中、華北、東北四個區域中,除華南地區外,英國在華的棉業勢力幾乎都已讓渡給日本[7]172,要想從正面奪回其在中國原有的棉業份額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棉貿易戰中敗下陣來的英國把希望寄托于貨幣戰的展開。如果能夠在中國幣制改革問題上占據主動,進而取得貨幣戰的勝利,英國或許可以挽回在中國棉業市場上的不利局面。
1935年中國的幣制改革將法幣與英鎊掛鉤,這將帶來中、英匯價的穩定,而匯價的穩定將刺激英國對華的棉貿易活動,更可以便利英國的對華棉業投資。中國只要成為英鎊集團中的一員,就可以像印度、澳大利亞等國一樣,追隨英國政府的貨幣政策,對英國的進出口棉貿易實行特惠關稅。英國或許可以憑借特惠關稅等中國幣制改革的副產品,在對日棉貿易爭奪戰中重整旗鼓,奪回被日本搶占的中國棉業市場上的部分份額。在印度棉業市場上,英國已經憑借關稅戰給日本以有力一擊。1933年4月,印度宣布廢棄1904年的日印通商條約;6月,印度宣布對英國棉制品征收25%的關稅,對英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棉織品征收75%的關稅。根據渥太華協定,印度的這兩個聲明必須要征得英國的認同方可發表,因此日本商界憤怒地認為“印度的關稅不表示印日沖突,而意味著英國工業和資本與日本工業和資本的沖突”[8]30,立刻表示:不買印棉以作抵制。1934年5月7日,英國進而宣布,英國所有的自治領和殖民地,根據1927-1931年棉制品進口量的平均值,對來自所有國家的棉制品課以基于此值25%的關稅。這種博弈讓日本感受到英國在經濟上的強大影響力。中國的幣制改革讓英國繼續與日本競爭于中國棉業市場再次成為可能,自然受到英國的大力支持。
對日本來說,中國幣制改革的結果將直接影響日本對中國棉業市場的占領,極大打擊日本在華的棉貿易優勢。多年來,日本之所以能夠在中國棉業市場上長驅直入,并成功地取代英國原有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日本財閥在華的投資網絡及由此而帶來的日本棉制品的低價格。日本在中國設立控制原料生產和交易的洋行以輔助日本在中國棉業市場上的進出口貿易,這些洋行在中國棉花商和日本工廠之間進行接洽交易,以日廠為后盾,任意控制棉花價格。還有的日籍棉花商直接從種植棉花的農民手中收購棉花,通過貸款給貧困的農民,來獲得棉花收購的特權,在收獲時壓低棉價進行強購。龐大和細致繁密的投資網絡使得日本在中國棉業市場上的勢力得以迅速發展,而要維持這個網絡的正常運轉,通貨的一致性是必要的。日本需要將日圓與中國的貨幣聯系起來。中國實行幣制改革后,日本在華投資網絡運作的各個環節都需要使用法幣,這將迫使日本必須將日圓與法幣聯系起來。而法幣本身沒有含金量,其價值是通過英鎊來體現的,這意味著日圓實際上是在與英鎊發生聯系。如此一來,日本對中國的貿易必然受到英國金融政策的影響,英國在試圖將中國拉入英鎊集團的同時,間接地起到了控制日本對華進出口貿易的作用,日本將失去對華棉業貿易的主導權,這與日本獨霸中國棉業市場的意圖是背道而馳的。而如果日本不響應中國的幣制改革,不將日本銀行的白銀兌換成法幣,日本在中國原有的棉業投資網絡將很難保持暢通,棉業利益的取得也將舉步維艱。此外,如果白銀國有化,華北將成為形同華南的經濟殖民地,這將對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經濟的侵略給予重大打擊,在占領的區域內沒有現銀,侵略的勝利將等于零[1]56。因此,日本與英國的態度截然相反,自始至終強烈反對中國的幣制改革,并在中國幣改實行后積極謀劃在華北實行獨立的幣制,試圖獨立于法幣之外,使華北的貨幣附庸于日圓。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在致東京參謀本部的密電中指出:“此次南京政府突然改革幣制,實行白銀國有,乃執行者只顧私人利益,罔恤民眾一般利益之舉動。華北經濟與日滿有不可分之關系,日本不能坐視華北經濟枯竭”,“且改革幣制之幕后含有英國勢力。英國勢力支配中國,將使我帝國(日本)多年之國是受到損害,東洋之永久和平發生危殆”[9]220,對英敵意溢于言表。
三、結語
盡管日英兩國在中國1935年幣制改革問題上是對立的,但在覬覦中國貨幣權問題上的態度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試圖將中國拉入他們的貨幣集團。為此,當中國出現貨幣危機時,日本大肆收購、擠兌現銀,然后走私出境,并堅決反對任何第三國向處于經濟危機中的中國提供援助,妄圖徹底破壞中國的金融貨幣體系,進而迫使中國淪為日圓集團的附庸;英國則向中國提出英鎊借款的建議,“名義上中國雖似仍以銀幣為本位,而實際上則實已成為英鎊之附庸”[2]174,“表面上擁護中國貨幣,可是,其真正的企圖卻是想使中國成為英國的經濟殖民地”[1]54。顯然,誰掌控了中國的貨幣權,誰在中國的利益就將實現最大化。日英在中國棉業市場上的
利益得失可以被看作是兩國在華整體利益得失的一個縮影,因此,從棉業競爭角度對兩國在華的貿易戰、貨幣戰進行觀察,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那個時代的日英關系。
[1]原勝.列強在華經濟斗爭[M].上海:不二書店,1937.
[2]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參事室.中華民國貨幣史資料:第二輯[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南開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中共黨史教研室.華北事變資料選編[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4]C.F.雷麥.外人在華投資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5]實業部.日本在華經濟勢力[M].上海:中華書局,1933.
[6]王子建.日本之棉紡織工業[M].北平:社會調查所,1933.
[7]嚴中平.中國棉紡織史稿[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5.
[8]Ann Trotter.Britain and East Asia1933-1937[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
[9]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上冊[M].臺北:綜合月刊社,1973.
2016-06-11
王小歐(1978- ),女,講師,博士,從事日本史和世界現代史研究。
K264
A
2095-7602(2017)01-008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