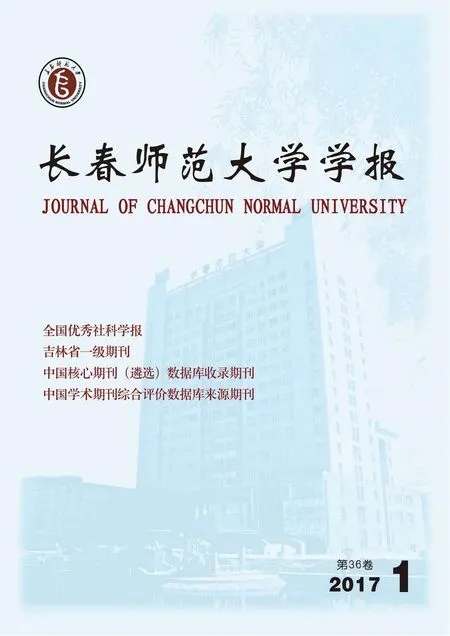語塊理論對西班牙語口譯教學的啟示
崔清夏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61)
語塊理論對西班牙語口譯教學的啟示
崔清夏
(安徽大學 外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061)
譯員口譯質量有賴于語塊的儲備和使用能力,但語塊理論在我國西班牙語口譯教學中的應用十分有限。本文闡釋語塊理論和口譯質量的相關性,分析目前語塊理論在外語教學中應用的情況,并針對西語口譯教學中存在的問題,探討語塊理論對西語口譯教學的指導意義。
語塊;西班牙語;口譯教學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飛速發展豐富了翻譯工作的內涵,并不斷拓寬其外延。中國翻譯協會副會長黃友義在第八屆亞太翻譯論壇上指出“小語種的需求將增長”,且“內容產業的爆炸式發展對語言服務將產生大量新需求”。但是,“真正的翻譯能力還有待于提高”[1]。社會新形勢給翻譯工作帶來更多挑戰,也向翻譯教學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國與西班牙語(以下簡稱“西語”)國家的交流日益頻繁,需要更多高質量的西語人才。目前,西語畢業生雖在規模上能滿足市場需求,但其質量尤其是口譯能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本文針對西語口譯教學中存在的問題,通過語塊理論和口譯質量相關性的闡釋,探討語塊理論對西語口譯教學的指導意義。
一、語塊、口譯和外語教學
(一)語塊理論和口譯質量的相關性
語塊的概念最早由Becher提出,他強調語言記憶儲存、輸出和使用的最小單位不是單個詞,而是固定或半固定模式化的板塊結構[2];Nattinger和DeCarrico認為語塊是約定俗成、搭配穩定、語用功能特定且在交際中頻繁使用的詞匯短語[3];Lewis將語塊定義為預制好的詞塊,無需臨時根據語法規則和詞語去當場構建詞句[4];Wray將語塊界定為“一串預制的連貫或不連貫的詞或其他意義單位,整體被儲存在記憶中,使用時無需語法生成和分析,可直接提取的詞語程式”[5]。不同研究者給語塊下的定義雖然不同,但其對語塊的認識基本相同。
關于語塊的分類,Nattinger和DeCarrico從結構上將其分為四類:(1)多詞語塊,如:de ninguna manera, se trata de;(2)習俗語語塊,如:Qué tal Feliz a o Nuevo!;(3)短語架構語塊,如:buenas (tardes, noches), como(quieras, quieran);(4)句子建構語塊,如:Es posible que …[3]。Lewis則同時把功能考慮進去,將語塊分成以下四類:(1)聚合詞,如:en primer lugar, por otro lado;(2)搭配詞,如:ir de viaje, poner notas;(3)慣用句型,如:Que yo sepa;(4)句子構架和引語,如:Primero…Al final[4]。
法國口譯研究專家Seleskovitch和Lederer指出,口譯中的表達無法進行語言學分析,也無法聽第二遍。對于口譯信息,要么立刻理解、記住,要么就錯過,這是口譯表達和交流的本質[6]。Gile認為譯員出色的語言信息記憶能力是口譯成功的必備條件之一[7]。如何提高語言信息記憶能力呢?有研究表明,口譯的記憶單位應該是“組塊”,組塊記憶對口譯的準確性有很大幫助。鮑曉英指出,在長句口譯中應以構成句子的不同成分為記憶的“組塊”;同時,把短時記憶的規律應用到口譯中將有助于實現口譯“信”的標準[8]。
語塊理論運用事物的組塊原理,將人們貯存于長時記憶的知識和短時記憶的信息加以組織,將較小的記憶材料,如某些固定或半固定短語組合成較大的記憶單元[9]。合理使用語塊可以減少譯員大腦認知和處理信息的負擔,提高口譯的速度和效率。在分秒必爭的口譯現場,譯員語塊的儲備和使用能力直接關乎口譯質量[10]。
(二)語塊理論在外語教學中的應用
在口譯中,利用語塊完成口譯工作是譯員下意識的操作。王建華指出,語塊教學策略對口譯的準確性提高有顯著影響;口譯常被視為“聽說讀寫譯”技能中最難掌握的一項,應及早教會學生以語塊為基礎進行學習和訓練[11]。
對于語塊理論在翻譯教學中的應用,目前國內既有理論研究,也有實證研究。理論研究指出語塊在外語教學中具有切實可行的優勢,可以幫助學生提高記憶力和信息處理的效率;實證研究指出語塊教學策略在口譯中有優勢,對學生口譯的準確性有正向的預測性。語塊對二語教學的積極意義主要體現在:大大增加二語習得者語言輸出的流利性和準確性;提高二語習得者語言的地道性和生動性;使學生獲得一定的交際策略能力,從而有效提高交際的得體性[12]。豐富語塊知識、提高語塊運用能力有助于解決二語學習者詞匯深度習得中的“高原現象”問題[13]。語塊教學有助于減輕學生的語言僵化程度,增強他們的語感,提高其語言運用能力[14]。
以上研究均為英語教學方面的語塊研究。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檢索“語塊+西班牙語翻譯”和“語塊+西班牙語口譯”,顯示結果均為零。可見,將語塊理論引入西語口譯教學尚處于摸索階段,也未有可借鑒的成熟教學模式。
二、西語口譯教學中的問題
(一)教學方法單一滯后
要想提高翻譯的熟練度,一些機械練習也是需要的。但對于這種機械練習,有些教師認為就是檢查學生背熟了多少句子。另外,學生語塊意識薄弱與教師對語塊認識不足有很大關系。大部分教師沒有經過系統的口譯訓練,口譯實戰經驗少,也沒有研究過口譯理論。在口譯課堂上,教師往往先朗讀或播放教材中的待譯資料,然后讓學生翻譯。練習過后,教師也沒有要求或和學生一起總結語對,教學方法單一滯后,效果不佳。
(二)口譯教材少
教材建設是專業建設與發展中不可忽視的部分。近年來我國與西語國家接觸交流日益頻繁,西班牙語迅速成為熱門專業。但相對于英語、日語、法語等,西語專業的教材還很匱乏。目前國內出版的西語口譯教材不多,在內容編排上多是分主題展開,適合語塊口譯教學的教材尚未問世。在與部分受訪學生的交流中,筆者發現,受到教材強調使用語法正確性的影響,學生易出現“啞巴西語”現象,即學生害怕口語出錯而不敢開口表達,而等到想發言的時候口語練習或討論已經結束。
(三)課程教學時間短
口譯課在西班牙語專業本科培養計劃中所占學分不多,大多只開設1~2學期,每學期36課時。這樣的課時安排無法保證口譯訓練的強度,真正意義上的口譯教學無從談起。
(四)學生口譯流利度不夠
根據筆者在口譯課堂上所做的記錄,大部分學生在口譯過程中經常出現猶豫不定、停頓時間長、單詞遺忘、語速慢、多次更正等現象,口語表達既不流利也不地道。比如,在一次中譯西的練習中,口譯材料出現了“有志者事竟成”,學生一時語塞,停頓時間超過10秒,最后給出的譯文是“El que tiene voluntad, la cosa inesperamente se triunfará.”但該譯文仍不準確。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兩個問題:(1)學生只憑頭腦機械反映,將聽到的詞一個個對應到西語中進行翻譯;(2)學生沒有語塊意識。“有志者事竟成”屬于習俗語語塊,已有對應的西語翻譯,即“Querer es poder.”學生沒有語塊意識,所以不知道使用已有對照的翻譯,導致口譯過程中停頓時間過長,而且翻譯結果不理想。另外,在西譯中的口譯練習上,也能發現語塊對口譯速度和準確性的影響。比如,材料中出現“Esta mujer está esperando el segundo hijo. La cigüe a va a venir en marzo del próximo a o.”停頓7秒后,學生譯成:“她正等待第二個孩子。白鸛明年三月來。”該譯文不符合原文的意思,原因就在于學生沒有語塊意識,不了解“la cigüe a va a venir”這個短語架構語塊是“分娩”的意思。不論是中譯西還是西譯中,如果學生有語塊意識,注意積累語塊,那么口譯能力應該會提高很快。
三、對策
西語口譯課程時數少,故編寫合適的口譯教材不失為提高學習效率的有效途徑。將分類后的語塊在每一類別下由易到難分組成列,以便學生記憶和使用語塊。口譯涉及的領域很廣,如經貿、商務、法律、社會、醫藥、政治,而且西班牙語在超過30個國家和地區被廣泛使用,有的國家地區在詞匯使用上還存在差別。編寫兼顧不同地域、不同領域專業需求的西語語塊教材無疑是一項大工程,但教材編寫出來后將會極大提高學生口譯學習的效率。
教師應加深對語塊的認識。在備課時將經常出現的話題或場景歸類,并將每一類中最實用的高頻語塊篩選出來,配以例句闡明用法,不僅可以用于課堂教學,也能作為語塊教材編寫的參考資料。
在口譯教學中,應培養學生的語塊意識,教給學生辨別語塊的方法,鼓勵他們積累語塊,要求他們在課外注意尋找語塊并記錄分類,使語塊習得條理化、系統化,逐步培養學生識別語塊的能力。
鑒于學生口譯實習機會有限,可以效仿吉拉里的“翻譯工作坊”培養模式,建立“口譯工作坊”。要求學生分組模擬工作場景,完成不同專題的口譯。小組經過討論、對比、確認語塊等方式獲得終稿,并將小組研討的過程記錄下來。教師對終稿和過程記錄點評答疑,并對語塊學習的重難點進行指導,最后模擬真實口譯場景,檢測學生是否能靈活運用已學語塊。建立“口譯工作坊”的意義在于引導學生通過合作探索,識別材料中語塊的類別和功能,在具體語境中指導并測試學生語言輸出,以加強學生的語塊意識,提高語塊運用能力。
四、結語
口譯質量有賴于譯員語塊的儲備和使用能力,語塊理論對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的影響已引起學界關注。針對目前西語口譯教學中存在的問題,語塊理論的應用或將成為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在教學中,通過培養學生的語塊意識,要求學生充分靈活應用語塊,從而提高學生的西語口譯能力。但是,將語塊分類界定并轉化為教學資料,包括語塊教材編寫以及語塊教學評價,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1]劉和平.中國口譯教育十年:反思與展望[J].中國翻譯,2016(3):46-51.
[2]Becker,J. The Phrase Lexical[M].Cambridge Mass: Bolt & Newman,1975.
[3]Nattinger, J.R. & DeCarrico, J.S. Lexical Phrases and Language Teaching[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Lewis, M. The Lexical Approach: The State of ELT and a Way Forward[M]. London: Language Teaching Publications,1993.
[5]Wray, A. Formulatic Language and the Lexicon[M].Cambrige: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2002.
[6]Seleskovitch, D. and Lederer, M. A Systematic Approach to Teaching Interpretation[M].Silver Spring, Md.: Registry of Interpreters for the Deaf,1995.
[7]Gile,D.Basic Concepts and Models for Interpreter and Translator Training[M].Ambsterdam/Philidaphia: John Benjamins,1995.
[8]鮑曉英.口譯標準“信”的實現——記憶心理學在口譯中的應用[J].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2005(2):10-13.
[9]郭云飛.語塊理論視角下的大學英語詞匯教學[J].遼寧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3):105-106,109.
[10]宋纓,蔣琴芳,馬秋武.語塊視角下的口譯教學研究[J].外語電化教學,2014(3):75-80.
[11]王建華.語塊教學策略對提高學生會議口譯準確性的實驗研究[J].中國翻譯,2012(2):47-51.
[12]伍萍.任務驅動下的語塊教學訓練模式有效性研究[J].外語教學理論與實踐,2014(1):34-41,93.
[13]段士平.國內二語語塊教學研究述評[J].中國外語,2008(4):63-67,74.
[14]方玲玲.語塊教學對減輕語言僵化的認知研究[J].外語界,2010(4):63-66.
A Feasibility Study on Chunks Theory for Spanish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CUI Qing-xia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61, China)
Interpreting quality depends on the reserves of chunks and the ability to use, but the application of chunks theory in China’s interpretation classroom of Spanish is still rare.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use of chunks theory and the interpreting quality, and a summary of the application of chunks theory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e chunk theory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Spanish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to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chunks; Spanish;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2016-08-15
安徽大學校級項目“西班牙語翻譯課堂教學研究”(JYXM201367)。
崔清夏(1983-),女,講師,碩士,從事語言學和西班牙語教學法研究。
H319
A
2095-7602(2017)01-017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