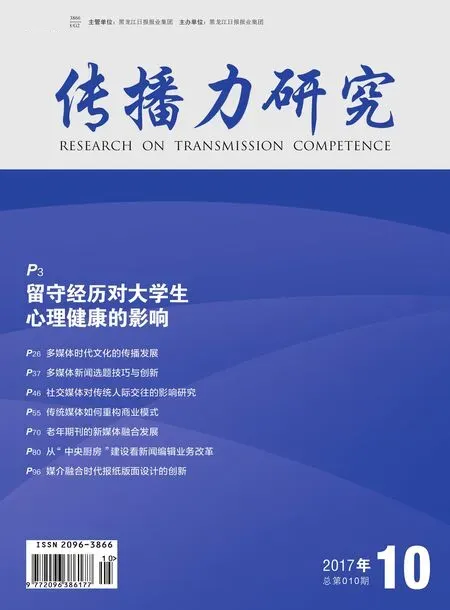分析中國傳統悲劇“大團圓現象”的哲學基礎
文/牟雪蓮
中國傳統悲劇“大團圓”現象與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結構及其性格有著必然的聯系。追溯歷史,周族以武力擊敗殷王朝,建立了以農業為主的、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中國式封建社會。上下相維、等級森嚴、內在和諧的封閉型社會結構,使人們漸漸習慣于各安其所、內向克制、追求穩定和諧的心理狀態。隨著儒家學說的逐漸深入,這種趨向封閉、內向的心理,以及由此產生的克制、穩定、忍讓的性格,便開始在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中積淀以至于定型了。
但儒家學說并不完全是封閉的,它還有積極入世進取的一面,作為儒家學說補充的老莊哲學,雖然也強調“安時而順處”,但它畢竟承認有一個“道”無所不在。因此不能完全放棄外向的追求,仍需竭盡全力在身外世界去尋找。這樣,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性格特征就必然矛盾而復雜了,封閉中略有開放,內向中稍有外向。
但是,總的來說,中國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世界最終包含著無限的適己性。因此,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意向的根本要素就是樂感。樂感的對立面是憂愁感。它在心理意向方面與樂感,剛好相反。事實上,自逸其樂與憂國憂民的主體意向在儒家那里都存在,但又明顯地具有內在矛盾,似乎不可調和。但微妙之處就在于,這一矛盾正好構成相互支持的要素。既然“樂”是終極意向,一旦憂患意識受到阻礙,“樂”終歸是一個絕對的保證。至于道家的態度則明確得多,那就是絕對的無待于外的自逸其樂,絕對地排除憂愁感。王國維認為,中國的傳統悲劇充滿了樂觀主義色彩而著意于團圓之趣,乃是因為“吾國人之精神,時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色彩,始于悲者終于歡,始于離者終于合,始于困者終于亨。”[1]
印度佛學傳入華夏,并結出了智慧空靈的禪宗之花。思想史家們一致承認,禪宗是儒家思想的進一步推進。我們知道,當印度佛教傳入中土時,中國傳統文化正經歷著一場巨大的變革,正所謂“有晉中興,玄風獨震,為學窮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2]玄學之風把儒家精神吹擠到文人士大夫心靈的角落,給他們重新組合了一個較開放的心理結構,卻也給佛教中的禪學、般若學敞開了大門。老莊思想中玄奧神秘的萬物本源——“道”,在玄學家那里變成了“無”,而“無”便與般若學中的“空”相一致了,“無”即是“空”,“空”即是“無”。佛教中那種抹殺物與物界限的佛學義理立即為文人士大夫們所接受。于是,主張在內心世界超脫羈絆,返回自然,追求無懼無俗、樸素淡泊的生活方式,在南北朝已經成為名士風流的標志。印度禪學自我解脫的方式便趁虛而入,滲入了文人士大夫階層。
中國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學一直在入世與出世、進取與退隱、殺身成仁與保全天年之間動搖徘徊。它的外在一面是士大夫與社會發生的關系。它的內在一面則是個人欲望。但追求人世間的享受與保全個人始終在文人士大夫心中共存。即使他們身居廟堂,春風得意之時,心中也暗自羨慕著功成身退的前賢圣哲,淺唱低吟“永憶江湖歸白發,欲回天地入扁舟”(李商隱《安定城樓》)。因此,他們不可能生活在“藏六如龜,防意如城”的世界里,于是南禪宗的“頓悟”學說對他們就再合適不過了。既不用坐禪,也不用苦行,也不念佛誦經,只要心中有佛就行了。這種隱士加食客的生活方式正與文人士大夫朝思暮想的完全一致,與老莊自然無為,退隱適意的生活情趣也完全契合。
這種以自我精神上的解脫為核心的適意人生哲學,對中國文人士大夫乃至于中華民族心理性格的影響是巨大的。它使人們以克制、和諧的方式來追求內心世界的平衡,使人們形成了對外界變化的漠視,甚至還本能地抵抗外界變化對內心世界平衡的沖擊。內心世界缺少壯懷激烈的震蕩感情,永遠處于一個完整而封閉的境界。
“儒道互補”與“儒禪互補”精神決定了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結構和性格,反映到藝術觀賞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圓”的刻意追求,因為“圓”是儒道釋謹慎最具體、最完美的表征和歸結。
盡管儒道釋三家思想體系各有差異,但是有一點非常有趣而且應該引起我們的注意,那就是它們在各自的思想中都表現出“以圓為貴”、“以圓為美”的共同傾向。
在中國古人看來,圓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模型,也是包羅萬象的宇宙模型。自古以來,圓就備受推崇。在中國古代文藝創作和藝術理論中,“以圓為美”的觀念到處可見,屢見于詩文典籍。“冰扣聲聲冷,珠排字字圓”(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新詩若彈丸”(蘇東坡《次韻答王鞏》)等,真是俯拾皆是,蔚為大觀。詩,繪畫、音樂、書法、舞蹈、戲曲唱腔,都無一不以圓為美,圓是最高境界。
當然,中國人所追求的“圓”不是一種簡單的重復,而是在更高層次上實現回歸,合二為一。這個“圓”不是孤立存在的無方之圓,而是事物普遍聯系和運動發展的必然歸宿。作為哲學共生體的中國古典美學,保持、綜合并發展了我國古代樸素辯證法思想,使由中國人的歷史觀、社會觀、生命論及意識論等所形成的中國古代精神現象學充滿了“首尾相銜,開闔盡變”的圓圈現象。
中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結構和性格是在儒道和儒禪精神互補的影響哺育下形成的。這三家思想在審美追求上的一個重要方面是以圓為美。那么,中國文人士大夫筆下的悲劇,原則上就不可能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悲劇與悲憫之二者,為悲劇中固有之物”(王國維語)了,而是充滿了溫柔敦厚、怨而不怒,以和諧取代沖突的大團圓現象。
明代戲曲家葉憲祖所作《易水寒》,寫荊軻抓住秦王,并逼他退還了侵略的各國土地,最后由王子晉度荊軻登仙;清代周樂清寫了八個劇本,都取材于歷史上的著名悲劇,卻全改為喜劇收場,總名《補天石》傳奇,其中《宴金臺》寫秦始皇被狙擊死于博浪沙,各國攻滅秦國;《定中原》寫諸葛亮一舉統一天下;《琵琶語》寫遠嫁塞外的王昭君終于回歸漢朝……
審美情趣是一個時代文化背景的產物,也是這個民族這個階層歷史上審美情趣逐漸積淀、變異、更新的結果。因此,考察分析審美情趣必須把握縱向(歷史的)與橫向(社會的)之間的聯系。上面所引的幾個劇例,大都還是出于“畢竟含冤難盡洗,為他聊出英雄氣”(馮夢龍語)的“補恨心理”,談不上什么藝術美感,純粹是一廂情愿的發泄。正如蒲松齡所說:“雖然撈不著,咱且快活口。”如果說這一類“補恨”之作還只是為了迎合閱者之心,還沒有直接損害到美的藝術的話,那么,有一種大團圓就是以直接損害藝術真實和藝術感染力為代價了。
元代楊顯之所作,寫秀才崔通中舉做官后棄妻再娶,原配張翠鸞尋至,崔橫加誣陷,把她發配遠方,張沿途受盡苦楚,在監江驛與失散多年,已做高官的父親重逢。結局是張與崔同歸于好。這本應是一出感人的悲劇,但劇作者硬把“背飛鳥紐回成交頸鴛”,把這種于情理不合的惡“團圓”強行塞給了觀眾。這種結局與歷史行程之間相去甚遠,不僅導致了戲劇藝術的“失真”,而且在極大程度上削弱以至損害了藝術的感染力和思想性。
在元雜劇的公案戲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通過清官來制造大團圓。這固然反映了人民希望政治清明的良好愿望,也有一定的現實基礎,但從根本上來說,這也只是一種愿望而已。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悲劇理論,所謂悲劇,就是“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的悲劇性沖突”。這是一對深刻的矛盾,然而在中國傳統悲劇里,這一對矛盾卻微妙地得到了調和,既忠君又愛民的清官在戲中成了悲劇性沖突的緩沖器。這其實正是隱藏在人們意識深處的溫柔敦厚、清靜無為、崇尚和諧的思想的曲折反映。
如果說,元雜劇——通常為四折——的前三折還具有某種積極的意義,只是在第四折表現出一種妥協而削弱了劇作的思想性的話,那么,明、清兩代的大多數傳奇悲劇則更是等而下之了。其思想性不但遠不如元雜劇,而且對“大團圓”的追求愈演愈烈,變本加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南戲《趙貞女蔡二郎》據徐渭《南詞敘錄》記載,寫蔡伯喈“棄親背父,為暴雷震死”。元末高則誠的《琵琶記》題材與此相同,卻替蔡編造了一個“三不從”的情節,變成了“有貞有烈趙貞女,全忠全孝蔡伯喈”,最后以大團圓結局。
南戲劇本《王魁負桂英》斜述妓女桂英資助王魁讀書赴考,王中狀元棄妻另娶,桂英憤而自殺,死后鬼魂活捉王魁。到了明代王玉峰的《焚香記》傳奇,情節改為王魁中狀元之后,壞人冒名休棄桂英,桂英死后事獲辨明,人亦復生,與王魁團圓。
著名的元雜劇《竇娥冤》到了明代葉憲祖的《金鎖記》那里,改為竇娥之夫未死,竇娥監刑得救,最后父女夫婦團圓。
由此可見,真正意義上的完美的大團圓在明代才臻其大成。明代是儒學復興的時期,以程朱理學為精神支柱的倫理社會,在更高層次上重新形成。于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和為貴”、“和為美”的倫理價值觀、審美觀,對大團圓心理產生了無法抗拒的影響,其結果就是強調矛盾對立雙方的最終協調,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善惡對立,把嚴酷的生活現實推歸于“誤會”、“不得已”、“小人使壞”,從而使大團圓結局顯得有趣而合情合理,達到了無利害沖突的最佳和諧境界。
明代中、晚期,社會發生了激烈動蕩的變化。新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萌芽,一大批半農半商的工商地主、從事出賣勞力為生的雇主、游手好閑的市民,以及從士大夫中分化出來的市民知識分子,他們的生活態度、入世精神和人生觀都頗與過去大不相同了。人們不再假裝清高,而是放縱地追求金錢聲色,倫理觀念變得淡薄了,失去了約束力。這一具有近代反封建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宋明理學的傳統封建價值觀和倫理觀,給清初的劇壇帶來了一絲活力。
從這個角度來說,它使清代的傳奇創作題材范圍擴展了一些,大團圓結局也不如明代傳奇那樣泛濫。盡管清代仍有不少諸如《雙仙記》、《如是觀》等落入悲劇創作大團圓俗套的劇作,但有不少劇作家寫出了頗具悲劇性的劇作。
更為重要的是,在清初產生了一部在中國傳統悲劇中鶴立雞群,獨具一格的杰作《桃花扇》。它“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結局是“白骨青灰長艾蕭,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興亡夢,兒女濃情何處消。”這部劇作曾得到廣泛共鳴,一度轟動劇壇,讓許多觀眾驚心動魄,甚至痛不欲生,悲劇美感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文人士大夫的人生哲學和他們的戲曲觀與傳統的道德倫理價值觀、循環人生觀以及善惡報應、以圓為美的觀念相融合之時,中國傳統悲劇的風格和形式——大團圓——便已經鑄成了。大團圓現象既是歷史之因,也是歷史之果,同時也是一種必然的文化。任何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由它的心理所決定的。時代心理作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之間聯系的中介,對于思想文化有著更直接的影響。沒有這種時代心理的基礎,無論政治力量如何扶持與提倡,大團圓思想是不可能生長的。
如果給古希臘悲劇加上大團圓結局,那就不是古希臘悲劇了,同樣,如果給中國傳統悲劇加上命運難逃的結局,也就不是中國戲曲了。任何一位藝術家都無法從根本商超越他所生活的時代,擺脫不了魔術般的時代“心理場”。“大團圓”作為一種文化已經是一種歷史的存在,我們所能做的只能是剖析,一種文化的剖析。對于“大團圓”本身,我們不需要接受,但需要了解。
[1]周貽白.中國劇場史[M].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6年.
[2]齊如山.國劇藝術匯考[M].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8年.
[3]謝柏梁.中國當代戲曲文學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