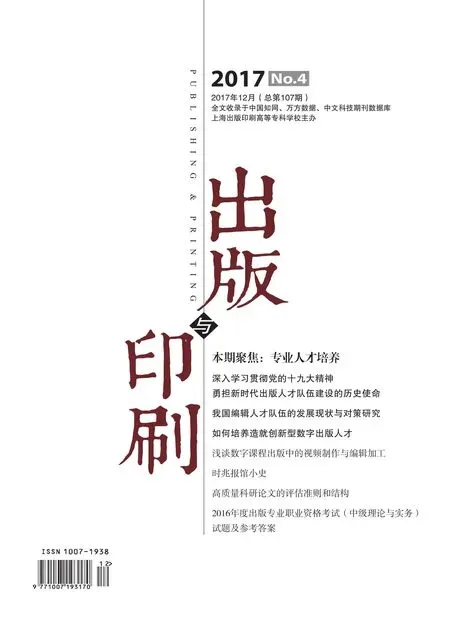“互聯網+”時代的出版模式與人才培養關系微探
林茂
有關出版人才的隊伍建設問題,業界爭論已久,一直未有定論。很多業內專家基于自身從業經歷或研究領域的差異,提出了不同的觀點:有的強調市場為王,將編輯出版人員的營銷能力置于首位;有的強調編輯加工能力,認為良好的編校質量是優質圖書的前提;有的強調選題策劃能力,認為積極尋找知名作者、策劃新穎獨創的選題才是作品成功的根本保障[1];更有要求編輯出版人員成為“復合式、專家型”通才的……各持己見,眾說紛紜。
筆者認為,上述對出版人才提出的要求與30年前即20世紀80年代我國圖書出版市場開始走向繁榮時期相比,并無明顯差異。目前,數字技術已經徹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閱讀體驗,紙媒影響力逐漸下降,以往的出版人才培養模式難以適應“互聯網+”時代的新型出版模式了。
一、“互聯網+”時代出版人才培養模式面臨的困惑
什么是“互聯網+”時代的新型出版模式?如何培養適應這種新型出版模式的出版人才?要回答這兩個問題,首先需要厘清“互聯網+”這一概念。
“互聯網+”一詞,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11月“三馬”(馬明哲、馬化騰和馬云)的一次發言。當時馬化騰提出:“互聯網加一個傳統行業,意味著什么呢?其實是代表了一種能力,或者是一種外在資源和環境,對這個行業的一種提升。”“互聯網+”就是“互聯網+各個傳統行業”,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兩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術以及互聯網平臺,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進行深度融合,實現產業升級,創造新的發展生態。
當前出版界有不少人對“互聯網+”的理解還存在誤區,他們以為,“互聯網+”于出版而言就只是以數字化閱讀器、交互式軟件、智能手機或互聯網來直接替代傳統的紙媒形式,實現閱讀形式的轉換,或是將紙質產品放于網絡銷售。這只是單純地在形式上加以轉化,并未實現新舊媒體的融合,更沒有產生“1+1>2”的經濟效益。以報業為例,《紐約時報》在收入持續下滑的危機中,開啟了大規模數字化轉型,希望借此獲得營收增長。從效果上看,數字版讀者盡管數量不斷增長,但新增的付費收入遠遠不能彌補廣告收入的大幅跌落。究其原因,這種數字化轉型與其過去的既有業務相沖突,具有“零和效應”。這樣一家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老牌報社拋棄自己的既有業務,完全依靠自我來實現數字化轉型,在思路、內容、技術革新方面都會受到一定的阻礙,難以和屬于后起之秀的大型門戶類新聞網站匹敵,因為后者還完全免費。
在這種純“數字化轉型”的思維主導下,不少出版社對如何培養新型出版人才感到困惑。一方面,出版社領導意識到數字化浪潮對于傳統紙質出版的巨大沖擊,深感壓力,甚至悲觀地認為紙媒會走向滅亡,出版社要適應時代發展,員工必須積極擁抱數字化浪潮。另一方面,由于成熟的數字化商業模式仍然處于探索階段,現有的數字化閱讀方式又不同程度地存在難以克服的技術缺陷,因而在實際推廣過程中步履維艱,很多出版社都是在迷茫中進行著各種探索。比如:對紙質圖書僅作數字化銷售不發行紙質版,會難以盈利;采用手機和電腦閱讀又極易造成視力疲勞;亞馬遜的Kindle閱讀器雖然閱讀時眼睛較舒適,但更像一個工具,沒有書的美感,更無法體會閱讀紙書時“隨手一個撩撥,恰翻到自己最想要的那頁”的那種美妙意境;出版社推出的軟件類產品,在用戶體驗、營銷手段上往往又比不上專業軟件公司。
這種困惑和迷茫也反映在出版社對人才的培養上,很多出版社不約而同地成立了專職的數字化部門,卻往往造就了一批根底淺薄的出版工作者,有些人到出版社后連圖書的出版流程還沒有摸清,就被分配到數字化部門,投入到數字化出版的“時代洪流”當中[2]。這樣的人才培養方式是否能培養出新型出版人才,相信時間自有答案。
二、“互聯網+”時代出版業的轉型升級以開發衍生價值為主
必須看到,無論新型閱讀方式怎樣進化發展,紙質閱讀在相當廣闊的領域內都將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現實。
筆者在這里大膽地提出幾種圖書出版業的“互聯網+”設想,其核心思想是在不拋棄紙質圖書的前提下,以互聯網為媒介,在線下或線上開發紙質圖書和作者的衍生價值,通過衍生價值來增加出版機構的收入。這種設想并非空穴來風,在同屬文化產業的唱片行業,已經有了可供參考的模型:唱片業在互聯網的沖擊下,早已放棄了僅僅以唱片銷量來維系企業運營的做法,而是推出歌曲供人免費收聽,從其所衍生出的付費下載和商業演出方面獲取盈利。
1. 教育學習類圖書衍生出的培訓市場
以圖書來教授知識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學習模式,雖然如今的桌面排版系統和版面設計水平較以往有所進步,能夠彌補單純以文字闡述的不足,但基于讀者自身文化水平、學業基礎的差異,對一些讀者來說,僅僅依靠一本紙書來實現高水平的自學仍然是困難重重,特別是在獲取等級證書、職業資格認證時,讀者為了順利通過相關測試,除了購買圖書,往往還會參加付費培訓學習。因此,可以在圖書上放置二維碼,讀者掃描二維碼就可以報名參加網課或者線下補習班的學習,并可直接支付培訓費,凡支付培訓費的讀者可憑書上的涂層密碼抵扣購書款。一本普通的圖書就衍生出了一個培訓項目,在給出版社帶來額外培訓收入的同時,也加強了出版社和讀者之間的互動。
2. 生活休閑類圖書衍生出的跨界價值
以生活類圖書中的孕產育兒題材圖書為例,該類圖書的價格一般在20元到40元之間,即便賣出3萬本以上,以出版行業平均不超過10%的利潤率來計算,獲取利潤空間有限。而對新生嬰兒家庭來說,大量的開銷是花在嬰兒的生活資料方面,如奶粉、尿不濕等。對于這類圖書,出版社可考慮在書上放置二維碼,鏈接到嬰兒用品銷售網站,購買圖書的讀者憑書上的涂層密碼可享受抵扣書款或打折優惠。
對于一些知名藝人的自傳或著名學者的專著等題材的圖書,出版社也可以按照類似方式組織演唱會、見面會、學術講座等,開發其衍生價值,獲取增值利潤。
開發圖書和作者的衍生價值,實現出版社的跨界經營,如果運作良好,出版社可從中獲取較好的經濟效益。
3. 免費報紙所衍生的流量效應
隨著大型新聞類門戶網站和移動新聞客戶端被越來越多的用戶認可并接受,報紙對于民眾的吸引力日益下降,這種趨勢難以逆轉,免費似乎是傳統報紙的唯一出路。免費并不代表與虧損畫上等號。人性與生俱來的特點就決定了人們必然會優先考慮免費的物品,若能以免費換取報紙的訂閱量,也會促使廣告商爭先恐后地去刊登廣告。在南京地鐵各車站內有一份長期免費發放的《東方衛報》,該報日發行量現已超過40萬份。在眾多傳統報紙紛紛關張的今天,《東方衛報》依舊受到廣告商的青睞,經濟效益蒸蒸日上。
綜上所述,在“互聯網+”時代,編輯出版人員應積極開發傳統紙媒的衍生價值,通過免費來拉動流量,在流量上升以后實現新的衍生價值,以衍生價值去彌補免費所付出的成本。相應地,這就對“互聯網+”時代的出版人才培養模式提出全新的要求,而培養“文化經紀人”將是順應這種需求的最佳選擇。
三、“互聯網+”時代呼喚“文化經紀人”
“互聯網+”時代出版業的轉型升級,要求編輯出版人員能充分利用互聯網這個平臺,開發更多的圖書衍生價值。這就要求傳統的編輯出版人員轉型成為進行全流程產品經營的“文化經紀人”。所謂“文化經紀人”,就是在演出、出版、影視、娛樂、美術、文物、體育等文化市場上具有前瞻意識,為供求雙方充當媒介,協調管理的中間人。
1. 當好消費者和作者溝通的橋梁
優秀的演藝經紀人可以為演員挑選適合其出演的劇本和角色。出版領域的“文化經紀人”必須了解消費者的文化消費特征,從而為其提供適合的出版產品。“文化經紀人”應該有意識地讓出版產品與當下熱點事件發生關聯,增加出版產品在媒體上的曝光度,以此來吸引消費者的關注,調動其購買的強烈欲望。
能否有效地開發一本紙書的衍生價值,還取決于“文化經紀人”是否挑選到合適的作者,是否能依據作者的特點,為其量身定做出版產品的運作模式。這與出版社在人才培養上一直強調的提升編輯的選題優化意識、增強編輯的發散性思維是相輔相成的[3]。應該說,“文化經紀人”對編輯的職業素養和創新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具備敏銳的市場洞察力
“文化經紀人”應當具有敏銳的市場洞察力,把握社會文化的發展脈搏,關注社會焦點,捕捉社會熱點,主動策劃選題,引導作者開展創作,并圍繞社會焦點和熱點話題,開發系列出版產品和衍生產品,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
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正在發生著深度融合, “文化經紀人”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新媒體技術開發出版產品的衍生價值,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媒體技術日新月異,本身還在發展變化中,今天受人追捧的技術模式,明天就可能無人問津。業界曾將“兩微一端”,即微博、微信、手機客戶端,當成圖書營銷的萬能法寶,而隨著微博本身作為一種社交媒體平臺的式微,利用微博進行圖書營銷的模式也日趨邊緣化。
3. 具備對出版產品的整體行銷能力與“跨界”推廣能力
“文化經紀人”不僅要熟悉出版專業知識,還要懂得現代市場學,尤其是廣告宣傳,實現整體營銷。“文化經紀人”應時常與廣告媒體界保持密切聯系,通過廣告傳播作品的社會價值。“文化經紀人”要認真審核廣告內容,對采用何種媒體、做什么風格的廣告要提出可操作性的意見,努力塑造作者品牌與產品品牌。“跨界”能力決定了“文化經紀人”是否真正能利用好互聯網平臺開發傳統圖書的衍生價值。
需要注意的是,在“互聯網+”時代,出版社內部原有各部門的聯動問題將日益凸顯,必要時可以成立跨部門協同行動的“聯動”指揮部門,而不再僅僅是依靠“挑大梁”型編輯的個人能力,否則,原有的信息反饋模式很難適應瞬息萬變的市場信息,這就需要從體制與機制上加以改革,協同單位各部門的行為,有效地實現出版社的“互聯網+”戰略。
四、結論
總的來說,“互聯網+”本身就是一個伴隨著時代發展在不斷蛻變升華的新生事物,因此,出版社要順應傳統出版與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潮流,探索“互聯網+”出版模式,這就需要培養一批具有職業素養的“文化經紀人”,對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將勢在必行。
[1]吉爾?戴維斯.我是編輯高手[M].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2]林茂.改革與出格——出版業資本化趨勢與堅守文化追求的辯證關系探微[J].大眾文藝,2014(22):254-256.
[3]林茂.碎片化閱讀風尚下的“全民閱讀”文化建設探析[J].大眾文藝,2013(18):271-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