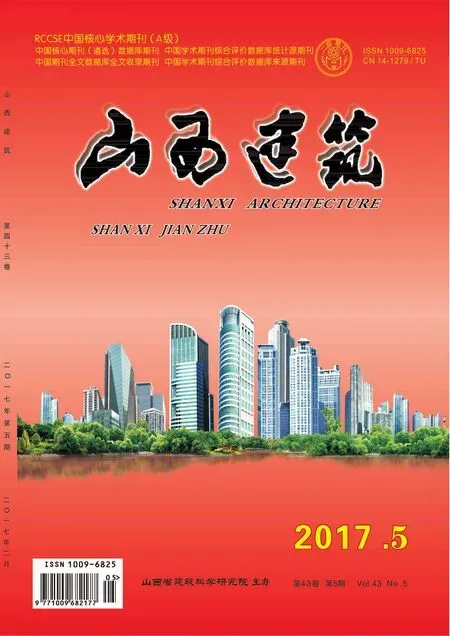景觀改造工程對地鐵區間影響分析
鄧 林 恒
(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湖北 武漢 430063)
景觀改造工程對地鐵區間影響分析
鄧 林 恒
(中鐵第四勘察設計院集團有限公司,湖北 武漢 430063)
采用土體硬化模型(HS模型),對某地鐵明挖區間正上方景觀改造工程進行了三維流固耦合分析,并探討了景觀改造對地鐵區間的影響,結果表明,工程實施具有明顯豎向卸荷作用,導致土層與地鐵區間變位,地鐵區間最大回彈變位4.58 mm,對地鐵結構安全與運營影響風險可控。
HS模型,地鐵區間,豎向卸荷,數值模型
0 引言
隨著城市軌道交通建設的快速推進、軌道交通網絡逐步形成,土地集約化效應日趨明顯,其他市政工程與既有軌道交通結構交匯幾率增加,位于地鐵區間上方的工程案例逐漸增多[1,2]。
軌道交通工程實施時改變了土體初始應力場、滲流場,使得土層應力分布非常復雜。新建工程實施時導致圍巖應力場二次重分布,引起既有軌道交通結構狀態變化,影響結構受力,甚至威脅運營安全。掌握新建工程實施中既有結構變形特征,確保既有結構正常使用,成為工程界必須解決的課題。由于此類工程問題的復雜性,很難通過解析方法求解,須借助數值方法。
本文對地鐵明挖區間上方的景觀水體改造工程進行三維流固耦合數值分析,得到了既有區間結構在不同實施階段時的變形變化規律,從而為工程可實施性提供了技術依據,并指導工程實施與制定監測方案。分析思路與結果可供同類工程借鑒。
1 工程概況
工程平面位置關系見圖1,地鐵區間結構位于人工湖下方,底板埋深約10.2 m,覆土厚度3.3 m~3.5 m,現狀常水位標高1.803 m。區間實施時采用三級放坡,坡度分別為1∶1.2,1∶1.5,1∶1.5。區間與兩側車站采用20 mm寬變形縫連接。目前區間已投入使用約2年,人工湖蓄水已完成。

景觀水體改造工程擬建圓弧形擋水墻,與地鐵明挖區間垂直正交,擋水墻結構形式見圖2,包含7 m寬隔水擋墻與兩側各5 m寬鋪蓋。

景觀水體改造時,需先抽干現狀人工湖蓄水(2.103 m深),開挖后施工擋水墻結構。為減少對下方區間影響,先開挖7 m寬隔水擋墻與外側5 m寬鋪蓋區域,并在內側5 m寬鋪蓋范圍內堆土(0.4 m高);待12 m范圍內結構澆筑后再實施內側5 m寬鋪蓋。結構全部完成后蓄水至現狀常水位。此外需考慮檢修工況(外側常水位,內側抽干至湖底)對區間影響。
2 數值模型與參數取值
數值模型見圖3,模型總尺寸125 m×120 m,景觀水體改造范圍與明挖區間單元尺寸按1 m控制,邊界處單元尺寸適當放寬至5 m。模型四個側面約束法向平動,底面約束三方向平動。

地鐵區間采用殼單元,擋水墻結構采用三維實體單元,鋼筋混凝土結構均采用線彈性本構。由于土體經歷多次卸荷與加荷,本構模型須能滿足工程需要。

為獲得地鐵結構實施后應力場,分析中考慮了明挖區間的降水開挖與回填過程,回填土體參數均采用①2素填土。
分析工況為:1)降水至湖底,降深2.103 m;2)開挖結構段1(7 m寬擋墻+外側5 m鋪蓋)土體;3)實施結構段1混凝土結構;4)開挖結構段2(內側5 m鋪蓋);5)實施結構段2結構;6)蓄水至常水位;7)檢修水位(外側常水位,內側至湖底)。分析中采用流固耦合分析。

表1 土層參數表
3 分析結果
3.1 對地層影響
景觀水體改造工程施工導致土層呈整體豎向回彈,降水至湖底階段土層豎向回彈相對較均勻,并在擋水墻實施階段繼續發展,開挖結構段1土層時土層豎向回彈達到最大值,如圖4所示,最大回彈量為9.32 mm。

蓄水至人工湖常水位時土層豎向回彈量有所恢復,如圖5所示,擋水墻結構回筑區域豎向壓縮,最大壓縮量6.86 mm。

檢修階段土層豎向變位見圖6,由于內側水位低荷載,內側土層呈豎向回彈,最大達6.56 mm。

3.2 對地鐵區間影響
不同工況下地鐵區間底板豎向變位見圖7,區間在降水至湖底階段變位最為顯著,沿區間縱向變位相對均勻。擋水墻結構開挖與回筑階段,地鐵區間局部相應回彈與變位恢復。由圖7可見,工程實施階段,結構段1外25 m,結構段2外38 m區域,地鐵區間底板豎向變位變化相對頻繁。蓄水至常水位時,地鐵區間底板變位基本豎向,最大殘余變位0.51 mm。檢修階段內側降水對地鐵區間影響較顯著,底板在內側降水區域豎向回彈,外側區域呈向下變位特征,最大回彈量3.95 mm,最大向下變位1.19 mm。

工程實施時地鐵區間底板最大豎向變位為4.58 mm≤10 mm,線路最大相對彎曲出現在檢修階段,為1/8 180≤1/2 500,工程實施對地鐵運營影響整體可控。
地鐵區間彎矩承載能力與本文工程實施時彎矩包絡值對比表見表2,可見雖然工程實施導致地鐵區間內力產生一定變化,但原設計能滿足受力要求,不會對區間結構安全產生影響。

表2 內力對比表
4 實測數據
景觀水體改造工程實施監測數據表明,當湖水降水至湖底時,區間底板最大隆起量1.8 mm;擋水墻結構回筑階段最大隆起量為3.5 mm;蓄水至常水位后最大沉降約2.8 mm。
工程實施階段實測數據與本文分析基本一致,蓄水階段沉降量偏大可能與區間明挖回填固結壓縮過程疊加所致有關。
5 結語
通過文中景觀水體改造工程對地鐵區間影響分析,可得到如下結論:
1)景觀水體改造工程產生明顯的上方卸荷作用,從而帶動周邊地層與地鐵區間豎向變位。
2)工程實施地鐵區間最大豎向變位4.58 mm,低于10 mm控制限值要求,地鐵區間內力產生變化,但仍在結構承載能力范圍內,不會危及結構安全。
3)工程實施中,軌道結構最大變位與相對彎曲仍在運營允許范圍內,不會影響地鐵運營安全。
工程實測數據與文中結果較為一致,分析思路與方法可供同類工程借鑒與參考。
[1] 張玉永,宋天田,周順華.軟土地層近距離上穿既有隧道變形的數值模擬[J].華東交通大學學報,2007,24(4):36-45.
[2] 何 川,蘇宗賢,曾東洋.地鐵盾構隧道重疊下穿施工對上方已建隧道的影響[J].土木工程學報,2008,41(3):92-98.
[3] SCHANZ T,VERMEER P A,BONNIER P G.Beyond 2000 in computational geotechnics,chapter formulation and verification of the hardening-soil model[M].Balkema, Potterdam,1991:281-290.
[4] Teo P L,Wong K S.Application of the Hardening Soil model in deep excavation analysis[J].The IES Journal Part A:Civil & Structural Engineering,2012,5(3):152-165.
[5] 王衛東,王浩然,徐中華.基坑開挖數值分析中土體硬化模型參數的試驗研究[J].巖土力學,2012,33(8):2283-2290.
The influence analysis of landscape renovation to metro tunnels
Deng Linheng
(ChinaRailwaySiyuanSurvey&DesignGroupCo.,Ltd,Wuhan430063,China)
The paper adopts the Hardened Soil model to undertake the three-dimension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analysis, explores the influence of the landscape reconstruction on the subway section, proves the engineering implementation has the evident vertical unloading effect which can lead to the deflection between the stratum and subway sections, and indicates the maximal springback deflection is 4.58 mm in the subway sections, so its influence on the subway structure safety and operation are controllable.
HS model, subway section, vertical unloading, numerical model
1009-6825(2017)05-0086-03
2016-12-09
鄧林恒(1985- ),男,碩士,工程師
TU43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