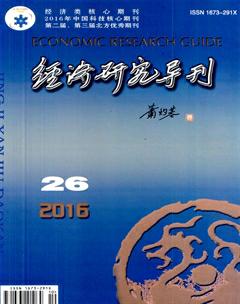論解除合同的通知方式
姜仲波
摘 要:經濟生活領域紛繁復雜、瞬息萬變,企業法人作為商業主體的利益訴求也須因勢而動。當市場不適或出現對方違約等情形達到解約程度或必要時,高效且有效解除合同不可避免成為重要課題。采取合同約定方式、規范快遞方式或公證方式,準確通知并保留相應證據,是最佳選擇。
關鍵詞:解除;通知;合同約定;規范快遞;公證
中圖分類號:D92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26-0157-02
一、非訴訟途徑解除合同通知對方的必要性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之后,沒有履行或沒有依約履行之前,當事人雙方通過協議或者一方行使約定或法定解除權的方式,使當事人設定權利義務關系終止的行為[1]。合同解除有兩種途徑:訴訟解除和非訴訟解除。訴訟解除當然要通過規范運行訴訟程序實現,而鑒于訴訟程序特有的周期較長、程序較嚴、成本較高、專業性要求較強等特征,現實生活中,很多主體會選擇非訴訟解除方式解除合同以求高效。
根據《合同法》第93條、第94條,非訴訟合同解除有三種形式:協商解除、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其中,協商解除一般合同各方會妥善安排后續清理結算等事項,并形成解除協議,不涉及通知事項;而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根據《合同法》第96條規定“主張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則“通知”成為解除合同的必要程序要件,只有該程序要件與《合同法》第93條第二款以及第94條規定的實體要件、第95條并《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規定的期限要件、第96條第二款規定的特殊形式要件相互配合,才能有效發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所以,通知行為將直接決定合同解除是否有效。
解除是否有效經常因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系單方意志、單方行為而引發爭議。而根據《民事訴訟法》第六十四條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下稱“《證據規定》”)第二條確定的“誰主張、誰舉證”原則,尤其《證據規定》第五條“主張合同關系變更、解除……的一方當事人對引起合同關系變動的事實承擔舉證責任”的明確規定,一旦發生爭議,將由解除一方承擔舉證義務。就是說,“通知到達”已經成為解除一方主張已經解除合同的必要證明對象,正確的通知方式即成為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二、通知方式不當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
解除合同的通知,只要對方當事人承認通知效力,雙方當事人無爭議地終止了合同,就應該認為解除通知有效[2]。但如對方不承認,而解除一方又通知方式不當,將導致“通知到達”舉證不能或不力,從而解除無法生效,解除一方不能擺脫合同的原有約束力。更為嚴重的是,解除一方常常因為通知已經發出即主觀上認定合同已解除而對合同事項另作安排,解除無效后果出現,將直接陷入違約而被追責的不利境地。
甲房開公司將新建項目電梯供貨安裝工程簽約發包給乙電梯有限公司,合同期限內,乙公司僅完成約定量的30%,甲公司多次催促未果,派經辦部門負責人電話告知乙公司經辦人解約,隨后與丙電梯公司重新簽約發包后續電梯工程。乙公司卻隨后將70%電梯運送到場并要求結算,對甲公司通知解約電話拒不承認,甲公司陷入拒絕收貨則對乙公司構成違約、收貨結算則對丙公司構成違約的兩難處境。
丁商貿公司向戊電子產品商行簽約訂購筆記本電腦20臺,約定貨到付款,如產品故障率達10%以上則丁公司有權解除合同。電腦到貨后,丁公司發現4臺有各種不同的質量問題,聯系戊公司派技術人員前來修理未見明顯成效后,制發解除通知函并派人直接送至戊商行,戊商行工作人員拒絕簽收,丁公司送達人留下函件及20臺電腦離開。隨后被戊商行起訴至人民法院,請求支付貨款并承擔延期付款的違約責任,丁公司因主張合同解除缺乏證據支持而敗訴。
己商場將一個鋪位簽約出租給庚商戶經營日用品。半年后,庚商戶出現遲延交付租金。己商場經兩次催告未果后提出解除合同。因庚商戶拒絕簽收解除通知函,己商場派人將解除函張貼至庚商戶租賃鋪位,隨后與戍商戶重新簽約出租經營電子產品。戍商戶交付定金后要求進場經營,庚商戶拒絕遷讓、不承認合同已經解除并將拖欠租金打入己商場賬戶。己商場被迫與戍商戶解約并承擔雙倍返還定金的責任。
上述實務案件,解除一方實際上已經享有并可得行使單方解約權,事實上也行使了該項權利并通知到對方。但因方式運用未盡適當、可靠,最終導致解除無效而蒙受損失。
三、正確有效的通知方式
(一)正確有效通知的前置條件
正確有效通知的前置條件有三個:其一,有正確的通知對象和致送地址;其二,有規范的解除文書;其三,有確定的致送痕跡材料即證據可以形成。正確的通知對象取決于合同主體,《合同法》第八條和第121條確立了“相對性”原則,也稱合同關系的相對性,是指合同主要在特定的合同當事人之間發生,合同當事人一方只能基于合同向與其有合同關系的另一方提出請求或提起訴訟,而不能向與其無合同關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請求[3];合同相對性規則的內容是十分豐富的,但集中體現于合同的主體、內容、責任三個方面[4],因此只有向合同文本所載明的對方當事人(也應當是尾部簽章主體)實施通知才可能發生解除效果;正確的致送地址應與對方當事人的營業執照或身份證所載信息吻合一致,或與合同約定的送達地址相一致。規范的解除文書應包含四項要素內容。首先是背景合同固定及解除的明確意思表示;其次是據以解除的客觀事實與法律依據,客觀事實主要指對方未履行或未誠信全面履行合同的具體表現,法律依據主要指合同約定解除權的具體條款或對方違約對應的《合同法》第94條具體條項;再次是是否同時追究對方當事人的違約責任,尤其在法定解除情況下,解除合同與追究違約責任幾乎是孿生必伴,如有相應主張盡量直接明示;最后是異議期給定,以避免“三個月”的法定異議期適用時限過長或影響解除效力。當然,規范簽章并準確填具致函日也不可忽視或出現誤差。確定的致送痕跡材料包括文書原件和致送憑證,后者尤須妥善留存原始信息資料,如簽章回執、交遞文書、張貼視聽資料、電子信息原文檔及截圖等。
(二)合同約定的通知方式
成熟、完善的合同一般會有“通知與送達”條款,其中會明確指示相互通知與送達的具體方式、經辦人員和致送地址,且大多會有“如有變更及時書面通知對方、否則依此致送即為有效”之類的約定。《合同法》第八條規定了合同神圣及合同嚴守原則[5]19,第60條規定了“全面履行”原則,該原則要求當事人在履行的主體、時間、內容、地點等多個方面要符合約定[5]114,因此執行該條款所為通知自當有效,留存好痕跡性材料即可。如前例己商場將解除函張貼至庚商戶經營商鋪,如商鋪租賃合同中確實載有該通知與送達方式,則張貼可產生解除效力,需要的是己商場張貼時同時保留能夠準確顯示時間、地址、函件內容與周邊環境的視聽資料予以舉證支持。
(三)EMS特快專遞方式
合同沒有約定通知與送達條款或約定不明情況下,EMS全球郵政特快專遞的通知形式比較可靠。EMS形式正規、程序嚴謹、痕跡確定、廣為接受和認可,鮮有方式不當或證明力弱差的異議。采用該方式的要點主要是正確填寫并妥善留存交遞詳單。“寄件人信息”處應當重點體現解約一方合同當事人的準確全稱及地址,而無論交遞人的自然人身份情況,如前例甲房開公司派員工張某向乙電梯公司致函,寄件人信息處應寫明“甲房開公司張某”;如直接寫“張某”,則應在下欄“公司名稱地址”處準確填寫甲公司的名稱與地址。“收件人信息”處與寄件人信息處類同,無論收件經辦人是誰,都要顯示合同對方當事人的主體信息,如張某填寫“乙電梯公司劉某”。“內件品名”處最為關鍵,應當寫明所致送函件的完整標題,如“關于解除電梯設備供貨安裝合同并追究違約責任的函”,而杜絕“文件”一類的泛化措辭或干脆在該處保留空白,這樣才能不給對方留下“來件但并非解除事項”之類的抗辯;如果兩份或兩頁以上,盡量同時注明份數和頁數。“附加服務”處應予勾選如“妥投短信”,則在對方簽收后張某會收到“已妥投”之類的手機短信通知,其中并會載明專遞序號,可以和交遞詳單、留存文書備份形成相對完整的有效送達“證據鏈”,充分支持解除通知的主張。交遞日期和聯系電話同樣需要準確無誤,以防止對方找到抗辯角度。其他類同方式如順豐、圓通、天天等快遞或更加便捷的手機短信、電子郵件等新媒體方式,目前階段尚未達到EMS的規范和認同程度,可選用但須更加謹慎。
(四)公證方式
合同沒有約定通知與送達條款或約定不明,甚至在對方下落不明情況下,公證通知形式效力相對最強。根據《公證法》第二條的規定,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民事法律行為、或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2]287。而根據《公證法》第36條、《民事訴訟法》第69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93條,公證具有強大的證明效力,即已為有效公證文書所證明的事實當事人無須舉證證明、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律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合同解除通知是具有法律意義的“法律事實”,更確定講屬民事法律行為的一種,從未來可能涉訴角度,也可以理解為對有法律意義的事實的公證項目中“對行為過程的證據保全公證”。在理論界關于證據保全應否作為公證的事項之一尚存在爭議,不贊成將保全證據作為公證事項的理由主要在于保全證據公證與司法機關的證據保全容易發生沖突,但是鑒于公證實踐中保全證據公證在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公證法》仍將其列為公證事項之一[6]317,只要符合《公證程序規則》規定的可予公證條件而獲得公證取得《公證書》,通知和合同解除的效力將很難推翻,而確定發生效力,充分幫助當事人實現解除合同的預期目的。
參考文獻:
[1] 隋彭生.合同法要義[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274.
[2] 唐德華.合同法案例評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682.
[3] 王利明,房紹坤,王軼.合同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4] 王利明,崔建遠.合同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6.
[5] 韓世遠.合同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9.
[6] 陳宜,王進喜.律師公證制度與實務[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