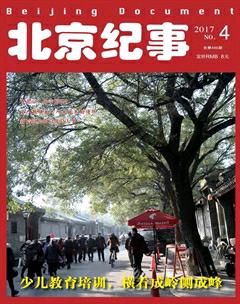喝蛤蟆骨朵
茅今道
北京的夏天比較漫長,而且酷熱難挨,所以有苦夏之說。您也許難以想象,老北京人為了讓孩子平安度過這個夏天,要在春夏之交的四五月份(農歷三月)讓孩子喝幾個蛤蟆骨朵。
蛤蟆骨朵,也可以寫成蛤蟆咕哚,或蛤蟆咕嘟。什么叫蛤蟆骨朵呢?簡單說就是青蛙的“孩子”小蝌蚪。
蛤蟆甩子,也就是產卵后,大概要在開春的四五月份變成蝌蚪。蝌蚪黑黑的大頭,留著小小的尾巴,在河邊成群結隊地游動,煞是好看,讓人瞧著,便會聯想到花的骨朵,所以,老北京人給它起了一個好聽的名:蛤蟆骨朵。
蛤蟆骨朵應該算青蛙的青春期。蛤蟆從骨朵變成會叫的青蛙,前后也就是一個多月的時間,而被稱之為好看的骨朵,大概只有20多天。
這之后,蝌蚪的發育奇快,那黑黑的小尾巴很快就越來越小,似乎在您眨眼愣神兒的工夫,那小尾巴就變沒了,轉眼之間,長尾巴的地方變出來兩條腿,那腿越長越大,成了青蛙的肢體。這種奇妙的變化像北京的春天,轉瞬即逝。大地變綠,脫了冬裝,和煦的春風在您臉上摩挲,剛感覺舒服,您還沒來得及感受春意,已經是烈日當空的夏天了。
這么看來,處于青春期的蛤蟆骨朵還是挺難得的。
一
蛤蟆骨朵長大了就是青蛙。青蛙也叫田雞,為什么叫田雞呢?因為過去河邊、稻田,只要有河有水洼的地方,都能聽到蛤蟆的叫聲,而且這小東西繁殖能力超強,一甩子,幾十條甚至上百條蝌蚪。
在老北京人眼里,蛤蟆并不是值錢的小活物。正因為如此,它也成了北京人餐桌上常見的一道菜,我小時候,常見街頭小販叫賣炸田雞腿,一些飯館也有這道下酒菜。那會兒的田雞是純野生的,到河邊洼地捉,有的是。
田雞必須吃活的,現捉現吃。田雞主要是吃它的兩條大腿,肉很鮮嫩,但并不香,所以吃的時候,得要蘸椒鹽。現在看吃田雞腿有些奢侈,而且也有破壞生態平衡和不保護野生動植物之嫌。但那會兒,青蛙實在是尋常之物。我小的時候,城墻還沒拆,護城河還在,每到春夏,我經常和胡同里的孩子,到護城河邊捉青蛙玩兒。
其實,胡同里的很多人是忌諱吃田雞的,包括我姥姥。她不吃,倒不是因為慈悲,不殺生,而是覺得田雞長得忒難看,也沒什么吃頭兒。我們家是姥姥主內,她不喜歡吃這東西,別人也就跟著嫌棄了。所以,我每次捉回田雞來都送了人,后來干脆就不捉了。
大約上世紀70年代末,隨著城市化的發展,住胡同里的人突然發覺晚上睡覺聽不著青蛙叫了。于是有人寫文章呼吁保護青蛙。也正是從那時起,野生的田雞逐漸在北京人的餐桌上消失了。
到了上世紀90年代,廣東的粵菜在京城餐飲界大出風頭,粵菜里有一道“紅燒牛蛙”,京城的“吃貨”們從這道菜,找到了消失已久的田雞口感。不過牛蛙是人工養殖,已經不是野生的了。
二
跟青蛙比起來,蛤蟆骨朵的生命力似乎更強。那會兒,每到農歷三月,在城里城外的大小河流中,都能看到它們的身影。老北京有一種風俗,每到這個季節,便讓家里的小孩兒喝幾個蛤蟆骨朵。
老人們說,北京的春夏之交風多,氣候干燥,小孩兒容易上火,而且這會兒也是各種瘟病的流行高峰期,喝蛤蟆骨朵能清熱解毒,讓孩子順順當當躲過各種瘟病。
我的姥姥對此深信不疑,所以,每到農歷的谷雨前后,總要讓蛤蟆骨朵到我的腸胃里溜達一趟。我八九歲之前,喝蛤蟆骨朵都是花錢買。
那會兒,每到春夏之交,總會有郊區的農民或是賣魚蟲的小販,走街串巷賣蛤蟆骨朵。賣魚蟲的賣蛤蟆骨朵,屬于摟草打兔子,捎帶手。農民賣蛤蟆骨朵,也屬于臨時抓撓倆活錢。
好在那會兒北京還沒有“城管”,這種走街串巷的小買賣沒人管。不過,蛤蟆骨朵的蛻變期非常短,所以沒人指著靠賣它吃飯。
賣蛤蟆骨朵的一般是推著單轱轆的小車,車上是個大木桶。桶里的水必須是河水,可謂原汁原味,因為蛤蟆骨朵只認原本生存的河水,換了別的水很快就死。小販在桶邊單預備一個小碗。也有挑著水桶的,小碗直接放在水桶里。
稱他們是小販,是因為這種生意實在太小了,而不是指他們的歲數小。通常賣蛤蟆骨朵的以五六十歲的老人居多,也許是年輕人不稀罕這種小買賣吧。
小販邊走邊吆喝:“蛤蟆——骨朵!”“骨朵”倆字輕輕往上揚,尾音變調,非常好聽。
胡同里的老人聽到吆喝聲,便拉著孩子出門,把賣蛤蟆骨朵的喊住。通常花五分錢就能買一碗蛤蟆骨朵。一碗里大概有十來只。
小販用小碗在桶里直接舀出來,小孩兒拿起碗直接喝,喝的時候不能看著碗,因為那小生靈還在碗里游動,看著會不忍心喝。一般是拿起碗,一仰脖直接就把這碗蛤蟆骨朵,連湯帶水吞進肚子里。
也有的買回去放一放,沉淀一會兒,但一般不超過兩小時,怕水不新鮮,蛤蟆骨朵會死。聽我姥姥說,喝死蛤蟆骨朵會中毒的。
三
常來我們這條胡同賣蛤蟆骨朵的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兒,長得又瘦又矮,花白頭發,胡子拉碴,眼眶子上趴著模糊(眼屎),一副沒睡醒的樣子,說話的語調低沉,挑著兩個木頭水桶,走道顫顫巍巍的。
但是這么一個瘦弱的老人,吆喝起來,聲音卻很豁亮悠長。我總覺得那聲音,不是從他嗓子眼兒里發出來的。
他跟我姥姥似乎很熟,每年春天,他準來我們這條胡同賣蛤蟆骨朵。我姥姥聽到他的吆喝聲,便會忙不迭地拉著我出門,必定要買碗蛤蟆骨朵讓我喝,然后塞給老人一把錢,也不數是多少。我覺得有幾毛或者有一塊多錢。
我常常納悶兒,明明老頭兒說五分錢一碗,姥姥為什么要給他那么多呢?
有一次,老頭兒快到吃晚飯的時候才挑著桶過來。他不停地說著抱歉的話,從桶里舀了一碗蛤蟆骨朵。姥姥低頭看了看,沒讓我直接喝,卻讓我回家拿來一個碗,倒在里面說:“回去再喝吧。”然后給了老頭兒一把錢,勸他早點兒回家。
我們回到家,姥姥把那碗蛤蟆骨朵給倒了。原來碗里的蛤蟆骨朵是死的。
“唉,他真是老眼昏花了。”姥姥嘆息道。
這是我最后一次見到這老頭兒。轉過年的春天,他沒來。又過了一年,他還沒來。
我問姥姥。姥姥低聲說:“他死了。”
原來我最后一次見到他時,他已經得了絕癥,而且家里還有一個癱在床上的老伴兒。
“你們認識嗎?”我問姥姥。
她苦笑了一下說:“八竿子打不著。我也是聽人說的。”
四
京城賣蛤蟆骨朵的不止這一個老頭兒,但我總覺得別人賣的,不如那個老頭兒的新鮮。姥姥好像也是這種心理,所以,自從那個老頭兒去世后,姥姥就讓我自己去護城河撈。撈回家以后,她要親自看著我喝,這樣才放心。
也許是自己長大了,也許是那個老頭兒的原因,記得我上小學三年級的那年春天,姥姥從別的小販那兒買的一碗蛤蟆骨朵,讓我喝了。
不知動了哪根神經,那蛤蟆骨朵喝進肚后,我只覺得它們在我的肚子里不停地游動,感覺自己的肚子是條小河。那天晚飯喝了一碗菠菜湯,我覺得那菠菜像是河里的水草。
越這么想,肚子里的“河”鬧得越兇,臨睡覺之前,“河”流到了我的嗓子眼兒,我惡心得吐了,好像要把“河”里的蛤蟆骨朵吐出來。吐得我昏天黑地,夜里還拉了稀。
第二天一早,母親帶我去了醫院。打針吃藥,在床上躺了兩三天才緩過來,但蛤蟆骨朵好長時間才在我的腦海里消失。從那時起,我再也不敢喝蛤蟆骨朵了。
多年以后,我到江南采訪,發覺那地方也有春天讓孩子喝蛤蟆骨朵的習俗。當地人說:喝這個能清熱解毒,治熱毒瘡腫。
后來,我查了《本草綱目》,上面確有這樣的描述:“蝌蚪生水中,蛤蟆青蛙之子也,狀如河豚,頭圓,身上青黑色,始出有尾無足,稍大則足生尾脫。俗三月三,皆取小蝌蚪以水吞之,云不生瘡,亦解毒治瘡之意也。”
這個習俗流傳了多少年,不得而知。但時過境遷,隨著人們醫學知識的普及和環保意識的提高,現在這個習俗基本上已經破除了。
我詢問過當醫生的朋友。他告訴我,蛤蟆骨朵有很多寄生蟲,加上現在許多河水有污染,喝到肚子里會引起多種疾病。
謝天謝地,我小時候北京的護城河還沒有污染。否則的話,保不齊蛤蟆骨朵真會把我帶到“河”里去呢。
(編輯·宋冰華)
ice705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