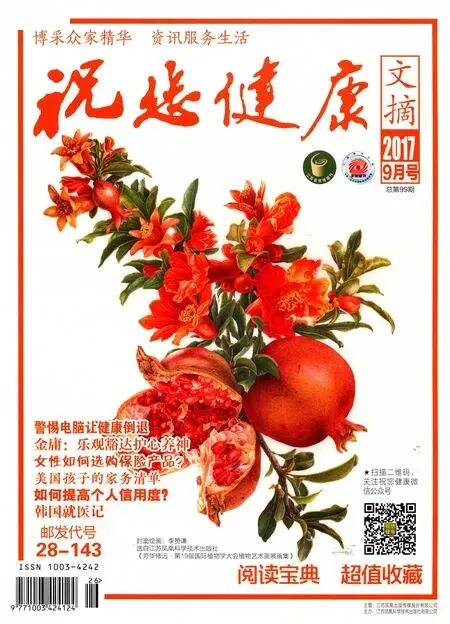康有為的流亡美食之旅
康有為的流亡美食之旅
當“六君子”經歷著人生最悲壯的最后一日時,“戊戌政變”中最為慈禧太后痛恨的康有為卻在外國使館的幫助下逃出生天。即使這一路上顛沛流離,康有為也不忘與美食為伴。
1898年到1913年,康有為還開始了一場頗為奢侈的“豪華列國游”。
說豪華,一點不為過。住的是高級酒店,出行是馬車和汽車,還經常雇用譯員(導游)、仆人和廚師。比如1904年6月,康有為從瑞士進入德國境內,輾轉于慕尼黑、柏林、波茨坦、漢堡等各大城市。他對德國可謂情有獨鐘,“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訪問參觀克虜伯制造廠,贊德國工業制造精益求精,冠絕歐美;訪問聯邦議院,頗感政治清肅,秩序井然;他甚至覺得德國男人都“英武雄壯”,女人則“秀倩可嘉”……正所謂“一切以德為冠”。
在到德國之前,康有為從不喝酒,說也奇怪,到了德國嘗了啤酒,康有為從此“開戒”,每日必飲,連續半月后,再難釋懷。也許對啤酒太有愛了,康有為還曾參加過慕尼黑啤酒節。這一喝,康有為對酒的喜愛開了頭。于是,英國“尾士竭”(威士忌)、法國葡萄酒都進入了康有為的酒單。
除了喝酒,康有為也十分懂得欣賞各種美食。他在斯德哥爾摩品嘗海鮮,“多魚蝦異物,咸酸皆備,其價賤而品多,味亦新異,蓋歐土所未見也”;在匈牙利吃生牛肉配醬;對于法國美食也沒有盲從,康有為抱怨法國菜雖然好吃,但是太貴,“一般飯店,三人一餐,一蒸雙魚,一白筍條,一雞湯,一雞與茶及紅菩提酒,竟花費近百法郎”;他吃得最滿意的國家是土耳其,“其一切肉品并切粒片,且先下味,極類中國”。康有為在土耳其,每飯必加咖喱,牛羊雞鴨、點心面食皆可口,實在算得上是當時的美食家了。
雖然喜歡咖喱,康有為卻十分討厭在印度的游歷生活,最痛苦就是找不到好吃的。按康有為的解釋,印度的王公富人們極少在外就餐,而一般市井賤民又無力享樂,故遍游印度,難覓美食蹤跡:“印人食無可取,惟糖物甚多。”
不過,這段在印度的痛苦歲月,卻成就了一首聞名海外的詩。這首詩出自康有為的女公子康同璧之手。1901年,康同璧18歲,在外文報紙上發現,父親逗留在印度,于是決心去印度找爸爸。1902年春,她女扮男裝,只一人經居庸關,下潼關、蘭州,入疆,翻蔥嶺、帕米爾,南下印度,驚動了英印報紙。梁啟超贊曰“以19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蒼濤瘴霧,真可謂虎父無犬子也”。康同璧終于見到了父親,并陪著父親游歷印度,賦詩曰:“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選自《民國太太的廚房》李舒/著,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