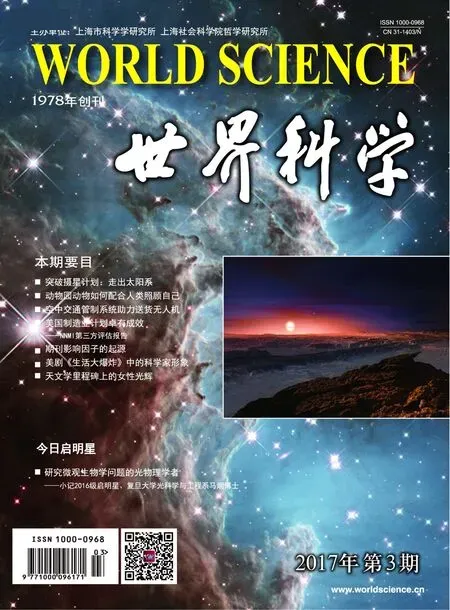研究微觀生物學問題的光物理學者
——小記2016級啟明星、復旦大學光科學與工程系馬炯博士
研究微觀生物學問題的光物理學者
——小記2016級啟明星、復旦大學光科學與工程系馬炯博士

馬炯與2014年諾獎得主Eric Betzig
這次我們約定的啟明星采訪對象是從事光生物物理研究的復旦大學青年研究員馬炯博士。
見了面才知道,眼前這位人高馬大、外形彪悍的小伙子乃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馬炯的爺爺奶奶這一輩是住在上海老靜安一帶的,馬炯的父母是當年去黑龍江大興安嶺林場的上海知青。在外婆退休后,馬母頂替外婆崗位回到上海,之后父母結婚,其父以解決夫妻分居的政策回到上海。1981年馬炯出生后,3代人擠在幾個平方米的小屋子,在這個小小空間里,馬炯一直住到他小學畢業。馬炯至今仍然記得那時居住的窘迫。
以父母為榜樣的上海好小囡
環境改變人。馬炯很敬佩自己的父母,他們作為老三屆初中生一直靠著努力打拼來改變生活,馬炯說:“父親為了養家,當了上海第一代出租車司機,當時一輛車只有一個人開,每天都是六七點就出門,到凌晨一兩點才回來;而媽媽則努力讀書,之后考取了大專,成為一名律師。”父母起早貪黑勤奮工作,有了一點錢后就改善住房,改善生活。小時候生活的艱辛和父母的努力對兒時的馬炯也是無言的教育,“我身上少一點獨生子女的嬌氣,懂得要吃苦忍耐,應該說與我父母的狀態都有關系。”
盡管我們無意強調馬炯的上海出生背景(啟明星中上海本土人士確實占比不高),但是聽到馬炯說起自己的成長經歷,說起他父母這代人為改變生活付出的努力、獲得的成功,真的讓人不得不對這些“有腔調的”上海人蹺起拇指。
馬炯小學就讀于一師附小。因為奶奶曾是南洋中學音樂老師的關系,馬家一直有鋼琴。琴棋書畫這些是上海人家希望小孩子學的東西,馬炯在父母的要求下都學過一遍,但唯一能取得好成績的還是他自己喜歡的數學。自從小學四年級參加了區里的業余競賽學校培訓,他對這些與平時千篇一律的上課內容不一樣的知識產生了興趣。到5年級,他得了上海市小學奧數競賽三等獎,因而得以保送進華師大二附中。隨著時間的推移,馬炯感覺奧數學習中要求重復練習的越來越多,而需要思考的東西逐漸變少。到了初二他就轉向了更具思考樂趣的物理學,找到了今后人生的至愛。高三時拿了全國物理聯賽上海市一等獎(全市第十名),被保送復旦大學物理系。
追索熒光量子點不穩定機制開掘出新方向
本科期間的學習相對平穩。大二大三,有些同學開始準備出國,忙著考托考G,但是馬炯不愿意花這么多時間做這些他認為重復記憶且浪費時間的事情,就計劃著準備留校直研。由于績點符合保研要求,馬炯如愿在物理系直研。馬炯的碩博導師陳暨耀先生的研究方向是生物物理,當時陳老師的興奮點是用顯微光學的檢測手段來研究新型納米量子點在生物體內的發光性質及其應用。因喜歡陳老師研究的東西,馬炯成了陳老師的第一個博士生。
也就是從大四進入陳老師研究組起,馬炯對生物物理的研究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他覺得自己能做的事太多了,從老師布置的東西開始閱讀,查資料看文獻,和不同專業的人打交道、討論,慢慢進入了準科研的狀態。當時他就覺得物理學能應用的面很廣,對閱讀文獻也越來越有感覺。他有個計劃,爭取每年發一篇文章,這樣既是對每個階段的總結,也會減輕臨畢業時的論文壓力。
研二時,陳老師和信息學院另一位老師湊錢買了一臺價值100萬的共聚焦熒光顯微鏡。圍繞這臺設備,他們就能把做生物的、高分子的人聚在一起,圍繞熒光量子點在生物體內的光學性質開展課題研究。馬炯在這個課題中側重做光學穩定性。當時業內一個幾成共識的定見是:熒光量子點在發光上要比其他染料穩定得多。但馬炯在實驗中發現還是存在量子點不穩定的情況,這種反常的情況引起他一探究竟的興趣。
在陳老師的支持下,他通過研究熒光量子點不穩定的機制逐步解開了這一不穩定之謎,找到了量子點光穩定性與氧氣的關系,確定了單態氧是影響量子點穩定性的主要因素。之后,馬炯只身一人到南非羅德斯大學化學系做為期3個月訪問學者,他幫助搭建了一整套用于測量單態氧產生量的紅外探測設備并研發了配套的數據分析方法。通過這套設備,最終確定了量子點的單態氧產量。
就這樣,馬炯通過追索“熒光量子點發光為什么不穩定”逐步打開了一條研究的道路,通過研究量子點穩定性的機理,找到了防止單態氧影響的新制備方法來優化量子點穩定性。反過來,馬炯又開發了一種新型量子點-光敏劑復合物,利用量子點優良的光學性質吸收光,再通過能量共振轉移至光敏劑以增強量子點產生單態氧的能力,并期望利用單態氧可以殺傷細胞的特性來殺傷癌細胞,使之成為治療癌癥的利器。為此,馬炯在博士最后一年里,花了半年時間去奧斯陸大學生理學系求學,在這個國際知名的單態氧光動力癌癥治療的先驅單位做訪問學者。
整個博士學習期間,馬炯進行了熒光量子點特性的深入研究。研究確定了熒光量子點在細胞生物學應用中的光學性質,發現了單態氧在水溶性熒光量子點淬滅過程中的作用,并首次測量了水溶性熒光量子點的單態氧產量。以此為基礎利用熒光共振轉移將量子點和光敏劑結合做一種新類型的藥物用于光動力治療癌癥,開創了一個新的方向。在此期間他發表的論文受到了化學、生物及醫學各方面科學工作者的關注。
七年博士后研究,專攻核孔復合物成績斐然
2008年5月,完成博士論文答辯后的馬炯正忙著落實博士后研究的事。正好美國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生物系及光化學中心的楊衛東教授來復旦講座,楊教授報告的內容是用新型單分子技術(超分辨率顯微鏡技術)研究細胞核孔復合物。所謂核孔復合物就是指細胞核與細胞質之間控制基因相關物質輸入輸出的主要通路,這本身也是細胞基因調控中的重要一環,與白血病、阿爾茨海默病等疾病密切相關。核孔復合物研究曾經是很熱門的方向,但在馬炯進入的這一年,這個領域已陷入了一個瓶頸期,普通生物化學的手段已用盡,大家都不知道怎樣進一步深入下去。當時國際上有幾個組都試圖用單分子熒光的手段推進研究,楊的研究團隊在這方面走在國際前列。
楊教授的講座激起了馬炯的興趣,馬炯感覺這就是自己想去的地方,于是就向楊教授表達了想去他那里做博士后的愿望。經過必要的程序,2008年,馬炯加入鮑靈格林州立大學生物系及光化學中心,在單分子測量研究組進行博士后研究。2012年,馬炯隨課題組搬遷至美國天普大學生物系。在此期間,馬炯晉升為研究助理教授。
博士后期間,馬炯專注于對細胞內分子快速輸運過程的測量和分析以及對新型超分辨熒光顯微鏡技術的研究。利用新開發的光學系統,馬炯在細胞核孔復合物的研究中取得了以下突破性進展:
1.發明單點斜入射快速超分辨顯微鏡(SPEED顯微鏡),確認核孔內非折疊蛋白的三維結構。馬炯利用其獨特的光學設計,實現在單個細胞核孔復合物(NPC)中以400μs和9nm時間空間精度追蹤單分子穿越核孔,并自主設計了獨特的退卷積計算方法,獲得了分子穿越的三維路徑。
2.首次獲得生物小分子穿越細胞核孔三維路徑和選擇機制。通過微調SPEED顯微技術,馬炯測定了不同大小的分子通過被動擴散方式穿越核孔的路徑,確定了被動擴散分子通過核孔中軸上單一通道穿越核孔,解釋了核孔對分子大小的選擇機制。
3.確認了mRNA核孔輸出三維路徑。馬炯改進了熒光標記mRNA復合物的方法,并結合SPEED顯微鏡技術及蒙特卡洛計算機模擬等技術,成功地獲得了mRNA復合物在核孔輸出過程中的三維路徑,糾正了因一維數據以及慢速追蹤的局限性所產生的對核孔控制mRNA輸出機制的誤解,證實了“快-慢-快”模型比原有的“慢-快-慢”模型更接近真實,提出細胞核孔中心才是控制mRNA輸出的關鍵而不是核孔兩邊。
4.通過選取能與核孔產生不同相互作用類型的分子作為熒光標記物,并結合SPEED顯微技術,首次獲得了細胞核孔內各類主要相互作用的分布,由這些分布獲取了由非折疊蛋白組成的核孔內主動運輸通路的具體信息,并通過濃度控制系統,發現了各類反應之間的優先關系。
如何更有效地推進交叉科學研究
2014年,圓滿完成博士后科研工作的馬炯首選復旦作為自己回國工作的單位。一直和他保持聯系的陳老師希望他回復旦物理系,但考慮下來馬炯覺得以開發技術為重的信息與工程學院更適合他。這樣馬炯就回到自己的母校繼續科研生涯。
馬炯很感謝復旦大學和信息學院給予他的扶助和大力支持。他剛一回來,學校和院里就給予他200萬啟動資金的支持。利用這筆錢馬炯在復旦搭建了一套和在美國做博后時一樣的設備,同時也招收了學生,組建了自己獨立的研究團隊。回國后第二年,馬炯申請到兩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2016年他又入選國家“青千”計劃和上海科技啟明星計劃。
迄今,馬炯已在國際權威雜志發表了22篇論文,主要包括:2篇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1篇Nature Communication,1篇Nature Structrue and Molecular Biology,2篇The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2篇Nanotechnology等,均為第一作者。此外,還在權威國際會議上發表了12篇論文,論文被引用總次數超過580次。他關于超分辨顯微鏡方面的論文,被包括Nature,Cell,Nature Review及PNAS等雜志引用81次,其中大段引用20余次。
這次對馬炯的訪問,讓我們有幸認識了一位十幾年來一直從事將物理學、化學及光學技術相結合研究微觀生物學問題的年輕學者。交談中,他對我們關心的交叉科學研究提出自己理解:“我學的是光學,之后去做生物有關的研究,這當中的跨度是很大的。一個好的交叉學科工作者,要在對自己原有學科有著扎實認識的基礎上,對所要研究的對象有深入的了解,對我來說就是對相關生物學知識必須要有大量的儲備之后才能進入其中。如果只是單純地找一個懂生物的人合作,自己不去深入,往往只能停留在很淺的層面上,是達不到最佳研究效果的。真正要做好交叉科學研究,就需要研究者一直不斷地深入研究下去并且要保持多方溝通交流,每一次面談都會產生一些火花、一些靈感,那都可能是一個新研究方案的開始。”
馬炯對交叉學科研究的感悟值得重視。如今越來越多的人對通過多學科交叉來研究諸如生命及疾病本質、環境、能源和新材料等問題抱有越來越大的期待,但是怎樣的交叉科學研究才是有效的?怎么來推進和組織交叉科學研究?十多年前作為經驗介紹過的,讓不同學科的人在研究空間上(比如一幢大樓里)有更多的交流機會。這種咖啡角式的碰撞交流無疑是一種有助于多學科交叉的手段。但是本文的被訪者馬炯提出的“研究者如能對所要交叉的主要學科有更多了解,就會大大提高這種交叉合作成功概率”的觀點,同樣值得傾聽。
[江世亮、顧姚星采寫于201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