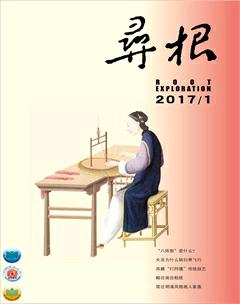紀曉嵐筆下的昆曲故事
陳益

《閱微草堂筆記》是紀曉嵐的筆記小說,寫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慶三年(1798年),主要搜集各種狐鬼神仙、因果報應、勸善懲惡等鄉野怪談,也有道聽途說的奇聞軼事,享有同《聊齋志異》并行海內的盛譽。紀曉嵐本是才子,嘉慶皇帝御賜碑文“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以政無不達”。他在官場滾打多年,閱歷深、交游廣、眼界遠,筆下文字非同一般。這里選取與昆曲有關的幾則故事,讀來別有趣味。
其中一則,紀曉嵐引用了田香沁的故事。一個風靜月明的夜晚,在家中讀書的田香沁忽然聽見有人在唱曲。歌聲曲折委婉、清麗圓潤,真叫人傷心動魄。仔細分辨,原來是在唱《牡丹亭》“叫畫”那一折。田香沁聽得入神,忘卻了身邊的一切。直到聽完,才驀然想起墻外是殘港荒陂,人跡罕至,歌聲是從哪兒來的?他推開窗戶一望,夜色里只有蘆葦在秋風中瑟瑟搖動(《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七《姑妄聽之三》)。紀曉嵐說,李商隱詩中有“空聞半夜鬼悲歌”的句子,用的是晉代鬼唱《子夜歌》的典故;李賀詩中描繪的“秋墳中鬼在唱鮑照的詩”,是因為鮑照寫過《蒿里行》,他加以想象發揮而成。
如果說夜半歌聲讓人生發出奇妙的想象,那么伶人方俊官的命運就發人深思了。方俊官以姿色出眾和演技高超擅名于歌舞場,常出入高門,紅極一時。上了歲數后,他無奈改行以販賣古董謀生。他對鏡自照,感慨萬千:“我方俊官競變成這副模樣兒了!誰能想到,這鏡子里的人,就是當年舞衣弄扇、顯赫一時的方俊官兒呢?”
方俊官追述說,他也是出身于書香門第,十三四歲的時候,在家鄉讀書。一天夜里,忽然夢見了笙歌花燭的迎娶場面。接著,他就被擁入洞房。低頭一看,自己已是繡衣錦帔、滿頭珠翠的新娘子,兩只腳也變成了纖纖巧巧的小腳,穿上了弓彎繡履。正不知所措時,競被眾人簇擁,在帳幃中與一男子并肩而坐,他既驚恐又羞慚,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隨即從夢境中驚醒。后來,他被強人逼迫,終于失身于歌舞場。方俊官把自己的身世和夢境相連,才省悟到人的命運是生前注定的。
對此,紀曉嵐和倪馀疆之間有所爭論。倪馀疆認為,果由因生,因由心造,怎能推脫夙命。紀曉嵐評價道:曲伎之輩,容易沉淪賤穢。這一切,應該認作是對他們前生罪惡的業報,而體現于今世,不能說就一點夙因也沒有。
今天我們假如將方俊官做一番分析,就不難發現他的夢境完全可能是角色心理的投射。六百年昆曲史中從來不缺少男旦名伶,明清時期的職業戲班,演員往往都是男性,男旦成為一種必然,同性戀現象屢見不鮮,演技出眾者甚至“妖艷絕世,舉國趨之若狂”。被稱為“姿色出眾,演技高超”的方俊官,不是天生就有飾演旦角的潛質,便真是一個心向旦角的男性,難免有扭曲的性心理。
《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二》記述的一則故事,可作佐證。
一位名叫朱靜園的貢生,有丁卯同年某御史,曾問喜歡的歌姬一個問題:像你這樣演戲的人很多,你是如何做得比別人好呢?歌姬回答道:我既然演女人,必須心也是女人,才能柔情媚態,別人才會喜歡。如果我有一點點男性的心,必然有一點不像女人,怎么可能爭取到寵信呢?如果登場演一個貞烈女,則擺正心態,就算是開玩笑也不失忠貞;演淫女,則蕩其心,雖端坐也不掩其淫;為貴女,則尊重其心,雖簡單的衣服而貴氣存;為賤女,則斂抑其心,雖盛妝而賤態在;為賢女,則柔婉其心,雖怒盛無遽色;為悍女,則拗戾其心,雖理詘無巽詞。其他的喜怒哀樂,恩怨愛憎,一一設身處地,演員在臺上不認為自己是演戲,而認為是真的,別人看起來就是真的了。而有些人演女人不能存女心,演種種角色而沒有種種角色的心態。這就是我演得比別人好的原因。
紀曉嵐引李玉典的評論說:這話雖然不足道,但道理確實非常精到。所講的事情雖然很小,但可以比喻很多東西。天下沒有那種心不在其事而能做到極致的人,也沒有那種心在其事而事不能做好的人。專心一致,則藝必精,職必舉。這番話,令人想起戲劇大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體驗派”戲劇理論,正是強調現實主義原則,主張演員要沉浸在角色的情感之中。
《閱微草堂筆記》中還有這樣一則,說獻縣、東光、泊鎮、任丘等地,不但有戲曲演出,且常常演至深夜,就連運糧船上也有演出活動。乾隆三年(1738年),大運河水淺,運糧船一艘接一艘都擱淺不能航行,于是演戲祭神。運糧官也在場。正上演《荊釵記》中“投江”那一折,扮演錢玉蓮的伶人忽然跪在舞臺上哀哭起來,聲淚俱下,喃喃說個不停。他說的是福建話,旁人一句也聽不懂。人們恍悟是鬼附體了,追問他怎么了,他聽不懂話,扔給他紙筆,連連搖頭好像不識字,只是指天畫地,叩頭痛哭。大家沒辦法,便把他扶到岸上。他仍然嗚咽掙扎,直到人們散去才停止。過了一會兒,這人清醒過來,說突然看見一個女子,手里拎著自己的頭從水里出來,把他嚇得靈魂出了竅,后來的事就不知道了。眾人皆言,恐怕是滯留水底的鬼魂,見官員在此,所以出來喊冤,但看不見她的形體,言語又不通。官員讓會水的人下河去尋找尸體,并沒有找到。兵丁中也沒有女的,查不出究竟。官員只好聯名寫了份狀子,送到城隍廟里燒了。四五天后,競有個水手無緣無故地自殺了。
紀曉嵐的筆記里常有鬼神故事,各有隱喻。這些故事是否講冤魂報復,暫且擱置,筆者關注的是昆曲進入河北的路徑。河北地處京畿,環繞京師,文化欣賞習慣無不深受京都影響。但是由于地域、經濟、文化發達程度的差異,河北的流行時尚往往會晚于京師。昆班大量進入河北,當在咸豐、同治、光緒三朝。進入河北有兩個渠道:一是南方藝人沿大運河進京,途經河北時,將昆曲傳播在運河兩岸,包括滄州、廊坊地區的大碼頭;二是往來于山西、陜西的昆曲戲班,經過大同、太原過張家口在張(家口)宣(化)一帶演出,也流布河北。昆曲受河北地區語言、傳統音樂、民間戲曲、觀眾欣賞習俗等影響,漸漸發生變化,形成了個性鮮明的藝術風格,與南昆有明顯的區別,曾被人戲稱為“怯昆腔”“高陽昆腔”。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如是我聞三》還記載了蔣士銓講的鬼故事。翰林院編修蔣士銓(字心馀)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考中的進士,在他江西家鄉,有一處老宅,已多年荒棄不用,可是人們經常發現有濃妝艷抹的年輕女子扒著墻頭往院外看。
村里有個王某,練就一身武藝,粗豪而有膽量。聽說這老宅里有狐女,他徑自一人帶上鋪蓋,跑到那里去住,想看看狐女到底長什么樣子,想有所艷遇。睡至大半夜,四處寂寥,他感到索然無味,就拍打著枕頭,自言自語道:“不是說老宅里有狐女嗎?跑到哪兒去了?怎么一個也不露面?”話音剛落,就聽窗外有個女子的聲音回答:“六姑娘知道今天您會來,躲避到河邊賞月去了。”王某不由追問:“那……你是誰?”窗外回答:“我是六姑娘房里的使喚丫頭。”又問:“你們家這姑娘也怪了,她為什么要躲著我?!”那丫頭囁嚅道:“我也不知道到底為什么,只聽她說,是怕見您這位‘腹負將軍。”王某語塞,怎么也弄不清“腹負”將軍是什么意思。
次日,王某逢人就問:“腹負是個什么官?在武官行當里夠幾品?”被問的人只是哈哈大笑,不作任何回答。
后來,有人向王某的同鄉打聽,問王某是不是真有這番經歷。同鄉回答說:“王某實有其人,獨宿故宅也實有其事。然而,他在那所老宅里,只是徘徊了一夜,一無所見。故事中的自言自語以及和小丫頭的對話,不過是蔣編修的點綴罷了。”
蔣士銓十分幽默地諷刺了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王某,其實他不僅會講故事,還會寫昆曲傳奇。在湯顯祖逝世150年后,蔣士銓寫了一部《臨川夢》。據日本學者青木正兒《中國近代戲曲史》記載,這部以劇作家湯顯祖為主角的傳奇分上、下兩卷,共20出。傳奇中多次出現特殊人物婁江女子俞二娘,例如第四出“想夢”,寫俞二娘耽讀《還魂記》,其中的柳生和杜麗娘競出現幻影。第十出“殉夢”,寫俞二娘讀《還魂記》斷腸而死。可是到了劇本的下卷,故事情節的變化超出了人們的想象。例如第十五出“寄曲”,寫俞二娘死后20多年,她的乳母將俞二娘批點的《還魂記》送到了湯顯祖手里。第十六出“訪夢”,寫俞二娘的亡魂打算拜訪湯顯祖,以此意訴之釋尊。第十九出“說夢”,寫湯顯祖長子死而歸天,與淳于棼、盧生、俞二娘、霍小玉等人在天王前相會,論世事皆夢。最后一出,則寫湯顯祖在玉茗堂睡覺,睡神引俞二娘的靈魂進入湯顯祖的夢中,與之相會。湯顯祖感其知己,淳于棼、盧生、霍小玉等人也來見,玉茗花神傳天王法旨,迎眾人入覺華宮。
在這部《臨川夢》中,湯顯祖與俞二娘不僅超越了劇作家與觀眾的關系,更超越了現實生活中人與人的關系,他們的靈魂居然能在夢境中相聚,并進入仙界天庭。蔣氏所著的昆曲傳奇,與紀曉嵐筆下生動入世的昆曲故事,亦有異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