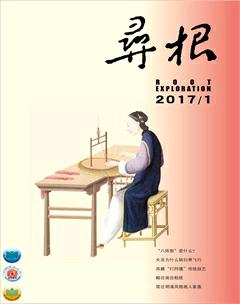《新小說》的“文藝通俗化”試驗
凌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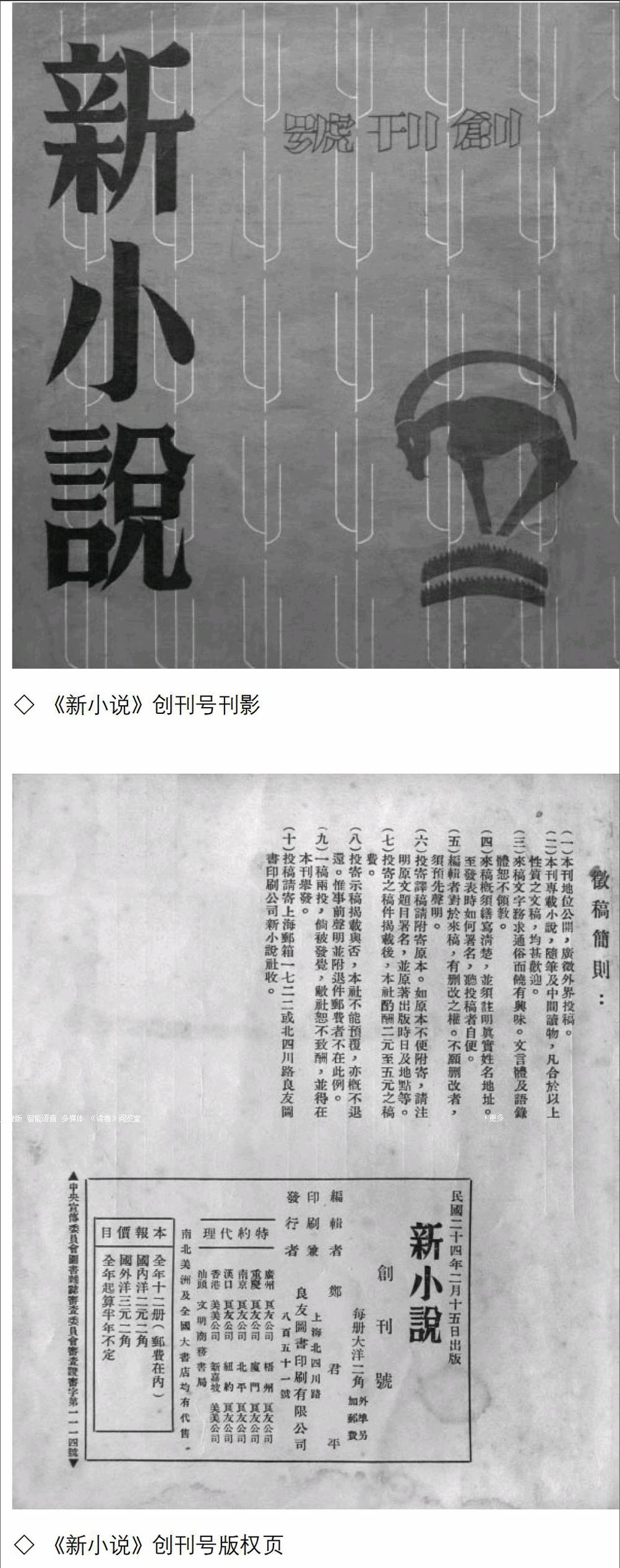
一
《新小說》于1935年2月在上海創刊,月刊,二十開,方型本。鄭伯奇編輯。
鄭伯奇(1895-1979),原名鄭隆謹(一作隆瑾),字詠濤(一作泳濤),伯奇原為筆名。陜西長安人。早年加入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1917年去日本留學。1921年加入創造社。1926年畢業于京都大學文學部。回國后任中山大學教授、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7年到上海,與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都是創造社的重要人物。參與籌備“左聯”并任常委。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后,鄭伯奇化名鄭君平,去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當編輯。他在《“左聯”回憶散記》中記述:
我提議編輯一種文藝刊物,書店負責人也同意了,決定由我負責。《新小說》就這樣產生了。這雖不是“左聯”的刊物,因為我在“左聯”參加“大眾化”的工作,很想借這塊園地來作試驗。
鄭伯奇說,“左聯”時期提出“大眾化”和“通俗文學”,“前者主張作者運用群眾日常使用的活的語言,即群眾的口頭語,反對五四文學運動以來知識分子慣用的歐化了的‘白話;后者主張運用鼓詞、評書、戲曲等通俗形式創作有革命內容的新的通俗文學”。(《“左聯”回憶散記》)《新小說》第一期《征稿簡則》要求:“來稿文字務求通俗而饒有趣味,文言體及語錄體恕不領教。”第四期《編輯后記》又重申:“我們歡迎通俗作品,太艱深的、太得山人名士氣的東西,恕不接受。”
二
《新小說》刊載的重點是小說。
張天翼的《一九二四三四》寫從五卅慘案到“九一八”“一·二八”十年時間翻天覆地的大變革。一個最初決心投身革命的青年,如何在殘酷的生活面前,放棄了遠大的理想,變成一個意志消沉的小市民。小說“用書信體,很客觀地描畫出大時代中的一個‘零余者”。
郁達夫的《唯命論者》寫一位教了二十幾年書、月掙三十八元六角的小學教員,他的妻子用外婆給孩子的一元錢,偷偷買了一張航空獎券。開獎那天,夫妻倆誤認為中了頭獎,做了一場好夢。夢想破滅,人們在學校附近的河浜里發現了小學教員的尸體。當年《文學》雜志稱許“《唯命論者》是既能通俗又耐回味的一篇小說了”(《雜志潮里的浪花》)。
柯靈的《犧羊》描寫在困難時期為生活為藝術而掙扎的一群青年女性。柯靈說,《犧羊》的題材是出于鄭伯奇的提議。鄭伯奇告訴他,電影界新舊勢力的矛盾很突出,也是社會矛盾的具體反映,其中形形色色的人事沉浮,都是很吸引人的素材。
張天的《伙計》描寫舊京公寓的伙計們,編者稱“他的輕松的筆致、流暢的語言,直可追蹤老舍先生的短篇”。
魯迅給刊物翻譯了西班牙作家巴洛哈的小說《促狹鬼萊哥羌臺奇》。
各期的《編輯后記》(或《編輯余談》《編輯室往來》《作者讀者編者》)中,有編者對作品的簡要點評。如:“茅盾先生一篇刻畫沒有自覺的摩登女性可謂入木三分。圣陶先生的《半年》假借兒童的口吻將教育危機的一端深刻地表現出來。靳以先生的《一人班》雖是素描式的短篇,頗富于人道主義的凄愴的情調。萬迪鶴先生的《晉謁》在平凡的場面中描畫出躍動的心情。鄭伯奇先生的《幸運兒》是有時事性的諷刺作品。吳泮云先生的《老提摩太之死》描寫戀愛與宗教的沖突。姚雪垠先生的《野祭》敘述由一個人的失蹤所引起的家庭悲劇。”這是就內容而言,而對表現形式的不同之處,編者也有獨到的發現:“施蟄存先生的《獵虎記》用評話手法,寫幽默故事;曹聚仁先生的《葉明琛》取歷史題材,寫隨筆體的小說:都是難能可貴的作品。”“陳子展先生的《呆女婿》用日本的狂言體寫中國的民話,這是有意義的新嘗試。”
《新小說》在小說之外也刊登隨筆、雜考、散文等。阿英的《燈市》是對《金瓶梅詞話》風俗的考證,洪深的《山東的五更調》是對民間文學的探討,編者將之列入《中間讀物》專欄。《名著研究》欄中有寒峰(阿英)關于《文明小史》的評論。散文中豐子愷的《放生》敘寫人生感悟,葉圣陶的《近來得到的幾種贈品》瑣記深厚情誼。刊物還設有《幽默小話》《閑話簍》等欄目,刊登輕松有趣的幽默笑話、民謠小曲。這些內容,淡化了政治色彩,突出了通俗化的主旨。
鄭伯奇廣約全國名家撰稿,第五期上曾刊出“經常為本刊執筆諸先生”名單,計六十三人。檢索六期雜志,作者中已在名單者有三十三人,未入名單的姚雪垠、任鈞、蕭軍、馬宗融、侯汝華、徐遲、戴平萬、立波、康嗣群、楊郵人等,也都是活躍于文壇的作家、詩人。《新小說》作家群體的壯觀由此可見一斑。
三
《新小說》作為通俗文藝期刊,鄭伯奇在編排和裝幀設計上也花盡心機,
第二卷第一期共刊發九篇小說,每篇都有插圖,達二十五幅。有的一篇就有三幅插圖,有的插圖畫面占一個全版。這在當時的文學刊物中是很少見的。刊物一出版,即獲得點贊。曹聚仁說:“《新小說》很好,畫和文字都有生氣。”陳子展說:“創作均有插圖,當益接近大眾矣。能做到雅俗共賞之通俗讀物。”張天翼說:“看到《新小說》極為高興,編制插畫都極吸引人。”
插圖作者都是年輕的畫家,但在書頁的狹小平面上展現出獨具的個性異彩。萬籟鳴以厚重的輪廓線條描繪人物形象;他的孿生弟弟萬古蟾的構圖則別具裝飾味道;楚人弓的人物特寫給人以強烈震撼;李旭丹的單線勾勒有一種動態的力量;黃苗子的素描筆觸略帶漫畫的效果;郭建英的線條單純柔美而又清晰流暢;馬國亮當時已是《良友》畫報的主編,是最本色的小品作家,他的插圖線條與黑色塊面交錯,明暗變化中富有意趣。其他畫家尚有陳元之、沈西等。《新小說》插圖的多彩多姿、花團錦簇,展卷披覽令人神馳意遠。
四十多年后,出版家丁景唐在《鄭伯奇在“左聯”成立前后的活動》一文中高度評價《新小說》,“內容豐富,編排新穎,插圖眾多,生動活潑”。特別指出:“小說、散文、譯文、游記,都配以眾多的美術題花、插圖、電影劇照,在當時文壇上別開生面。”肯定《新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史占有創新的一頁”。
鄭伯奇的《插畫漫談》(署名“平”,《新小說》第二卷第一期),有對插畫的精辟見解:“小說的插畫是幫助讀者欣賞的。插畫的作風若和小說的作風不一致,反來可以引起讀者由乖離而發生的不快感。但是,畫家要做到和原作者一致,倒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時候,嚴肅的作品會插上漫畫式的插圖;有時候,輕松的作品而插畫卻采取厚重的筆調。”他認為,缺少寫實精神的插畫,不合通俗化的旨趣。“呆板的模寫當然不就是寫實,但繪畫要引起觀者的寫實感是必要的。這一點,我們的插畫畫家能做到的并不多。”
四
《新小說》出版了六期,先后發表了十二篇關于文藝通俗化理論探討的文章,分別是第三期的《通俗的和藝術的》(平)、《通俗和媚俗》(樂游)、《偵探小說和實生活》(華尚文),第四期的《通俗小說和民話》(樂游)、《通俗小說形式問題》(華尚文)、《通俗文學和讀者趣味》(方鈞),第六期的《身邊的小說》(樂游)、《基本漢字》(華尚文)、《插畫漫談》(平),這一期還有任鈞翻譯的“通俗小說論集”,包括日本人片岡鐵兵的《通俗小說私見》、武田麟太郎的《通俗小說問題》、森山啟的《關于通俗小說》。實際上,十二篇中除去三篇譯文,其余九篇全是鄭伯奇的文章,“平”“樂游”“華尚文”和“方鈞”都是他曾經用過的筆名。鄭伯奇將他對通俗文藝的意見化整為零,一個個小題目深入議論問題的一個個側面,內中不乏精當見識。如論及藝術作品與通俗作品,他指出:“藝術的作品尊重獨創,通俗的作品注重常識,這的確是一個很好的對照。”(《通俗的和藝術的》)如區分通俗和媚俗:“通俗的作品只是作者把寫作的態度降低到一般人所能理解的水準上。這一點也許是妥協的,而這種妥協是正當的。若拋棄了作家的天職,只去迎合低級趣味,那就是媚俗了。”(《通俗和媚俗》)
五
編者說:“我們要出一本通俗的文學雜志,這雜志應該深入于一般讀者中間,但同時,每個作品都要帶有藝術氣氛的”;“我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都是能夠通俗的,都是能夠深入于一般讀者大眾中間去的”;“同時,有生命的通俗作品也都是在藝術方面很成功的。”編者認為通俗化和藝術性是可以統一的,“把作品分為藝術的和通俗的,這是一種變態。《新小說》的發刊,就是想把這種不合理的矛盾統一起來的”(第二期《作者讀者和編者》)。
這個愿望是好的,作家和讀者都很歡迎。郭沫若說:“《新小說》饒別致,文體亦輕松可喜,能于大眾化中兼顧到大眾美化(廣義的美),是一條順暢的道路。”段可情說:“內容甚好,編排亦佳。”“此刊物雖云系通俗文學之讀物,然亦不可過分將趣味降低,弟向來主張文學非帶藝術氣氛不可,否則使人有讀后無回味之感覺。”讀者也表示:“現代的文學界確實太缺少通俗化的作品了,貴刊之發行,真深合我們的需要。”
但是既要深入于一般讀者,又要在藝術上成功,做到二者的統一,談何容易。讀者反映:“有幾篇作品,仍不脫考據性質或名士氣,刊名新小說應當多登有故事的作品,以求成為大眾的普遍讀物。”“老舍蟄存兩先生的小說通俗則通俗矣,然有點‘紅玫瑰的氣味。”“考證文字與翻譯作品似都不是學校以外的讀者所喜歡讀的。”小說《唯命論者》和《一九二四三四》都受到好評,作家卻底氣不足。郁達夫說:“要把小說寫得通俗,真不容易。”“我自以為通俗小說,終不是我所能寫的東西。”張天翼說:“我覺得我那篇不大合式,因為這種文字只有讀書人能看,未能通俗。”
刊物的發行并不理想,但鄭伯奇對《新小說》的“通俗化試驗”仍充滿信心。第五期有編輯室的《征稿》:“本刊自第二卷第一期(通數第六期)起,改革內容,力求通俗化,除原有之小說,隨筆,中間讀物等外,特增加以下各欄,廣求外來文稿:(一)速寫
簡短的即景速寫。(二)通信
各地實際生活的通信。(三)民話傳說
荒唐無稽者不錄。(四)民謠時調
肉麻及迎合低級趣味者不取。(五)短劇
以能在短時間內演出者為合格。(六)讀者意見
對于本刊的意見和讀后感想。”意在強化刊物的重點并力求主旨統率下的多元化。第二卷第一期的開本改為二十三開,增加了篇幅。同時預告了第二期、第三期的重點文章:《晚清文學研究特輯》,由鄭振鐸、阿英等執筆;《上海動態點滴特輯》,將有二十位作家分工合作,從不同角度表現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編者相信第二卷會大有起色。
第六期在7月剛剛出版,《新小說》卻戛然而止,朋友們感到非常突然。停刊的原因,晚年的鄭伯奇這樣寫道:“我自己對于‘大眾化也缺乏明確概念,所以刊物的面貌既不統一又缺乏特色,雖然得到魯迅先生的熱情支持和不少青年作家踴躍投稿,刊物的發行量不高,影響不大,出到第六期,終于停刊了。”(《“左聯”回憶散記》)而趙家璧在《回憶鄭伯奇同志在“良友”》中道出了真正的原委:“8月下旬,(良友圖書公司)經理又和伯奇為了銷數、成本、稿費開支等問題鬧了一場。伯奇耿直為懷,經理錙銖必較。一怒之下,伯奇于第二天拂袖而去,從此離開了良友。”
新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糾結,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一個獨特的學術景觀。通俗文學回歸到中國現代文學史格局,從而初步形成一個雅俗兼容的大文學史框架,時間已到20世紀80年代了。
六
《小說的將來》是鄭伯奇在《新小說》上刊發的短文。他預言:“有聲電影和無線電播音是現在全世界最新最流行的藝術,在不遠的將來,電視(Tolevision)又有完成的希望。”這一定會對藝術各部門產生巨大的影響,尤其是小說將因此發生激烈的變革:
小說不單是作家一手包辦的東西,而變成和詩歌戲劇相同,要假借別個藝術家的媒介來和大眾相見。大眾不需要躺在沙發椅上一個兒去悶悶地看小說,借著電視和無線電的力量,有一個媒介的藝術家用肉聲的言語把小說送到大眾的面前。
今日影視和手機屏幕上展現的令人炫目的小說樣式,已遠遠超出八十年前鄭伯奇的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