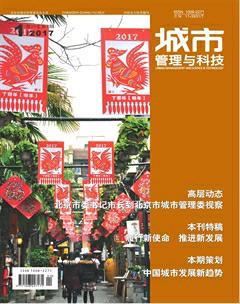倫敦城市群環境治理的重要特征和主要經驗
王玉明
一、引言
倫敦城市群是當今六大世界級城市群之一。從1960年代開始,英國強力治理倫敦城市群的大氣污染和泰晤士河流域污染,經過數十年的治理,倫敦市摘掉了“霧都”的帽子,泰晤士河恢復成為一條潔凈的河流。
在倫敦城市群的環境治理中,各級政府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中央政府通過立法和區域戰略規劃,為區域環境治理制定行為準則和提供指導。大倫敦市政府和區域政府辦公室、區域發展局和區域議事廳共同推動倫敦大都市區的整體發展。泰晤士河水務局的設立和高效運作,促進了流域政府間的合作治理和一體化管理。同時,政府組織以外的社會主體也積極參與區域內的環境治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與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既是倫敦城市群環境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環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經驗。
二、倫敦城市群概貌
倫敦城市群形成于20世紀70年代,在空間結構上包括四個圈層:一是內倫敦,這是城市群的核心區,包括倫敦城及內城區的12個區,面積310平方公里,其中倫敦城是核心區,面積只有1.6平方公里;二是倫敦市或大倫敦地區,包括內倫敦和外倫敦的20個市轄區,總面積1580平方公里;三是倫敦大都市區,包括倫敦市及附近郊區的11個郡,總面積11427平方公里;四是倫敦城市群即包括倫敦城、內倫敦和外倫敦,以及鄰近大城市在內的大都市圈。以倫敦-利物浦為軸線,包括倫敦、伯明翰、謝菲爾德、曼徹斯特、利物浦等數個大城市和眾多中小城鎮[1]。這一地區總面積約4.5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18.4%;人口365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64.2%。
在倫敦城市群內,倫敦既是英國的首都,是該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也是英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和交通樞紐。與此同時,城市群還擁有伯明翰、曼徹斯特、利物浦等一批次級中心城市。該城市群是英國產業密集帶和經濟核心區,也是世界五大城市群之一。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業革命和走上工業化的國家。19世紀中期,隨著人口增長和現代工業的發展,英國的“城市病”和環境問題日益突出,集中表現為水體和空氣污染。造成倫敦城市群空氣危害的主要是煙塵、濕霧和有害氣體,如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主要出自以煤為燃料的各類工廠和家用爐灶,可稱之為煤煙型污染[2]。呼吸系統疾病肺結核、支氣管炎、肺炎等是當時非常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3]。從1960年代開始,英國強力治理大氣污染。上世紀70年代后,倫敦市摘掉了“霧都”的帽子。2010年大倫敦城市區PM10年均值達標[4]。
倫敦城市群的水污染集中表現在泰晤士河流域的污染上。泰晤士河是倫敦城市群的一條重要河流,流經英國南部六郡,向東流往倫敦,橫貫倫敦與沿河10多座城市,被稱為英國的“母親河”。泰晤士河流域有人口1200多萬,流域中經濟最發達、人口最稠密[5]。流域西部為農業區,中部泰晤士河谷為高科技工業園區,東部為倫敦市。自19世紀工業革命開始,河流兩岸人口激增,大量的工業廢水、生活污水未經處理直排入河,沿岸垃圾隨意堆放,泰晤士河水質迅速惡化,病菌滋生,乃至魚類絕跡[6],成了一條舉世聞名的臭河[7]。70年代頒布新的《水資源法》后,泰晤士河流域進入了一個綜合治理時期,1980年代的河流水質很快恢復到了17世紀的原貌,達到飲用水標準。泰晤士河治理的成效不但令英國為之自豪也為世界所矚目。
在倫敦城市群的環境治理中,各級政府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英國,三級政府構架包括中央政府、地區性政府(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與地方政府。其中,地方政府構成較為復雜,并且不斷變動。第一層為郡、郡級市,大倫敦郡議會;第二層為郡屬區、自治市鎮;第三層為教區和社區議會[8]。除了各級政府之外,企業、環保組織、大學、社區與媒體等社會力量也積極參與倫敦城市群的環境治理。
三、中央政府對環境治理的頂層設計
英國是單一制國家,地方事務受到中央政府的強力干預。中央政府在倫敦城市群環境治理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在治理計劃中的一切政策行為皆在中央政府的控制監督之下[9]。
面對倫敦都市區和泰晤士河日益嚴峻的環境形勢,英國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法律法規,規范指導大氣污染和水污染治理。1876年,英國議會通過了《河流防污法》,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國家立法,也是世界上第一部水環境保護法規。為了防止倫敦市區空間蔓延,20世紀40年代,英國議會專門制定了《綠帶法》,通過環城綠化帶將倫敦大都市包圍,把倫敦大都市圈分為倫敦城中心、內倫敦和外倫敦。1974年制定的《空氣污染控制法案》嚴格規定了工業燃料中的含硫上限。1995年頒布的《環境法》規定,各個城市都要進行空氣質量的評價與回顧,對達不到標準的地區,政府必須劃出空氣質量管理區域,并強制在規定期限內達標[10]。
為了保護大倫敦都市區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英國政府多次編制了大都市區戰略規劃。
1937年,為解決倫敦人口過于密集的問題成立了巴羅委員會。1944年編制的《大倫敦規劃》將大倫敦都市區劃分為四個同心圓:內圈、近郊圈、綠帶圈、鄉村外圈。內圈是控制工業、舊城改造、降低人口密度、恢復功能的地區;近郊圈作為建設良好的居住區和健全地方自治團體的地區;綠帶圈的寬度約16公里,以農田和游憩地帶為主,嚴格控制建設,作為制止城市向外擴展的屏障;鄉村外圈計劃建設8個具有工作場所和居住區的新城,從中心地區疏散40萬人到新城[11]。
為了疏散倫敦市區的人口和功能,到上世紀50年代末,在距倫敦市中心50公里的半徑內建設了8座衛星城,有效控制了倫敦城區無序蔓延的勢頭。1994年頒布的《新倫敦戰略規劃建議書》提出構建“新倫敦都市區”,對環境高度關注,除大氣、水體、噪聲等問題外,還包括對一些重要空間要素的整治,如開放公園、廣場綠帶、歷史遺產等地的空間、街道和廣場,更加注重空間規劃與產業規劃、功能規劃相協調。特別是2004年頒布的《倫敦規劃》是倫敦未來數十年發展的最重要的規劃文件。該規劃將大倫敦劃分為5大現代服務業功能區,進一步將某些具體區域界定為機遇區域、強化區域和重建區域[12]。這些規劃是中央政府指導倫敦城市群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重要文件,有效優化了大倫敦地區的空間布局,引導產業和人口有組織外遷,推動了倫敦城市群在經濟、社會、交通、環境等方面的協調發展。
四、區域政府對環境治理的協調推動
在大都市地區的政府結構中,倫敦地區最早出現了區域性機構和地方單位之間權力分享的雙層、聯邦式結構[13]。
為了倫敦都市區的綠地建設,適應城區開放空間的擴大、中心城區人口密度降低、平衡周邊區域發展的需要,1964年創立大倫敦議會,作為區域政府專門負責整個大倫敦地區的發展和協調管理,承擔戰略規劃與協調發展職能。1986年保守黨政府廢除大倫敦議會,將其履行的眾多職權移交給了32個自治市議會和倫敦城法團及其委員會,比如城市規劃、道路、橋梁和街道的維護,垃圾和下水道的管理,防洪以及司法判決等。此后通過實踐,這種多頭分散治理的格局制約了大倫敦地區的整體發展,使得大倫敦地區各種“城市病”凸顯[14]。為此,英國工黨政府1999年頒布《大倫敦市政府法案》(Greater London Authority Act 1999)。根據該法案,2000年成立大倫敦市政府。大倫敦市政府由倫敦市長、倫敦地方議會組成,統轄整個大倫敦地區的32個自治市和1個倫敦城。
大倫敦市政府的主要職責是戰略規劃指導,對交通治安、消防應急、經濟發展、環境衛生以及其他社會服務負責,研究制定倫敦發展戰略規劃,致力于實現大倫敦地區的經濟、社會、環境整體協調發展。大倫敦都市區實行大倫敦市政府-自治市議會雙層治理結構。大倫敦議會是一個擁有權力和稅收基礎的民主合法機構。倫敦的大多數服務項目包括教育、社會服務、住房、環境健康和消費者保護等,由32個倫敦城區來提供[15]。而交通和環境(如廢物收集處理與污染防控)等事務則與大倫敦市政府共同管理。
上世紀80年代,英國成立了蘇格蘭、威爾士發展局,負責處理區域內的投資和管理事宜。此后在中央政府成立了區域政府辦公室,主要負責協調歐盟的區域政策在英格蘭地區的執行。嚴格講,這些區域政府并不是一級真正意義上的政府,更多地具有中央政府派出機構的特征[16]。
1998年,英國頒布《區域發展局法》,根據這個法案成立區域發展局和區域議事廳,建立區域層級的合作政府。1999年在英格蘭除倫敦郡以外的8個地區建立了區域發展局,2000年在倫敦郡建立了區域發展局,從而形成了一個以區域政府辦公室、區域發展局和區域議事廳為主體的治理結構[17],其中區域政府辦公室是在國家層面將不同的部門政策進行整合,同時體現區域優先發展的重點,對區域的土地利用進行規劃。區域發展局主要負責領導地區的經濟發展,同時還監察各個次區域的伙伴關系及其在地方實現。區域議事廳主要由一些地方議員和其他組織成員組成的志愿組織,負責制定區域發展戰略和檢查執行情況[18]。由于這3個部門更多的是代表中央政府,此后英格蘭各地區也成立了區域議會。這些機構在全國和區域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五、專門機構對環境事務的具體管理
在倫敦大都市區環境治理中,區域性或流域性的環境管理機構發揮了重要作用。
早在1751年,英國喬治二世時期議會通過法案,成立泰晤士河管理局[19]。該機構管轄克里科雷德至斯坦尼斯大橋這一段水域。成員包括來自泰晤士河流域的議員、泰晤士河邊城鎮的市長和其他官員、倫敦市長和市議員、牛津大學的官員和一些學院的領導以及諸多教區的官員,此外還有一部分宣誓加入大土地的所有者、地產繼承者、擁有大量個人財產和債券持有者[20]。
19世紀30年代,英國政府針對倫敦污染問題,開始考慮設立都市性權力機構對都市區實行統一管理。1848年成立都市下水道委員會,擬將都市區的下水道、排水和供水等相關職能置于都市統一管理,以期改善都市區的衛生狀況[21]。1856年成立新的機構——泰晤士河管理委員會,由其負責西起斯坦尼斯河東至延特勒特河口的泰晤士河管理。該委員會的委員主要來自港務局、海軍部和商務部,代表城市和航運利益。該機構雖然規模比較小,但權力比較廣泛,對泰晤士河流域的治理進行計劃安排、監督和糾紛處理[22]。
1973年,英國制定《水資源法》,改革水管理體制,分別建立以城市或工礦區為中心的水污染防治體制和以水體為中心的區域性污染防治體制。針對泰晤士河流域的生態整體性和區域關聯性,采取區域性污染防治體制,特點是以流域為主體,做到點、線、面相結合,體現多目標、多層次、多因素的綜合治理[23]。1974年,英格蘭-威爾士組建了10個新的流域水務局,泰晤士河水務局隨之建立。這些機構除提供污水處理和供水服務外還負責流域管理、水污染防治、防洪及地表排水,承擔推進和協助流域水治理工作,統一負責流域治理與地表地下水資源管理,包括水文水情檢測、工農業及城市供水、污水處理與排放、水質控制、防洪、水產、水上旅游等。規定凡從泰晤士河取水的公司或廠礦企業必須由水務局發放許可證并繳納許可證費,審批、監測的原則是取水量不得影響泰晤士河流域生態和植被環境;任何向泰晤士河排水的單位,污水必須經過處理或由水務局收取費用后集中進行處理。
泰晤士河水務局的設立和高效運作,推動了流域政府間的橫向聯動,促進了流域政府間的合作治理和一體化管理,造就了今日干凈的泰晤士河。撒切爾夫人上臺后,1989年對水務管理局實行私有化改革,水務管理局成為泰晤士河水務管理公司[24]。政府通過建立專業化的監管體系,負責財務、水質監管等,實現了經營者和監管者的分離。泰晤士河水務公司只承擔供水、排水、污水處理職能,不再承擔防洪、排澇和污染控制職能,水質檢測、污水監管、檢舉起訴等權力收歸全國層面的國家河流管理局,但該公司仍然是泰晤士河治理的重要主體。泰晤士河水務公司經過近十多年的公司化運作,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提高服務標準方面取得了很大進步。
六、多元主體在環境治理中協同行動
在倫敦城市群的環境治理中,英國中央政府、大倫敦市政府、區域政府辦公室、自治市政府、區域發展局和區域議事廳,以及專門環境機構都是治理機構的重要主體。同時,政府組織以外的社會主體也積極參與區域內的環境治理。地方政府間的合作行動與社會主體的廣泛參與是倫敦城市群環境治理的重要特征,也是環境治理取得成效的主要經驗。
在環境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主要表現在大倫敦市政府、倫敦市與各自治市之間的合作和協調。
大倫敦都市區不是大倫敦市政府壟斷所有的地方行政權力,而是與各地方政府一道,共同分享大倫敦區的行政權,合作展開公共治理。特別是在關于環境保護(如跨界生物多樣性、大氣排放、水質保持等流域環保)方面。雖然大倫敦市政府在層級上高于倫敦市和大倫敦區內的自治市政府,但是33個自治市仍然處于自治狀態。
大倫敦市政府與倫敦自治市議會之間職能分工明確,權責劃分清晰,避免了兩級政府之間互相推諉,有利于發揮各自的優勢,有利于彼此合作和意愿的表達。大倫敦市政府與32個自治市和倫敦市政府共同推動了中央政府采取彌補方案,以增加充盈流域的治理經費[25]。大倫敦市政府與各域內政府的協調更多地是流域內統一行動和發展規劃,著重于執行全國環境政策,以便步調一致分工協作。從大倫敦市的空間關系看,倫敦城、內倫敦與外倫敦各區域的地方政府所面臨的問題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倫敦城、西倫敦、東倫敦、南區、港口區與郊區的劃分方法,泰晤士河流域的環境保護與生態建設的具體任務存在區域性差別。因此,不同區域的地方政府間必須充分溝通,進行有效合作[26]。
倫城城市群環境質量的改善不僅有政府的努力,企業、環保組織、各大高校、社區與媒體等社會力量也形成了合力。
在英格蘭的區域政府辦公室、區域發展局和區域議事廳中的論壇、網絡體系和委員會中吸納了大量的區域伙伴組織參與,這也是英國政府區域治理的一個基礎[27]。
在英國,私有企業對改善空氣環境的創新和投入絲毫不亞于政府。例如,金融企業野村證券公司參與倫敦舊城公司發起的城市空氣項目,有效合并了食品、辦公設備的投遞和垃圾的清運,以減少排放量大的垃圾車運輸次數。私有化改革后的泰晤士河水務公司承擔倫敦和泰晤士河流域的飲用水、生活用水供應和污水處理。該公司向社會籌措資金,向排污者收取排污費,通過發行股票募集資金。同時,這家私營公司也受到了政府、環保組織、公益機構、媒體和公民“無情”的監督[28]。近年來,在這種“無情”的監督和該公司的努力下,泰晤士河流域的污染得到了嚴格的控制,受到世人好評。
參考文獻
[1]王紅.借鑒“倫敦規劃”,改進戰略規劃編制工作[J].城市規劃,2004(6).
[2]梅雪芹.19世紀英國城市的環境問題初探[J].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3).
[3]Stradling,D .& Thorsheim,P.The Smoke of Great Cities,British and American Efforts to Control AirPollution[J].1860-1914.Environmental Histry.1999(4):No.1,8.
[4]倫敦如何告別霧都?[N]西安日報,2013-1-16.
[5]余敏江,黃建洪.生態區域治理中中央與地方府際間協調研究[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P245.
[6] Sauvain,Philip A.British Economic andSocial History 1700-1870[M].England:Stanley Thornes Ltd,1987.P214.
[7]陳思模.國外一些河流和流域水污染防治與管理的主要經驗[J].水利科技,1992(2).
[8]戴維·威爾遜,克里斯·蓋姆.英國地方政府[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P12。
[9]余敏江,黃建洪.生態區域治理中中央與地方府際間協調研究[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P246.
[10]倫敦如何告別霧都?[N]西安日報,2013-1-16.
[11]王紅.借鑒“倫敦規劃”,改進戰略規劃編制工作[J].城市規劃,2004(6)
[12]劉江華,楊代友,張強,陳來卿.整合與超越——廣州大都市圈發展研究[M].商務印書館,2010,P91-92.
[13]Teaford,Current Municipal Affair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Feb.,1912,p.91.
[14]高秉雄.倫敦大都市區治理體制變遷及其啟示[J].江漢論壇,2013(7).
[15]戴維·威爾遜,克里斯·蓋姆.英國地方政府[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P77-79.
[16]王鳳鳴,李艷. 英國新工黨的憲政改革[J]. 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03(2).
[17]Cabinet Office of Britain.Reach Out[R/OL].http://www.cabinetoffice. gov.uk/strategy/dewnloads/so/reaching/regions/reaching-ant.pdf,p77.2016-5-05.
[18]曾令發,耿蕓.英國區域治理及其對我國區域合作的啟示[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1).
[19]毛利霞.19世紀中后期英國關于河流污染治理的博弈[J].理論月刊,2015(2).
[20]Luckin,Bill.Pollution and Control: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ames in the 19th Century[M].Bristol:Adam Hilger,1986.
[21] John R·Green wood,Developnent Planning in the English Metropolitan Counties:A Comparison of Performance under Two Planning Systems,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Britain,Regional studies, 1993(7).
[22]Breeze,Lawrence E.The British Experience with River Pollution,1865-1876[M].New York:Peter Lang Publishing,1993.
[23]湯建中等.城市河流污染治理的國際經驗[J].世界地理研究,1998(2).
[24]戴倩.泰晤士河綜合治理實踐[J].水利水電快報,2006(19).
[25]余敏江,黃建洪.生態區域治理中中央與地方府際間協調研究[M].廣東人民出版社,2011,P251.
[26]Blair, T. Leading the Way: A New Vision for Local Government, Londo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1998.
[27]曾令發.探尋政府合作之路——英國布萊爾政府改革研究[M].人民出版社,2010.P241.
[28]焦東雨.泰晤士河管理為何私有化[N].中國周刊,2013-06-21.
(責任編輯:李靜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