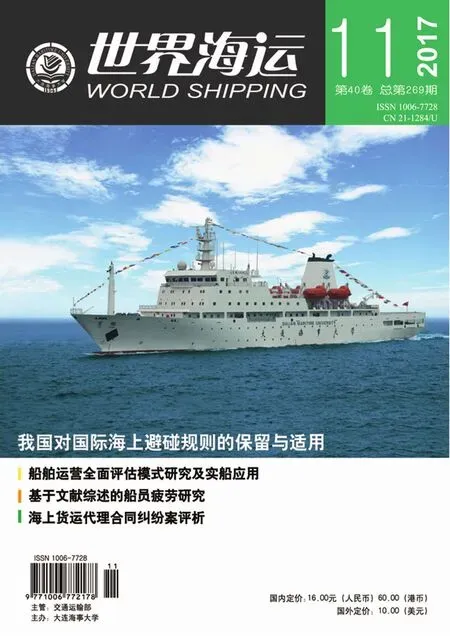海上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評析
王正宇
海上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評析
王正宇
貨運代理接受委托后轉交他人實際辦理委托事務形成的法律關系及在該法律關系下各方的權利義務的確定是運輸實務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對于此問題,從合同相對性及表意行為的構成要件等方面可以查明委托人同意轉委托的意思表示應當是明確、具體的,不應適用默示推定原則。從法律規定、第三人身份界定的角度也可以對委托關系下產生的代理與轉委托予以明確區分。
[案情]
B公司與C物流公司簽訂海運代理合同,約定C物流公司為B公司提供貨物陸路、海陸運輸的物流服務,C物流公司不得轉讓或讓渡合同或合同的任何權利。C物流公司與A物流公司簽訂了海運代理合同,約定A物流公司為C物流公司提供陸路、海陸運輸的物流服務。A物流公司又通過其代理人實際完成了B公司委托C物流公司辦理的貨運代理業務,并墊付了費用。B公司確認C物流公司向其報送的預定運價后,貨物起運,待貨物交付海運后,C物流公司向B公司報告海運情況。C物流公司與A物流公司對賬后確認拖欠其費用2 387 380元,但以B公司未支付為由欠付上述費用。
[爭議]
合同法第四百條、第四百零三條的如何適用。
[審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根據涉案運輸中A物流公司、B公司、C物流公司各自負責的事項和實際操作,結合涉案兩海運代理合同,證明B公司委托C物流公司辦理貨物陸運、海運運輸,C物流公司接受委托后又將上述委托事務部分轉委托A物流公司。B公司收到了C物流公司的海運報告和發票僅是體現了雙方之間貨運代理合同的履行結果,并不能構成對C物流公司轉委托的同意或追認。B公司也未直接向A物流公司作出委托指示,故依據《合同法》第四百條,C物流公司的轉委托未經B公司同意,A物流公司作為次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B公司主張代理相關費用。一審判決,C物流公司給付A物流公司代理相關費用。
二審法院認為,C物流公司當庭陳述其與A物流公司簽訂雙方協議時向其披露了C物流公司的委托人是B公司,并要求其開具以B公司為抬頭的發票。依據《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的規定,C物流公司以自己的名義在委托人B公司授權范圍內與第三人A物流公司訂立合同,第三人A物流公司知道C物流公司與B公司之間代理關系的,該合同直接約束B公司與A物流公司。本案不存在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C物流公司與A物流公司的除外情形。二審改判為B公司向A物流公司給付代理相關費用。
[評析]
委托關系下會產生代理關系,同樣也有轉委托情況存在,但代理與轉委托的法律規定及后果不同,關鍵在于對“第三人”身份的區分。
(1)在代理關系中,一種為顯名代理,即直接約束被代理人,一種為隱名代理,即《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的規定,其合同介入權不同。兩種代理形式中選定的“第三人”應是委托人(被代理人)要求受托人(代理人)尋找的實現交易行為的合同相對方,比如要受托人(代理人)尋找的承運人、報關行、港口經營人等,使委托人直接或間接地與前述第三人建立合同關系。
(2)在轉委托關系中,除非有明確轉委托的授權,受托人尋找的次受托人不是前述委托人意欲尋找的作為合同相對方的“第三人”,仍是促成交易實現的受托人。轉委托行為本身不符合代理行為的法律特點,當然不能認為是代理行為。《合同法》第四百條所規定的“第三人”僅指向次受托人,與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的“第三人”范圍所指截然不同。
筆者認為,本案中,C物流公司雖在庭審主張其與A物流公司訂立合同時聲明是B公司的代理人,但C物流公司通過該合同沒有尋找交易實現的合同相對方,不是代理行為,故A物流公司不是《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的“第三人”,而是《合同法》第四百條的“第三人”;A物流公司沒有為B公司實際運輸,而是繼續尋找承運人,進行的是貨運代理業務,與C物流公司實為轉委托。該轉委托未經B公司的同意,不應適用《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條、第四百零三條的規定。
10.16176/j.cnki.21-1284.2017.11.011
王正宇(1983—),女,大連海事法院海商庭法官,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