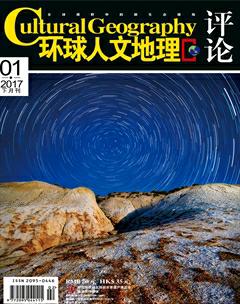從區域地理到中國地理學的復興
居珈名
區域地理是中國地理學的偉大傳統,從我國的古代典籍中就能夠發掘很多有價值的地理資料,對于研究我國地理相關科學知識有著極為重要的支撐作用。不論是農業、軍事、政治、旅游、經貿、人文都或多或少與地理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地大物博和復雜的地理因素吸引著無數地理愛好者專研我國的地理學,為我國地理學奉獻出無數心血,成就了我國地理學的發展。
早在五千年前,華夏文明剛剛開始的生活,《山海經》就已將神州大地依據四海八荒進行劃分,人們開始第一次見識到這個世界的廣袤;隨后的各個朝代中不乏一批批優秀的地理學家誕生。其中,最令人記憶深刻、為地理學做出重大貢獻的學者莫過于唐朝著名的地理學家酈道元撰寫的有關我國水系著作——《水經注》,明朝的地理學家徐霞客用幾十年的時光潛心撰寫地理游記著作——《徐霞客游記》……無論是有心抑或是無意,古往今來的中國地理學著作都是以區域的劃分作為立身之本的要素,他們專研地理要素的某一方面,真正讓人們深入了解我國區域性地理知識。所謂的區域性地理知識可以認為是一個區域,如:平原、高原、丘陵、山地、盆地等等;也可以認定為某一地理現象,如:河流、土壤、水質、氣候等進行分類。然而到了近代,清政府對自然科學的強勢打壓,連年戰亂造成人才凋敝的現狀,中國地理學一度沉淪無聲,這段時間里,可以說我國在地理學方面沒有進步,人們紛紛為營生而堅強的活著。好在1943年隨著國民政府對國境問題調查的展開,中國地理學從故紙堆中被喚醒,在現實中再次熠熠生輝,這是我國近代地理學開端的一個重要時間節點。
1957年,中科院應國務院之邀,開展了一項名為“綜合自然區劃”的課題 。這項與“大躍進”運動同日開展的研究,是那個荒唐年代里罕有的的存在。新中國地理學的奠基者們:竺可楨、黃秉維、任美鍔……一個個承前啟后的大家們,此刻就坐在北京飯店一間逼仄的會議室中,延續著中國地理學的偉大傳統。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領域都需要一批前赴后繼的革命者們,而這些人就是地理學的革命者,他們把過去我們丟掉的文化再一次從廢墟中撿回來,深入研究我國地理學文化,為我國當代的地理學文化的研究起到了重要的奠定基礎的作用。
在近二十年的工作中,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對于地理學的研究,尤其是美國、澳大利亞這類國土面積較大、自然科學發達的國家,因為地理學對于一個國家的自然環境、生態發展、人文科學、生物研究、農業升級、氣候監控、海洋問題、資源勘測等方面都有著直接的聯系。我國學者們同樣延續著前人們的腳步一如初始般心無二意地踏實前進。然而,這種研究也對于過去的地理學提出了更多的新的挑戰和問題,對于我國地理區域的劃分有了新的見解和分析。其中不乏多種不同的聲音:有提議按民間傳統來的,這類科學家們重視人文地理對于一個區域的影響;有采用溫度條件、水分狀況和地貌因素等基本地理學要素來劃分的,這類學者對于地理條件的本質因素更加重視;也有基于教學目的,這類學者對于人們的接受能力和未來的研究方向更加接近;還有按照工農業發展而劃分的,這類學者同樣也是著重人文地理的作用;其間自然是眾口難調,最突出的一個問題,便是關于亞熱帶的劃分,這個問題一直都成為我國地理學上面一個爭議較大的區域劃分。
中國是一個季風氣候顯著的國家,加之中部地區地勢平坦,來自印度洋與太平洋的暖濕氣流極大地改變了中國的氣候分布,特殊的地形和海洋、季風的影響導致很多同緯度的地方有著不同的氣候類型。如果按照國際盛行的年積溫與7月均溫的劃分方法,中國的亞熱帶北界甚至可以延伸至哈爾濱!當然,這種劃分肯定是有問題,畢竟哈爾濱的冬季氣溫可以達到零下20度攝氏度,明顯不符合亞熱帶區域對于溫度的要求。這些在和煦的地中海地區百試不爽的標準,在易遭西伯利亞南下寒潮侵襲的華夏平原,自然是極為不符。俗語道:“入鄉隨俗”,在地理學也有著相關的案例存在,也就說地理學的復雜甚至不能用已經沿用多年的理論來定義,特殊的地區需要靈活多變才能夠符合當地的區域劃分。
在諸多地理學大家的本土化方針之下,我國亞熱帶北界最終定在了“秦嶺—淮河”一帶,南界定在了北緯22°左右的地區。*1 在這樣的劃分中,廣州一下子從熱帶變成了亞熱帶,看似出乎意料,實則情理之中。由于中國的自然區劃是為農業服務的,因而才有了如今“東七四二一海洋”的格局。試想如果將廣州劃入熱帶,那么中國就又多了一處不定時受寒潮侵擾的橡膠種植地。*2 若是以欣賞中國景觀之美為目的進行一場區域劃分研究,人們就不會把南嶺之南這些榕樹蔥郁、紅棉似火的南國之地與長江流域小橋流水、人家枕河的江南都當做亞熱帶了。所以,選擇什么樣的標準來決定區域,這個問題在自然界找不到答案。做什么樣的選擇,必須由地理學家按照他對其重要性的主觀判斷而定,因此不能談什么區域的真偽,只能談目的性的有無。
可以說,區域是客觀世界的反映,而區劃方案是人為建構的知識體系。其它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都是一清二楚的,唯有區域地理學,是自然與人文共同的后代,需要學者們憑智力活動來構建自己的研究對象,因而區域的本質是一個容器,是一個不存在定論的學科。例如青藏高原的再劃分中,無論是黃秉維方案的完整性,還是任美鍔方案的分裂性,都是人為的側重某一方面所賦予它的。那么,我們的地理學家也不能肯定未來的地理區域就不會發生變化,隨著全球氣溫的變暖、動植物的活動范圍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冰川融化為水汽,沙漠化的進一步加深,人類的各類活動、土質的變化等等因素都可能決定著地球生物的變遷和區域的變化。大地是一幅畫,但不是用馬賽克鑲嵌而成的。畫面上每一平方厘米的部分可能看來都有自身的“個性”,但實際上沒有一個部分是獨特的單元個體。我們在地表上劃出的任何一片區域,都不會是一個統一的整體,而只是一片任意選定的土地,甚至自然的完整性與整體性是不會受制于國界的。我們否定卻也需要著地域。江南、塞北、中原、北境、嶺南、西域,研究區域,并非只是在研究一個冷冰冰的課題,更是在研究中國民族生存空間之形成發展。只有認識“區域”的人為性與建構性,才能在地球上畫出更有用的圈,更美的圈。愿中國區域地理學繼往開來,生生不息!
注:部分資料引自《黃秉維<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