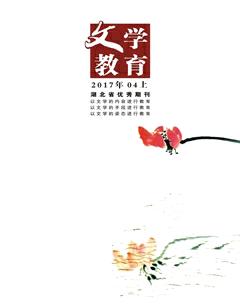抒情自我與現實反應
趙目珍
中國文學傳統從整體而言就是一個抒情傳統,而詩歌更是“以其‘抒情功能,在社會生活上起著重要作用,使得人際互動不止于實利物質,還有其精神情感的一面。”(陳國球《“抒情”的傳統》)然而,中國新詩自“第三代”以來,反抒情的趨向愈演愈烈,似乎詩歌以傳統的抒情手法來表現已成為一種相對“落后”的寫作方式。其實,認真觀察中國新詩的百年傳統,抒情仍然占據著一個突出地位。新世紀以來,現代詩中的抒情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回歸。80后詩人中的楊慶祥是一個良好的例證。
楊慶祥在其詩歌中表現出了一個強有力的抒情自我。盡管在《看見一棵樹很后悔》一詩中,他宣稱:“長成一個人真是件無趣的事”,但是在“黑暗之心”中,面對“親愛的”,他仍然選擇了“哭泣和愛你”(《我選擇哭泣和愛你》)。他為“很多人不知道為什么要愛”而憂心忡忡,他認為“把眼淚給了該給的人/就可以死了”(《于是很多人哭起來》)。詩者,情動于中而形于言。這樣的話語一定是情愫殷勤的人才能說出。其實,楊慶祥的詩歌能夠寫得平正自然而且動感充盈,正是其內在情思不斷涌動的結果。
詩人觸物事而興詠,常常會有很多感慨。楊慶祥的詩歌也常常因物因事而興。比如其《春夜獨飲不醉》顯然是因自己在春夜中飲酒而起,《我走進人間的煙火》是因洞察現實之后的感喟而起;而《貝殼》《雨雪天登黃鶴樓》《看見一棵樹很后悔》等則顯然是因貝殼、黃鶴樓、一棵樹等事物而起。然而盡管如此,詩人卻并不因這些情事而無端放縱自己的情感,這些情事只不過是詩人借以發揮的一個“據點”。如果取深層次的情感指涉而言,“抒情自我”的主體性才是詩人要顯現的意志根本。如其《春夜獨飲不醉》,雖然以“有多久”的時間類比來制造情感的波動起伏,以“明月”“山水”來襯托情感軌跡的逆向反差,然而詩人真正要歸結的卻是:“當我一口飲下蕭條的春夜/有多少人獨自走過多少花獨自開放”。這是一種獨處“春”與“酒”兩種美好事物之下的肅穆孤獨感,也體現了詩人借“春”“酒”以銷憂的內在情志。與此對比,《雨雪天登黃鶴樓》則是詩人通過對“鶴”的情感設定來找尋一個幻化中的自己,亦即那個與“鶴”相愛相知的少年。詩歌起筆以“來遲了”點出,這是詩人以抒情自我占據高位的一個象征,而黃鶴樓不過是一個物性的對立面。這種抒情自我的主體性還體現在詩人雖以“樓”為興起的對象,然而通篇卻只以“鶴”為楛矢,最后又以人之遐想為指歸:“罷。罷。生與死都是人類的設定。飛與不飛/都抵不過冰冷的鐵流。/雨雪天登黃鶴樓。請問,那與鶴相愛的/少年去了哪里?”毋庸諱言,這兩首詩都是在宣示個體的風塵閱歷與情感沉浮在內心當中的聯翩起舞以及二者在矛盾沖突中所造成的美妙中和。亦且尤為難得的是,詩人不僅借助平常物事實現了抒發情性和拓展意志的目的,還為詩歌營造出難得的靈性和虛境。這是一種藝術的玄思,更體現出對人性的自我關懷。
然而亦不能不說,楊慶祥的詩均是對現實存在的一種反應。現實存在最大的籠罩莫過于實實在在的人世生活。楊慶祥也難逃這一網幕。不過,對于人間煙火,他抱持的是一種樂觀的態度。“攪動牛奶的勺子”“鄰人廚房的切菜聲”“送快遞的小伙子低頭看單的神情”都是讓他快樂的源泉。不過,要想真正得到這種快樂的趣味,卻并非易事。幸好,楊慶祥懂得“將自己放棄”,然后走進人間的煙火去體味那合而為一的真實。(《我走進人間的煙火》)不過,為“抒情”而沉思總還是要帶來一些沉痛的憂患。“皇帝的屁股坐龍椅/宮娥的小腳穿金蓮//書生們念起了歌頌的華章/哎呀呀//一個公鴨般的嗓子高聲問:/誰還沒有閹割?”(《逆水寒第三》)這看起來遠離塵世的“文化守望”,其實隱存了詩人對世道浸壞的“惻隱”,大有對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感遇。然而最讓人心耽的怕還是對個人所處家國“情實”以及塵世“運轉”中所藏百變危機的憂慮:“警察選擇了制服/和辣椒水//霧霾選擇北京/受難者選擇口罩和沉默// 時間在不同的世紀/選擇不變的君王//黑暗選擇遮蔽一切/黑暗已經遮蔽了一切啊”。
在當下甚至是近三十年來的詩歌寫作中,將“情”視為詩歌的立命之本似乎已成為一件新鮮事。然而細觀新詩傳統的繁復面貌,“抒情”依然隱隱滲透,并且成為貫通新詩百年之齡中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楊慶祥是中國文學抒情傳統中的一個優秀個體。
(趙目珍,詩人,批評家。深圳職業技術學院人文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訪問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