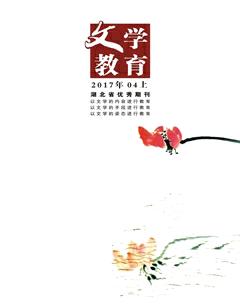《白象似的群山》的“冰山化”敘事特征
內容摘要:作為“冰山”原則的積極踐行者,海明威的作品中無不滲透著“冰山化”的敘事痕跡,詮釋著“極簡”與“至美”的美學轉化。本文將以海明威的經典短篇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作為研究對象,根據敘事學理論,分析闡述小說在敘述視角、敘述時間、敘述空間上所采用的“冰山化”的敘事策略。
關鍵詞:海明威 《白象似的群山》 “冰山化”的敘事策略
1954年,海明威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其獲獎理由是“精通于敘事藝術”。其短篇小說《白象似的群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就是對此的最佳印證。這篇發表于1927年的經典小說篇幅極其短小精悍,全篇字數不足1500字,可謂用字“極簡”。但是,又正是這部作品讓讀者見證了海明威這位語言大師對語言的精湛使用以及對敘事的緊密安排,無處不在的象征手法體現著作品的“至美”美學價值。
“冰山理論”最先由弗洛伊德提出,他認為人格如海中的冰山,人格中有意識的部分只露出了一角于海面,而人格大部分是無意識的,且潛藏于海面以下。這一理論由海明威運用在了文學創作領域,他個人多次表示文學創作如冰山,八分之一露于水面之上,由簡潔的文字和豐富的形象所展現,而剩余的八分之七則藏于水面之下,是等待讀者去挖掘的思想內涵。
小說《白象似的群山》講述了發生在一位男士與女孩吉格之間的對話。從表層文本,我們看到美國男人和女孩吉格在西班牙北部的一個火車站等待從巴塞羅那開來的列車,因天氣炎熱,兩人來到車站附近的酒吧喝飲料,他們的話題從對面的白色群山說到了男人勸說女孩去做的手術,他們的對話一度很緊張,以致于女孩請求男人不要再繼續說下去,因此,這個手術極有可能是人工流產。而男人言辭行動表現殷勤,似乎不愿意因為這個手術而結束與女孩的關系。小說最后以男人到車站放好旅行包,女孩回之以微笑并心情轉好而收尾。
正如海明威希望留下更多的空間讓讀者去猜測,文學批評者對這篇小說有著各種各樣的闡釋。本文則旨在通過敘事學理論,揭示小說背后所隱藏的社會悲劇性。
一.攝影式外視角與“白象”凸顯
《白象似的群山》中,敘事視角僅僅關注故事中美國男人、女孩吉格和酒吧女人的外在言行,所以是外視角,使用了第三人稱敘事。而由于小說中敘事者既無法透視故事中人物的內心活動,故事中人物又并未替代敘事者的眼光,因此小說采用的是攝影式外視角,即站于故事外的敘事者扮演著攝影機的角色,單純客觀地拍攝、記錄故事中人物的語言和行為,并不予以額外評論。
作品開篇就呈現這樣的畫面,隨著“鏡頭”的移動,我們先看到白色的群山,再看到埃布羅河河谷,接著看到車站,轉而又看到酒吧,隨后看到一對男女及一張桌子。小說第一句話“The hills across the valley of the Ebro were long and white”就開門見山地交代白色的群山連綿起伏,“白象”的形象由此凸顯了出來。這里,攝像頭帶領讀者由遠及近看到故事景物及人物,展現了聚焦者即敘述者的視角位置。這種視角逼真而客觀,可以在小說中設置很強的懸念。讀者仿佛置身于這個西班牙火車中轉站,天氣炎熱,四十分鐘后從巴塞羅那開往馬德里的快車就要進這站,停車時間兩分鐘。對話中,女生熱情地開啟話題,男人又做出應答,看似尋常生活中的情境,卻勾起讀者無限的猜測。這對男女為何在火車站見面?他們要一同去往何處?還是男人來看望女孩?美國男人在西班牙干什么?女孩美國人還是西班牙人?他倆是什么關系?是一對相愛的戀人?還是偷偷摸摸的婚外戀?對于這些匪夷所思的問題和無從獲知的答案,讀者需要親自給予闡釋。雖然讀者似乎是現場的參與者,是事件的觀察者,但是讀者卻很難接近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樣營造出來的距離恰好呼應了這位男人和女孩謎一樣的關系及“手術”事件所造成的二人疏遠的距離,體現了人與人之間難以相互溝通的困境。
讀者似乎隱約感覺到白象和女孩的“手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小說在敘述進程中,又通過反復來不斷深化“白象”的意象。在美國男人和女孩吉格簡單的兩句關于在酒吧點飲料的對話后,小說暫時用酒吧女人和女孩吉格的眼光替代了敘事者的眼光:
那女人端來兩大杯啤酒和兩只氈杯墊。她把杯墊和啤酒杯一一放在桌子上。看看那男的,又看看那姑娘。姑娘正在眺望遠處群山的輪廓。山在陽光下是白色的,而鄉野則是灰褐色的干巴巴的一片。
“它們看上去象一群白象,”她說。(翟象俊譯)
“冰山化”的敘事策略在小說的敘事視角上體現在讀者主要看到的是攝影式的外視角,而隱藏了偶爾視角轉化的內涵。小說中,攝影式的外視角產生了種種懸念,而敘述者的視角暫時轉化成了人物的視角,即酒店女人在看女孩吉格,而女孩吉格正在眺望遠處的白色群山。女孩的視角更加加深了“白象”的意象,白象是珍貴的,是與眾不同的,對女孩來說是獨一無二且反復縈繞在腦海的。因此,“白象”極有可能是女孩肚中的胎兒,只是對于美國男人來說,“白象”可能難以供養,他還沒有做好迎接“白象”的準備,或者他根本不愿意承擔照顧“白象”的責任,“白象”更有可能成為橫亙在他與吉格感情之間的大山。
二.“場景”式的故事時間
從敘事時序上來看,《白象似的群山》按照人物出場順序和事件發展順序依次進行。美國男人和女孩吉格坐在火車站的酒吧,他們點了啤酒、飲料,女孩提到白象,繼而說到“手術”的話題,兩人一度發生爭執,女孩也因爭執而情緒失控,但火車快進站時男人去車站放好行李包回來兩人又都回歸了平靜。小說陳述的事件實際上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對話,話題的中心就是男人勸說女孩去做“手術”。整個對話也是按自然時序發展的。
從敘事時距來看,《白象似的群山》設定的“故事時間”就在等待火車的四十分鐘內,也就是說從故事開始到故事結束,讀者只能觀察到這對男女在故事中等待火車的這四十分鐘所發生的全部事情。而讀者所能觀感到的“話語時間”也不過是限制在100多行的簡短對話,總共1400多詞的篇幅中。由于小說中故事時間和話語時間是基本相等的,因此根據熱奈特在《敘述話語》中的理論,可以判斷《白象似的群山》所采用的敘述時間的表達方法是“場景”式的。而最常見的場景就是文本中的人物對話,在小說中有這樣一段對話:
“你現在能為我做點事兒么?”
“我可以為你做任何事情。”
“那就請你,請你,求你,求你,求求你,求求你,千萬求求你,不要再講了,好嗎?”
他沒吭聲,只是望著車站那邊靠墻堆著的旅行包。包上貼著他們曾過夜的所有旅館的標簽。
“但我并不希望你去做手術,”他說,“做不做對我完全一樣。”
“你再說我可要尖聲叫了。”
那女人端著兩杯啤酒撩開珠簾走了出來,把酒放在濕漉漉的杯墊上。“火車五分鐘之內到站,”她說。
“她說什么?”姑娘問。
“她說火車五分鐘之內到站。”
姑娘對那女人愉快地一笑,表示感謝。(翟象俊譯)
這段對話既是事件的高潮,又是事件的轉折。男人與女孩在“手術”問題上爭執不下,引起女孩的強烈反感,以致于要情緒失控。整段對話中圍繞的“手術”這個話題可能是指男人想勸服女孩去做的流產手術。這一場景為讀者呈現了強烈的既視感。敘述者放棄了對文本的評論注解,也無意使用間接引語和自由間接引語這些含有敘述者聲音和理解的語言,甚至省略了如“他說”等對人物話語的附加解釋。將讀者推至“場景”現場,親自觀察審視故事人物的對話和舉止。
海明威擅長的“冰山”原則體現在《白象似的群山》的敘事時間上,就是雖然使設定的事件時長和敘事時長一樣占時短暫緊湊,但故事背后還有更多的故事,等待讀者去挖掘并體會。通過讓“故事時間=話語時間”來增強讀者的在場感,而敘述者賦予“手術”較多的話語時間,使讀者察覺到“白象”對于故事人物,即美國男人和女孩吉格的特殊的存在性,從而深化了故事的內涵。故事人物的話題分散、無確指,也是對男女性感情疏離、心靈異化的反映。
三.故事空間的雙重內涵
《白象似的群山》并未涉及敘述者的“話語空間”,所以本文僅研究小說的“故事空間”。“故事空間”之所以重要,不僅在于其為文本中的人物創造了活動空間,更在于其對文本主旨的揭示以及對人物心理活動的描寫和人物形象的刻畫。
敘事空間需要用“眼光”去觀察,所以往往會結合視角而展開敘述。正如《白象似的群山》第一段所展示的攝像式視角,讀者可以跟著鏡頭以俯瞰的角度對“故事空間”進行全景把握,故事人物也連同所處的空間一起展現在讀者眼前,即一對男女、酒吧女人、河谷、山、車站、酒吧、房屋。因此小說全文的布局也正是從空間角度切入的。
為了讓故事畫面更清晰具體,小說有時更采取人物視角的空間描寫,如待男人和女孩在小店外坐定并點好飲料后姑娘眺望遠處的群山,她 “看見”:“山在陽光下是白色的,而鄉野則是灰褐色的干巴巴的一片”(翟象俊譯)。正是這一“看見”,女孩吉格隨之想到一個可以轉移煩悶情緒的話題,繼而做出可能幫助改變氣氛的嘗試,她說“它們看上去像一群白象”。相比男人的不負責任和消極情緒,女孩更迫切地爭取機會解決問題,試圖打破相處的尷尬和僵局。不知是炎熱的天氣所致干旱還是戰爭后生態被破壞后的窘況,灰褐色的干巴巴一片的鄉野通過表達自然環境的惡劣,恰到好處地烘托了男女間談話緊張的氣氛。
對話中圍繞著“白象——手術”這對含有因果意味的關系,女孩窮追不舍,男人試圖逃避又極力掩飾。天氣的炎熱和情緒的煩悶相疊加,女孩變得憂慮和失望,轉而去關注周圍的景色,相應地,敘事視角再次暫時切換為女孩的視角:
姑娘站起身來,走到車站的盡頭。鐵路對面,在那一邊,埃布羅河兩岸是農田和樹木。遠處,在河的那一邊,便是起伏的山巒。一片云影掠過糧田;透過樹木,她看到了大河。(翟象俊譯)
此時的空間環境卻恰好與之前所描寫的灰暗的環境形成反差,變得美好和諧,更似乎是與協商無果后的情緒形成強烈的對比。
小說對于故事空間的敘述,依據“冰山”理論的創作原則,“冰山”以上的文本揭露工業文明給生態所造成的破壞行徑,生動地襯托渲染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人們的精神生態狀況,即不知不覺陷入了精神的荒原。但“冰山”以下的文本,則是呼喚人們直面慘淡的人生,即使生活一團亂麻,也要向前看,去探索生命的真諦和生活的意義,去處理感情的疏離、去應對精神生態的危機。
四.結語
海明威的短篇小說《白象似的群山》依據“冰山化”理論,在敘事視角上采用攝影式外視角以凸顯“白象”意象,通過“場景式”的故事時間增強讀者的參與度,又以故事空間和敘事視角相結合的設置深化文本的雙重內涵。小說的敘事特征不僅強化了讀者對于文本表面的閱讀體驗,更鼓勵讀者去挖掘探尋“冰山”以下文本的深層根源和內涵,即走出男女感情危機和人性精神荒原的危機。
參考文獻
[1]申丹.敘事、文體與潛文本:重讀英美經典短篇小說[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2]申丹,王麗亞.西方敘事學:經典與后經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3]張薇.海明威小說的敘事藝術[D].蘇州大學,2003.
(作者介紹:陽志奇,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